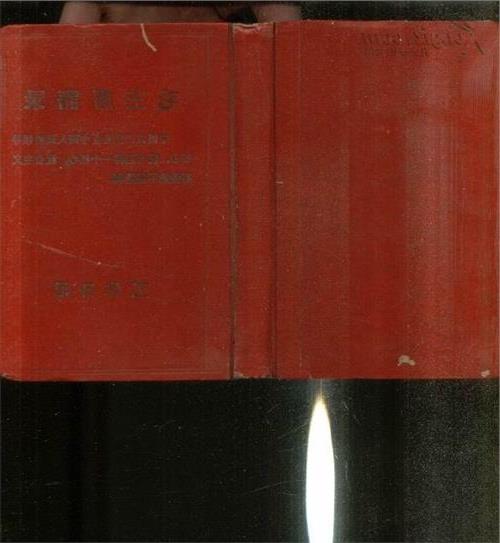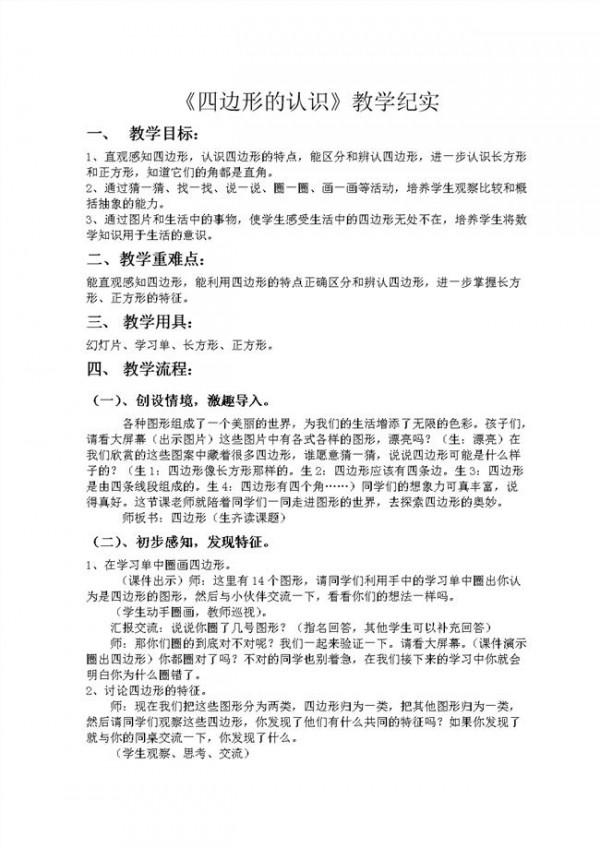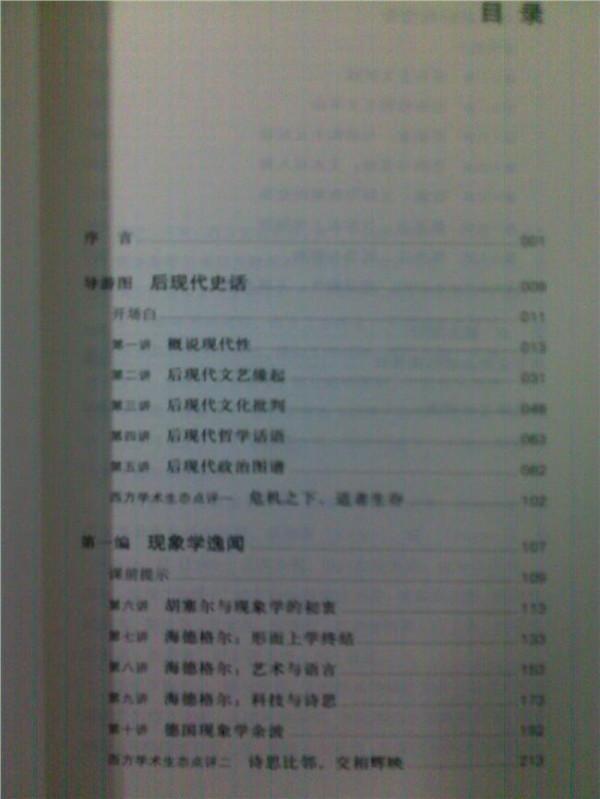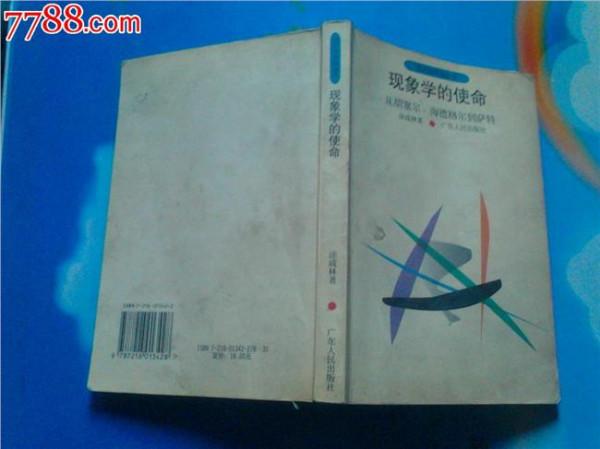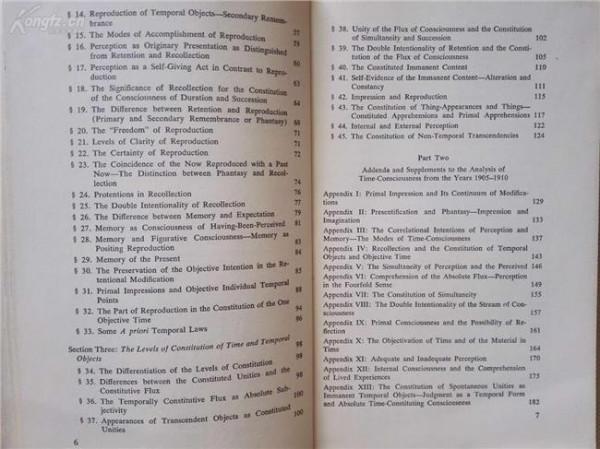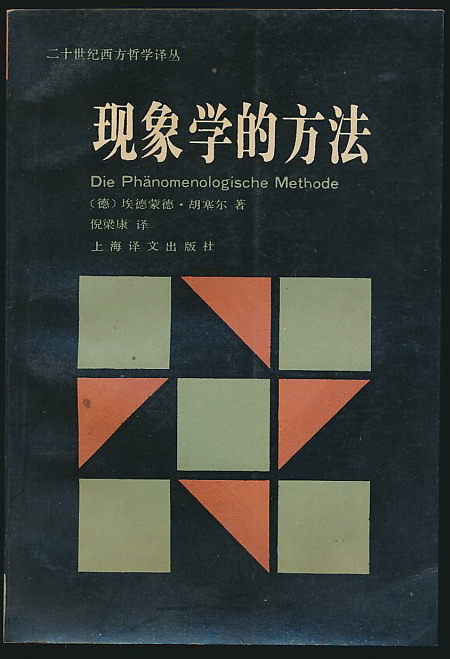胡塞尔时间分析中的“原意识”与“无意识”
“意向性”这个表达——如海德格尔所说——即便在胡塞尔之后也仍然“不是一个口令,而是一个中心问题的称号”;但同时也为海德格尔以及后世所普遍承认的是:通过胡塞尔的分析,意向性获得了“一种原则性的揭示”。[1]这个基本确定同样适用于并且尤其适用于时间意识的问题领域。
因为毫无疑问,通过他的意向性分析和研究,胡塞尔在时间意识领域中引发出诸多的讨论,并且因此而开启了更为宽阔的视域。在这些众多的讨论中,我们在这里尤其要关注一个特殊的问题组,它与胡塞尔时间分析中的“原意识”和“无意识”处在紧密的联系中。[2]
从词的构成来看,“原意识”(Urbewußtsein)与“无意识”(Unbewußtsein)这两个概念是如此接近,以至于它们常常会被混淆起来。[3]但是,这两个概念在胡塞尔的时间分析中却根本不具有相近的意义,这一点表现在:胡塞尔原则上——至少是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时期(1905年)——把对无意识的分析视为不可能。
他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谈论某种‘无意识的’、只是后补地(nachträglich)才被意识到的内容是一种荒唐(Unding)。
”他接着说,“意识必然是在其每一个阶段上的被意识存在(Bewußt-sein)”(十,106)。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显然是现象学的直接直观原则,即人们不应当以某些从根据中推导出来的东西为基础,而应当仅仅建基于某些直接可直观到的东西之上。
类似于M. 舍勒所讨论的“超意识的人格”或“超意识的存在”论题,根本不是胡塞尔所想思考的东西。J. 德里达的断言在这里还是有效的:“胡塞尔对经验以及‘实事本身’的效忠誓言,使得别样的情况在这里成为不可能”[4]。
但胡塞尔仍然在他发表的文字以及在他的研究手稿中不时地考虑“无意识现象”(六,192),甚至谈及一门“无意识的现象学”(十一,154)。如果胡塞尔不是自相矛盾,或者说,如果一门“无意识的现象学”并不意味着类似于“木质的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讨论这样的问题:在胡塞尔意义上的“无意识”与“原意识”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或者说,胡塞尔在它们之间确定了何种关系,并且一门原意识的现象学以及一门无意识的现象学在何种范围内是可能的。
这里的研究便试图阐释这些问题。
一.与“无意识”相关联的两个“原意识”概念
在我们转向“原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指出:原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区别构成了时间流构造的一个核心问题。更具体地说,在这里所说的无意识与在一个根据滞留才被给予的开端时段上未被意识到的滞留内容有关。
这个开端时段与原意识的联系只是在于:胡塞尔——至少是在时间意识讲座中——把每一个内容都标识为“自身必然被‘原意识到的’”,并且把一个未被意识到的内容——如前所述——称之为“荒唐”(十,119)。
这里所说的“原意识”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实际上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方面,它标志着处在滞留与前展之间的原印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谈及“原意识与滞留”以及“如果没有原意识,那么滞留便是不可思义的” (十,119)。这个原意识概念是“原印象”(Urimpression)概念的同义词。
另一方面,原意识在胡塞尔那里还意味着“自身意识”(Selbstbewußtsein)或者说“内意识”(inneres Bewußtsein)。它首先涉及到一个被意识到的“内容”或一个意识。如前所述,被意识到的乃是意识体验在其自己进行的过程中的自身进行活动本身。意识进行的这种被意识到状态可以说是构成了任何可能的后补反思的前提。因此,倘若我们不具有原意识,我们也就不可能进行反思(《全集》四,318)。
这里还须提到的是:这两个原意识概念都不是指一种对象性的行为,并且因此也都不是指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意向性,而仅仅是指“特殊的意向性”或者说“特有种类的意向性”(十,31、118)。据此,我们可以将滞留、原印象(原意识)和前展称作三种特殊的意向性。
这也就是说,在时间意识中有三种时间性的东西以下列方式被意指:滞留、原印象、前展。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在我还把捉着已流逝时段的同时,我也贯穿地经验着当下的时段,我也‘附加地’——借助于滞留——接受它,并且还朝向将来的东西(在一种前展中)。
”(十,118)在此意义上,这里存在着三个对时间的观看方向,或者说,三种时间的外观。但由于滞留、印象和前展如前所述并不是真正的意向,因此这样的“观看方向”或“朝向”也不是真正的朝向,而且它们——如K. 黑尔德已经指出的那样——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充实”。因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说,在内时间意识中还不可能谈及对象性的意向。
我们现在可以一步一步地重复一下胡塞尔的思路:第一步:没有滞留,回顾的目光便是不可能的。更确切地说,“开端时段只有在它流逝之后才能通过上述途径,即通过滞留与反思(或者说,再造),而成为客体” (十,119);第二步:滞留是狭义上的原意识的变异。没有原意识,任何滞留都是不可能的。以此方式,前面所引的胡塞尔的命题便得以自明:“如果没有原意识,那么滞留便是不可思义的” (十,119)。
二.胡塞尔时间观中的所谓“现前主宰”
由此可见,现在(Jetzt)或现前/在场(Präsenz)或当下(Gegenwart)在胡塞尔的时间分析中构成了一个原初的和中心的点,或者说,一个“原形式”(Urform),以后它也被德里达称之为和批评为胡塞尔时间现象学中的“现在的主宰”或者说“现在-现前的特权化”。
德里达以此指出,这个始终想“对形而上学空泛争论做一了结”(二十七,142)的胡塞尔,自己却仍然处在希腊的传统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屈从于“希腊的现前形而上学”(《声音与现象》,117-118/80)。
在做了这个简述之后便可以说,原意识的问题的确涉及到时间意识的“原始形态”,“正是在这种原始形态中,时间之物的原始差异直观地、本真地作为所有与时间有关的明见性的原本来源构造起自身”(十,7)。
但显而易见的是,德里达的批评乃是建立在一个对胡塞尔时间分析的误解之上。这个误解是因为德里达没有足够地区分“滞留”(Retention)和“再造”(Reproduktion)所导致的。这里的要点在于这样一个实事状态:如果不能鲜明地区分滞留与再回忆,那么也就无法分离感知与想象。
恰恰是通过他的时间意识分析,胡塞尔才找到了划分感知与想象的途径。[5]但笔者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分析德里达的这个误解,而是宁可转向他的另一个误解,即:德里达也没有注意到,时间分析的希腊传统还具有另一个重要的趋向,即柏拉图时间观的传统。
正如黑尔德在至此为止尚未发表的一篇报告手稿中所示明的那样,柏拉图在《蒂迈欧》中已经将时间定义为“永恒的形象”并且把“这个形象”标识为“活动的”(《蒂迈欧》,37 d 5)。
而德里达所理解的现前形而上学的希腊传统仅仅是指“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接受而来的时间概念,它是从‘现在’、‘点’、‘界限’和‘圆圈’这些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声音与现象》,116/77)。
除此之外,德里达的下列断言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即: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所做的时间分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与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概念进行了决裂(116/77)。这个论断其所以不能成立,首先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这种陈述在《存在与时间》中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其次,这样的陈述在《存在与时间》中出于以下理由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实际上是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一年后才发表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受这些微小知识错误的误导,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潜含批评毋宁在于,胡塞尔的时间分析并没有做出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现前形而上学的彻底决裂。
确实,作为点的现在的概念在胡塞尔的时间意识讲座中起着一个中心的作用。而且同样确实的是,胡塞尔以此而与亚里士多德的时间理解相衔接。因为后者将时间看作是可计数的各个现时的现在点或现在序列,并且因此而把时间变为固定的形式,如今这种做法构成了自然科学时间观的基础。
但是,倘若那种臆想的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赞词的确成立,那么胡塞尔与这种(被海德格尔称之为)亚里士多德的“流俗的时间观”的决裂究竟何在呢?这是第一个问题。与此相连的还有第二个问题:现在的主宰必然就意味着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或者说,前者无条件地会导致后者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今天已经不再困难。即便是德里达本人也已经注意到:“胡塞尔不仅认识到,没有一个作为瞬间或纯粹点状的现在可以被孤立起来,而且他的整个描述都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灵巧和细腻的笔触来追踪这个不可还原之延展的各个原初变异”(《声音与现象》,116/78)。
恰恰是这些为胡塞尔所做出的认识,使得胡塞尔有可能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时间观进行彻底的决裂。现在-点(Jetzt-Punkt)在胡塞尔这里成为现前-域(Präsenz-Feld)。
用黑尔德的确切表述来说就是:胡塞尔的划时代发现就在于,“具体地经验到的现在不是一个未延展的界限,而是现前域(Präsenzfeld):当下意识以‘前展’和‘滞留’的形态自身展开到某个——依赖于各个注意力程度的——宽度之中,并且作为具有“原印象”的视域环境、作为体现之核心的视域环境而共同当下地具有正在到来的最近将来和正在消失的最近过去。
这样一种关于现前域的意识从本质上有别于作为现在次序的时间的意识,这个区别在于,前者自身是一个发生——用隐喻的方式说是一条“河流”——,而被构造的客观时间作为现在次序却具有一个固定的、不动的形式的特征;在这种形式中,原初的时间方式停滞下来。
”[6]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胡塞尔把时间理解为“运动着的河流”,那么他便已经确定了柏拉图传统的方向。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如果胡塞尔同时也把现前域视作时间中的中心点,那么他便始终还在某种程度上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就此而论,他可以说是无意中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这样,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同时得到回答。作为中心点的现前域与现在核“始终还是界限,但这个界限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理念化的产物,而是被理解为在现前域发生中的这样一个可被经验到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滞留变更与前展变更的连续统相互交切’”(同上文,页5)。
由于现前域不是固定的、不动的形式或单纯的理念化产物,而是流动的、可经验的时间位置,或者说,时间的原初发生,因而对“现前形而上学”的批评便失去了效力,因为这个批评建基于一个假设之上,即:现时现前的特权仅仅意味着“与形而上学的原则性区分、即对形式和质料的原则性区分的系统联结”,并且此外还意味着对这样一个“传统”的证实,即“那个在希腊的形而上学和‘现代的’作为自身意识的现前形而上学或作为表象的理念形而上学之间创建起连续性”(《声音与现象》,118/80)的传统的证实。
上面所做的分析已经表明这样一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德里达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现某种形而上学的现前痕迹,而更多地是在于创建一门“作为无意识的非现前的理论”,或者他自己也说,“对非意识的思”(同上),他试图通过这种思来比附胡塞尔的先验意识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将这个有趣的尝试当作我们的探讨课题。在对胡塞尔的原意识概念进行了一定的阐释之后,我们现在更多是要探究在本文标题中含有的另一个胡塞尔的概念,即“无意识”的概念。胡塞尔的“无意识”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