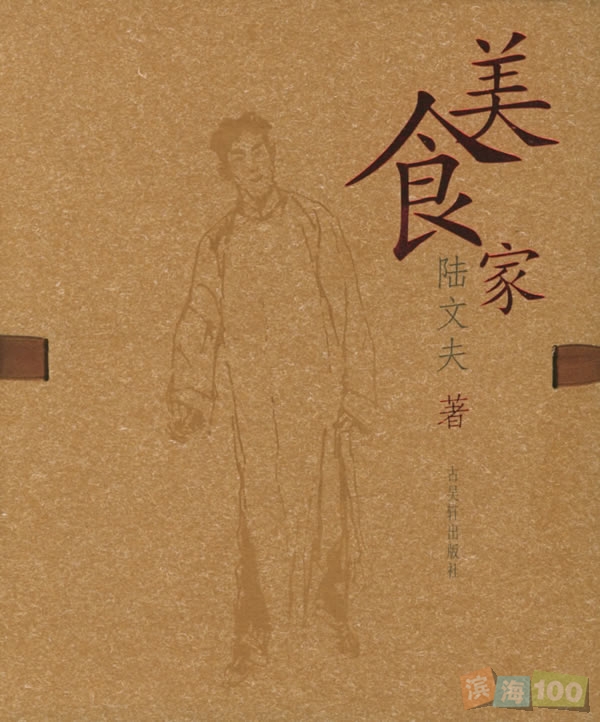蒋子龙作品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作者:蒋子龙[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作者:蒋子龙[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我和金厂长到公司汇报工作。坐进吉普车,好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他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问题:“‘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是哪个戏里的一句词儿?”我看看他:“《沙家浜》。”谁也不再说话了。
但是他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直到下了车,踏进公司的办公大楼,金厂长又对我说:“我们要争取头一个讲。开头大家总有点客气,你推我让。有身分的人不想开头一炮,都愿意先听听别人怎么讲。我们这样的小厂,正好可以挤上去。
再说会议刚开始,领导们精神集中,听得仔细。到后边老头们都累了,抽烟喝水上厕所,谁还认真听你的发言。”我佩服他的分析,但也替他担心。他来厂还不到一个月,能讲些什么呢?公司通知是厂长来开会。
任何会都有个灵活机动,憨厚的刘书记害怕金厂长来的时间太短,情况掌握得不多,提出叫骆副厂长来参加。我知道骆副厂长也最愿意干这种出头开会的事。可是金厂长笑笑说:“我还是去吧。”非常微妙。是他不愿意给骆明这个以厂长身分出头露脸的机会呢?还是自己不愿意放弃这个在公司领导面前表示新身分的机会呢?会议开始以后,他果真头一个发言,讲得很生动,举出了庞万成三天丧假只歇一天半的例子。
他表扬的是工人,没有表白自己。
给人的感觉却是领导很高明。公司领导表扬了我们厂。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厂受到表扬,太稀罕了。我越发感觉到,金厂长这个人不那么简单。第二个发言刚开始,金厂长就悄悄地对我说:“老魏,你好好记一下,特别是外单位好的经验和公司领导的指示。
我出去一会儿。”他这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到快散会的时候才回来。真是怪事。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怪事一件接着一件,这两天我发现骆副厂长脸上的麻点不那么明显了。这场新的权力角逐的暴风雨,难道这样快就过去了?骆明这个人不会轻易服输的。
难道是他对金厂长服气了?他似乎也不是那种肯服气的人。中午,我从食堂回到办公室,金厂长正在我的屋里打电话,骆副厂长以少有的媚脸在旁边陪着。“……叫骆晶玉,骆驼的骆,晶体管的晶,林黛玉的玉。
她是我的亲戚,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一个星期内我听你的信儿!好,就这样定。”我心里有点开窍。我不赞成金厂长老来这一套,可是佩服他的心计和手段。骆明是个不好对付、不好配合的副手。
但他熟悉这个厂的生产情况,下边也有一帮子人,如果把他治服了,金厂长的脚跟就算站稳了。我却没有想到金厂长会用这种办法:小人喻以利。难怪有的工人背地议论金厂长够滑的。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我和金厂长到局里开会。
坐了一会儿,他又悄悄地对我说:“老魏,你好好记一记,我出去一会子。”一到公司和局里来开会,他就来这一手。他出去干什么?哪来的这么多事?等了一会,我也走出会场。我想看看他到底去干什么。
天气已经转暖,许多办公室都开着门。金厂长是在化工局大楼里, 挨个屋子“拜年”。从一楼到四楼,一个处一个处地转。每到一个处,就象进了老朋友的家一样。从处长到每一个干部,都亲熱地一一打招呼,又说又笑。
他兜里装的都是好烟,大大方方地给每一个会抽烟的人撒一根。谁的茶杯里有刚沏好的茶水,端起来就喝。当然,他也不是光掏自己的烟,别人给他烟的时候也很多。他和每个处的人都很熟识,又抽又喝。有时谈几句正经事,有时纯粹是扯闲篇、开玩笑,嘻嘻哈哈,非常开心。
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在化工局里,我们厂是排不上号的一个小单位。这样一个小厂的厂长,在局办公大楼竟这样自由自在,到处都有熟人,到哪里都可以谈笑风生,而且认识许多职位比他高得多的干部,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本事。
散会以后,在回厂的路上,我问金厂长:“听说你在局里和公司里有很多熟人?”“今天下午你不都看到了!”他冲着我笑了。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尴尬。他很开心地说:“魏秘书,这些日子我看出来,你是个好同志。
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漂亮,成天忙得四脚朝天,比哪一个厂长 都忙。就是有点书呆子气,办事死心眼儿。老魏,我告诉你一种我发明的学问。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金钱。
在我们国家,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搞好关系。今后三五年内这种风气变不了。我们是小厂子、小干部,要地位没地位,要权势没权势,再不吃透社会学、关系学 就寸步难行。”惊人的理论!我说不清心里是敬佩他,还是厌恶他。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骆副厂长脸上的笑纹几乎把所有的麻点全遮住了,他兴致冲冲地对我说:“老魏,交给你个任务,今天晚上你陪着金厂长到我家里来吃饭。我怕老金不来,你一定得作陪,无论如何要把他拉来!
”我心里说:“浅薄的人。给你闺女找个工作就值得这样!”转念又想,一个五级看泵工,由于某种机缘入了党,当上了副厂长,你又能要求他怎么样呢?我是决不能到他家里吃这顿饭。以前我遇到这种拉拉扯扯的事就往老婆孩子身上推,不是借口老婆病了,就是推说孩子发烧。
反正是老婆孩子跟着我倒霉!今天说轻了推不掉,我狠了狠心就对骆副厂长说:“哎呀,不凑巧,我那个小不点得了肺炎,下班后我得赶紧回家送他上医院。
”骆副厂长的脸象外国鸡,立刻变了:“我就知道我老骆的脸小,请不动你这位大秘书。这样办吧,下班前,你把老金送到我家门口,然后,就请你自便。”我没有办法,谁叫我是秘书呢!只好冲着骆副厂长的背影又骂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将来要再给人家当秘书,我就把他的手指剁掉!
”临下班的时候,我去请金厂长。金厂长答应得很痛快,而且约我一块去。我把瞎话又说了一遍。金厂长那对突出的金鱼眼眯成了一道缝儿,笑了: “老魏,你不会编瞎话,往后就别编了,瞧你那脸色,红了又白,白了又红。
”“金厂长,这是真的……”我急忙遮掩。他笑得更凶了:“得了,你的瞎话千篇一律,连个花样也不会变。你就不拿耳朵摸摸,全厂谁不知道魏秘书有一手绝话,一 旦人家有事求他,他不愿意给办的时候,就往老婆孩子身上推。
老魏呀,你那么大学问编什么瞎话不行,干嘛非给老婆孩子招灾!”我只好苦笑着摇摇头。他拍拍我的肩膀:“你真是个书呆子,副厂长请客,不吃白不吃。
他要是拿出两块钱以下的酒,咱都不喝!你就跟着我去,进门不用你说话,只管低头吃你的饭。这样的美事还不干!”我最终也没有去。但我知道了骆明请客的原因,他的女儿今天到国营无线电十厂去报到了。金厂长的道行真大,这一手就可以把骆明给降住了。
当党性、纪律和法律对某些人不起作用的时候,也可以用义气和恩惠试一试。不知为什么,金厂长这一手却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敬佩。相反,他在上任第一天留给我的那个朴实可亲的印象,已经被后来的这些事给冲淡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九月的日记略)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上行下效,领导干部之间关系有多复杂,社会上就有多复杂,群众的思想就有多复杂。骆明和金厂长摽成把了,刘书记和金厂长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今天在讨论奖金问题的支部会上,书记和厂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了。
九月份,上级发下来一个文件,工厂可以从利润里按比例提取奖金。我们厂原是由搞综合利用起家的,大部分原料是捡别的厂甩出来的废物,花钱不多,一本万利。
发奖给钱的事,厂子越小、工人越少,就越好办。九月底一结算,每个工人可以拿到五十元奖金。就连科室的干部,也可以分到四十多元。大部分工人等于一个月拿双份的工资。刘书记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汉子,一听这个数目字吃了一惊。
虽然他的生活条件在厂级干部里最差,每月多收入四十多元还是很需要的。但他一摆脑袋,表示反对:“不行,发这么多的奖金,这可了不得!”“有什么了不得?”他的意见遭到了不少人在心里反对,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钱不是坏东西,给多少也不烫手,每月多进个四五十元,谁还不高兴?但是,委员们嘴里,谁也不说赞成,谁也不说反对。都拿眼瞅着厂长和书记,等着一二把手定板,谁 都想多领钱,少担责任。
金厂长对骆明说:“老骆,说说你的意见。”骆副厂长很干脆:“应该发给工人,照文件办事。”刘书记说:“文件是指一般情况说的,我们有我们厂的特殊情况,不能钻这个空子。上级要知道我们发这么多奖金,也不见得就会同意。
”骆明:“这笔钱不发给工人怎么处理?难道白白地上交?”刘书记:“存在银行,将来搞点集体福利设施。”金厂长只顾抽烟,一言不发,谁也猜不透他的态度。他是个会处关系、善于权衡得失的人,决不会为了多给工人发几十块钱的奖金而让自己担风险。
万一为了这件事和局、公司的领导把关系搞僵了怎么办?伤害了国家利益,使工厂和国家的关系搞坏了怎么办?哪头重,哪头轻,他不会不知道,他不会因小失大。更何况党支部书记已经表态,象他这样的人难道愿意站到书记的对立面去吗?连我都觉得,金厂长一定不会同意发奖。
金厂长开始表态,一张嘴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老刘说得对,奖金数目是大了一点……”胳副厂长脸突然涨红了:“你——”金厂长冲他摆摆手,他们两个似乎是私下已经碰过头了。
我心里一动,金厂长既然收服了骆明,就一定会利用这个“贼大胆”。今天说不定也是拿他当一杆枪,先试试刘书记的火力。金厂长接着说:“我们是东方化工厂的领导,我们用不着替国家操心,我们要操心的是东方化工厂的群众,得罪了他们,我们就要倒霉了。
文件向群众传达了,如果奖金不照数给,我们就失了信,国家也失了信。我们挨骂还不说,群众的心气一散,生产就会掉下来。所以,我主张五十元的奖金一个不剩全发下去。
公司里要问,我们有词儿:按上级文件办事。兄弟厂要反映,咬扯我们,我们更有理:这是多劳多得,我们厂搞得好,给国家赚钱多,奖金自然就发得多,大伙说怎么样?”委员们大多数都同意金厂长的意见,就算通过了。
刘书记心里感到发这么多奖金不合适,嘴上却又讲不出更多的道理。虽然在会上按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金厂长的意见,可是散了会,老刘把金厂长留住了。他就是这么个爱钻牛角尖的人,骆副厂长背后就骂他是“犟死亲爹不戴孝帽子”。
我要给公司赶写个材料,下班后也没有走。我把通刘书记房子里的上亮门打开,一边写着材料,一边支起耳朵听着隔壁房间里谈话声。我担心刘书记的脾气,他也太认死理、老实得过份 了。
以前正副厂长不和,他成天焦心。调走的王厂长最对他的脾气,作风正派,对上对下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弄虚做假。就是心胸太窄,爱生闷气,不到一年就被骆明气跑了。现在来了个金 厂长精明能干,上上下下关系都处得挺好,连骆明都服气了,正副厂长配合得挺好。
按理说老刘这个党支部书记不该省心了吗?他却偏要没事找事。过去他和王厂长两个人还对付不了一个骆明,现在他一个人又怎么能对付得了金厂长和骆明两个人!心实的斗不过心虚的,搞事业的斗不过搞权术的。
我真替他、替我们厂担心。隔壁房间里老刘的声音越来越高:“……当个领导最主要的 是思想要端正,不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口味,八面讨好。更不能拿着国家的东西送人情。老金,有人确实向我反映这个问题,你不能不注意点。
”这话说得太刺人了,一把手对二把手哪能这样说话!我赶紧把写好的材料送过去,冲淡他们的紧张气氛。金厂长真有两下子,什么话都听得进去,脸上一点不挂相,冲我一笑,说:“老魏,你来得正好,咱们一块扯扯。
咱们这位刘书记真够呛,难怪以前咱厂的班子都尿不到一个壶里,他这个一把手不是给下边擦屁股,下边得给他擦屁股。我问你,你说我思想不端正有什么事实?你说我拿国家的东西讨好群众,我执行的是不是上级的文件?”“唉!
”老刘一摆手,“给钱的事越多越不嫌多,一降下来群众就有意见。但是,我们作领导的应该为群众的长远利益考虑,要教育引导群众,文件上不也说可以抽出一部分奖金搞些集体福利事业吗?”“你扣住这五十元不给,那群众就会骂我们。
再说你把这钱扣下干什么用?”“留点后路,长流水不断线,万一哪个月出点事,没有完成任务,仍然可以发奖。再说钱存多了还可以给群众盖点宿舍。”“得了,刘书记,你吃亏吃得还不够!
”金厂长转头对我说,“你当秘书最清楚,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现在叫你发奖,你就发;如果不发下去,精神一变,剩下的钱你就没有权力支配了,你还想盖房子?咱们这个小厂,好不容易盖几十间房,土建部门要几间,管电的要几间,给水的要几间,煤店、副食店再要走几间,层层扒皮,我们还能剩几间?花了钱,受了累,还得惹气挨骂,本厂工人落不着实惠。
把钱往大伙手里一分,又稳当又实惠。”刘书记并不认可,但他也不吭声了。
金厂长掏出烟盒,每人给一支烟。老刘没接,掏出自己的烟吸着。金厂长也不在意,把给老刘的那支烟叼在自己嘴上,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老刘,你那一套五八年以前行得通,现在不行。对上级文件既不能不办,又不能完全照文件的精神办,这里边学问可大啦。
就说你老刘吧,在这方面坐了多少蜡!文化大革命中遣送的可以回城安排工作,你没有快抓快办,现在又冻结了,叫就地安排。这一件事你挨了多少骂?退赔,办得快的钱就拿到手了,办得慢的就没拿到。
这种事多了。谁死板谁就吃亏。”金厂长说得很诚恳,他是真心想劝刘书记灵活点。我却觉得老刘听了这番理论,对他的反感更深了。—九七九年十月十日得便宜卖乖,奖金发下去了,全厂上下议论纷纷。
可气的是,群众对昨天党支部会上讨论奖金问题的争论都知道了,而且知道得比我的记录还详细。刘书记挨了大骂,金厂长成了“青天大老爷”。我感到不公,替老刘抱不平。金厂长提出要借发奖金这个东风,把群众情绪鼓起来。
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金厂长在会上做了个简短而又深得人心的报告,没有叫我给起草,那是真正代表厂长的水平。他说:“……这个月的奖金一分不少,全发给大伙了。有人接到这一包子钱,吓了一跳。只要大家干得好,我们厂的利润再提高一块,下个月奖金还会多。
你们放心,只要是通过我的手发给大伙的钱,我是一分不扣,一分钟不停,全发给大伙!……”—九七九年十—月二日这个星期天最丧气了,从早晨四点多钟起来的,到下午三点钟,才钓到三四条小鲫鱼。
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金厂长。他钓了满满一篓子,我问他在哪儿钓的,他笑而不答。我猜他一定是和哪个看养鱼池的人有关系,从养鱼池里钓的。他不顾我的拒绝,硬是把鱼分了一半给我。路过他的家门口时,还要拉我上楼坐一会。
我不好拒绝,也想看看他的家里是个什么样子。我猜想,象他这样神通广大的人,家里一定搞得很富丽堂皇。我走进去一看才知他的家里非常简朴,简朴得使我不敢相信这是金厂长的家。他的女儿正在家做功课,他叫女儿给炒个菜,要和我喝二两。
他女儿瞪他一眼,拿起书包到奶奶屋里去了。金厂长还有个老娘,他只好又去求老娘。老奶奶虽然答应给他炒菜下酒,但是嘴里也不停地埋怨儿子。很快我就从老太太的嘴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金厂长每月工资七十多元,只给家里一少部分,剩下的抽好烟,喝好酒。每天晚上在饭馆里喝完酒,回到家里随便吃两口饭就行。老娘和两个孩子主要靠他爱人的工资养活。他在家里的地位,远不如在工厂里。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一种人。这使我对他倒产生了一种好感。是同情他的家庭,还是欣赏他把神通用到厂里,并没有往自己家里搂东西?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真是莫名其妙!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班铃早响过了,干部们一个也没有走。
金厂长从银行打来电话不让干部走。从早晨一上班他就带着财务科长到银行去了。我们厂在年底每人要发一百元的奖金,银行不同意。厂长亲自拿着文件去交涉。他在银行蹲了一天,连中午吃饭都没回来。
不知他把干部们留住是什么意思?又等了一会,厂长回来了。他满脸喜色,对干部们说:“大家都动手,今天无论如何要把钱分出来,发下去。”干部们一个个都很髙兴,在财务科长的指挥下开始数钱,数到一百元就装进一个红信封。
刘书记把金厂长叫到我的屋里,动感情了,说:“老金,不能这样干,这叫滥发奖金!文件里没有叫你年终发这么一大笔钱吧?”金厂长忙了一天,也没有好气地说:“文件里也没有说不让发这笔钱。”“老金,这样要犯错误!
是不是发完这笔钱,过了年,我们厂就关门?”“你这人,真是!”金厂长强压住火气,“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有多少发多少,而且必须在今天发下去。要不还用得着我亲自到银行里去泡蘑菇!上边的精神没有准,一会一变,明年还不知道是嘛章程,要是来个新文件,奖金冻结,你想发也发不了,到那时我们就挨大骂啦!
”“你怕挨骂我顶着!”“这是支部会上定的,你一个人不能推翻。发!”金厂长推门走了,我这是第一次看见他发火。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今天一上班我就收到了好几个文件,其中有一个文件就是通知七九年的奖金暂时冻结。我把文件拿给金厂长,他哈哈一笑:“我早就猜到会有这一手!”一公布,全厂上下对金厂长的欢呼声更高了。干部们也都议论这件事:这一百元拿得太巧了,晚一天就飞了。
金厂长既有远见卓识,又敢做敢为。下午,选人民代表。按我们厂职工人数,区里只给我们厂一个代表名额。今年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上边连候选人都不提,完全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
四个车间分成四个选区,全体干部编为一个选区。车间的三个选区投票结果,金厂长以绝对压倒的优势当选。在干部这个选区里,金厂长只差三票就是满票。这个结果是谁都料得到的。可是也有一点没有料到,在车间的选区里有一张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金凤池是个大滑头!
”由于检票、唱票的那几个工人嘴不严,这句话给传出去了,这对金厂长是个打击。看来不管多滑的人,也很难滑过群众的眼。但是,让群众看出是滑头的人,还能算滑吗?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真正的、让人并不觉得滑的滑头呢?下班后,金厂长提着多半瓶“芦台春”来到我的办公室:“老魏,先别走,可怜可怜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陪我先喝二两。
”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两包花生米。“您怎么不回家?”我问。
“昨天和老婆吵架了,今天不能回去,一回去还得吵。”他把酒斟到茶杯里,一扬脖就灌了一大口。我劝他:“金厂长,您这样不顾家可不行。从下个月起,我把您的工资扣出一大半,送给您的家里。”他笑了:“来来,喝酒!
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老婆和我打了二十年,都没有管住我。你能管得了?来,喝!”他真是个喝酒的能手,光喝酒不吃菜。喝两口酒,才吃一粒花生米。越喝口越大,不一会儿,那对突出的金鱼眼就有点发红了。
他突然盯住我的眼睛说:“老魏,现在的群众真难侍候!五教八流,什么人都有,不管你怎么干,也不会让他都满意。”我明白他是指什么说的,还不好答腔。他喝了一口酒又说:“我是为了群众,得罪了头头。反过来说,让头头满意,一定又会得罪群众。
你知道今天干部投票时反对我的这三票都是谁吗?”我心里一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呢?他一定是疑心刘书记,但刘书记是个光明正大的汉子,他不会投金厂长的赞成票,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只好回答说:“不知道。”金厂长嘴角一咧:“有一票是老骆投的,没错,准是他!”我实在是没想到,也不大相信:“他对您不是很敬佩,很好吗?”他笑了:“那是因为我给他办过事,他那两下子也玩不过我。
但是这个人比较毒,嫉妒心太强。不过今天他不赞成我当人民代表是对的。”我又问:“那一票是谁的呢?”他用食指点点自己的鼻子尖:“我自己!”他不是醉了,就是成心拿我耍笑着玩。“我说的是实话。”他又灌了一口酒,果真是带着几分醉意了,“我知道,连你也瞧不起我,一定认为我是个大滑头,社会油子。
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滑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越混,身上的润滑剂就涂得越厚。泥鳅所以滑,是为了好往泥里钻,不被人抓住。
人经过磕磕碰碰,也会学滑。社会越复杂,人就越滑头。刘书记是大好人,可他的选票还没有我的多,这叫好人怎么干?我要是按他的办法规规矩矩办工厂,工厂搞不好,得罪了群众,交不出利润,国家对你也不满意,领导也不高兴。
你别以为我的票数最多就高兴,正相反,心里老觉着不是滋味。所以我明知老刘不投我的票,我却投了他一票……”“金厂长,你喝多了。”我扶他在值班员睡的床上躺下来,“您先躺一会,我回家给您拿点饭来。”我真后悔下午投了他一票。他虽然票数多,可是他这个人和“人民代表”这种荣誉总不协调。难道金凤池是当今这个时代最合格的“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吗?我在心中连连暗自摇头。我坚信在下次选举中,他一定会落选!



















![>韩少功日夜书 [2013上海书展新书推荐]韩少功:《日夜书》](https://pic.bilezu.com/upload/b/60/b609466569629a51e0fffcc4ae83b7a7_thumb.jpg)

![>柯云路作品 《三千万》作者:柯云路[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https://pic.bilezu.com/upload/e/1d/e1d9f4a4d4da3b27a14758259b3c62f3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