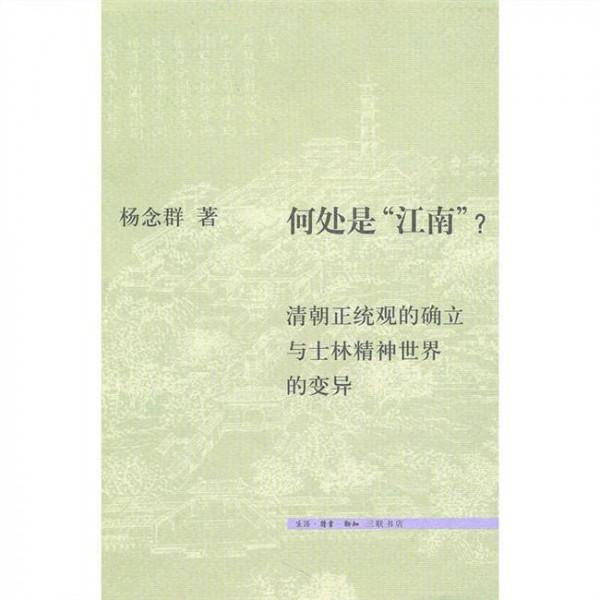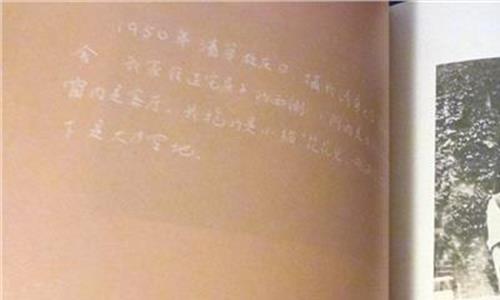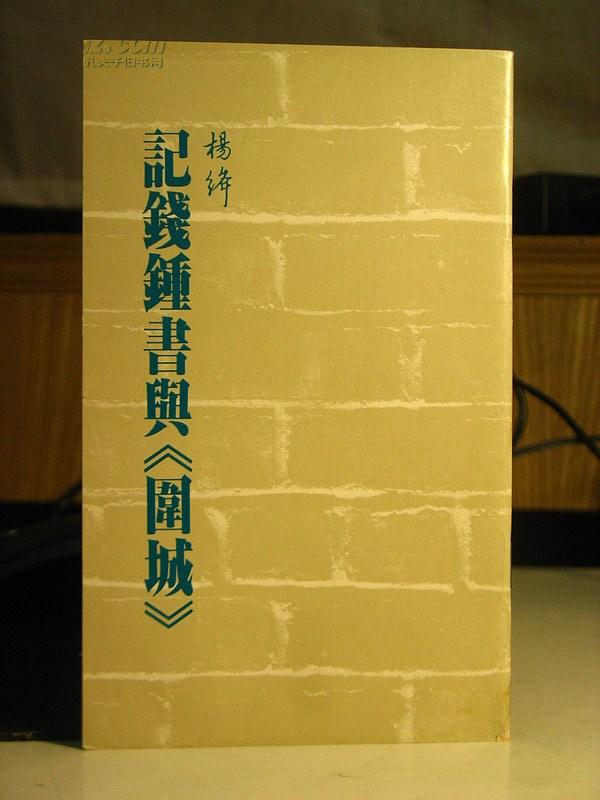杨念群何处是江南 读杨念群老师《何处是江南》后的一点管见
读杨念群老师《何处是江南》后的一点管见
刘卓异
我最近有幸拜读了杨念群老师的新作《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并聆听了杨老师关于此书的一个讲座。杨老师在讲演时反复地讲:“我们都要学着去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略略地读了书中的内容之后,杨老师的感慨是很让我受启发的。
清代明立,虽然在政治上征服了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主体,但江南的士人却绝难接受满清的统治,只留恋明月而无意于清风。江南士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消极抵抗,显得心意十分坚决。然而当老一代的明朝遗老去世后,甚至还未曾等到他们去世,很多江南士人就出现了被“收编”的倾向。到了乾隆年间,江南士人完全丧失了以前的独立与坚守。而杨老师在这本书中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分析。
在明朝灭亡后,尤其是南明的小朝廷也灭亡之后,在江南出现了一大批不与满清政府妥协的遗老,他们拒绝应召,隐逸山中,宁可衣食不足也不出山。还有选择各种方法自虐自残甚至自杀以明志的。他们用隐晦的语言表达他们对前朝的哀思,而对于“北狄”建立的新朝进行坚定的不合作抵抗。
有的在农村种地,有些呆在家里十数年不出门,有些绝不踏进城市半步,有的出家为僧进行苦修,最极端的是以近乎疯癫的方式进行自虐。虽然期间很多人对这些行为的意义产生过争论,但没有人否认他们对故朝的坚守。这其中就有一个尤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吕留良。
吕留良在崇祯皇帝遇难后痛苦不已,尽焚少年诗稿。后其侄吕亮功参与反清失败,被执遇害,留良呕血数升,几近死亡。之后又弃儒服,生活极度贫困。他对官府的畏惧已经达到病态的程度,宁可卖文章写时文也不向朝廷让步,以致晚年出家为僧。吕留良的一生正是明末清初士人的典型写照。
然而这种坚守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就被打破。遗老的后人们开始出来考满清的功名,开始顺着皇帝说话。在杨先生看来,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就这些士人本身而言,他们已无上一代亡国的切肤之痛,而且又有满腹经纶,这都强烈驱使他们出世入阁。即使是他们的上一代,那些坚定的遗老,有时仍会为空负了一身的才学而感到遗憾,因此这些人的后代不再坚守下去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满清政府尤其是皇帝的极具高度汉化,促使了这一“收编过程”。康熙皇帝研读朱子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他的造诣已经超出了一些大儒。当时在江南士林中有一种强烈批判王阳明心学的大势,他们以为空谈结党致使明朝灭亡。而批判阳明心学与康熙帝提倡理学是有契合点的,另外,在反心学的人中有一大批人是赞同程朱理学的。这就使士人的言语同朝廷有一个不谋而合,只要有和就不怕不会产生更大的共鸣。
不止是不谋而合,康雍乾三代帝王对汉文化的精深造诣已经使他们不再是个夷狄之人。倘若江南士人以不与蛮夷为伍而拒绝合作,那么这一点在此时已经不成立了。同读四书五经,受同样的文化熏陶,士人与满清皇帝之间已经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的意识观念渐渐合流。其中很多问题的讨论都出现了不谋而合,如“文质之争”。江南士人认为明末时“文”太重而导致衰微,他们是倾向于“质”的。而满清皇帝也提倡简约。
第三,就是强制力的作用。文字狱起的就是这样一个作用,修《四库全书》也是这个作用,禁止私人修史也是这个作用。在满清政府高压政策下,士人安静了很多。他们开始顺着皇帝的意思说话,不敢再有反对政府的议论,不敢再编著历史。从此,士人的话语权被满清政府成功地剥夺了。
士,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就这样丧失了自己的高贵的独立和顽强的抗拒。实际上,他们的“精神坍塌”已经宣告士阶层的死亡。在一个诺大的国家里只有一个声音响彻南北,而听不到理性而睿智的反对声,这确实是很可悲的。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