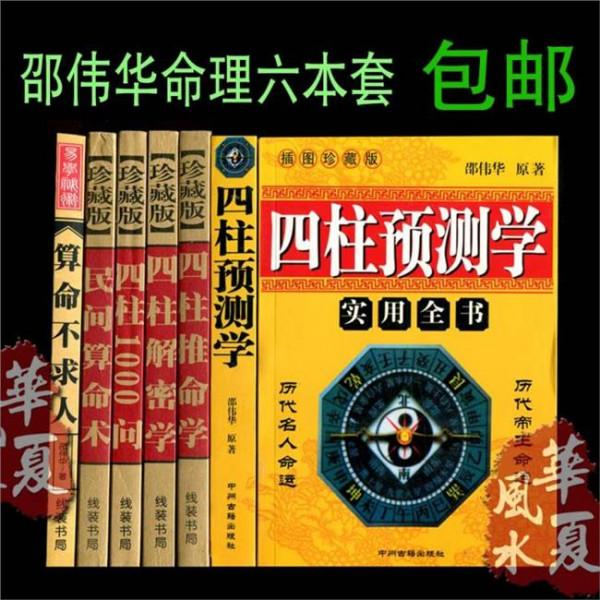邵飘萍的地位 对一幅邵飘萍殓葬照片的重新解读与思考
把这一块泥堆拍了一个相,几个乡人就拿着器具将土拨在两面并且深深掘下去。大约有两尺多深的时候,渐渐地露出白板,一个老年的巡长说,这是特别埋得深一点的,因为飘萍先生生前,大家对他感情都很好。各个人的脸上罩着沉痛。
凄咽的哭声在这广漠的空气中颤抖,……一具不及一尺高半尺宽的薄板棺材抬进芦蓬里,邵新昌先生气厥了,大家又忙着呼唤。当开棺的时候,我看了飘萍先生最后的一眼:惨白的脸色,圆睁着的右眼下是弹痕,有几条转紫的凝血,倒流在头部。
起棺后,抬到地藏庵去成殓!我受不了这种情境所给我的感觉,到那边不久,也就回来。这一晚使我不敢一个人住到伏园先生的房间中去。
上述回忆距事发仅一年时间,应比几十年后一些人的回忆更加准确、可靠。从中可知,早在奉军始进京城,不详的预感就已经笼罩在京报馆同事们心头,大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有一定准备。当报馆被封,大家觉得“这原是意中事”,“并不怎么出惊”,京报馆仍在运转着。
在邢的笔下,李钰的从容淡定和认真负责、孙伏园的及时躲避和迅速离京、邢和同事们满怀悲愤秩序井然地送别“以笔墨为刀剑”的飘萍先生等重要细节,无不生动了然,犹在眼前。
从中可看出,组织者对殡殓活动作了精心策划,时间安排得很紧,整个活动过程有准备、有组织和有计划。虽然邢在行动中处于听候指令的末端,不知谁是指挥者,然其叙述却为我们搞清指令怎样发出执行,以及活动中某关键动作方面之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
1.京报馆被封后的重要联络方式——电话
京报馆在面临社长被捕,经理暂避,报馆被封,人员不能自由出入的困境下,如何与只身在东交民巷的吴定九联系、沟通呢?这个曾让笔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在邢墨卿的回忆中找到了答案。
4月24日晚,身居绍兴会馆寓所的孙福园接到李钰从报馆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明日如没有他的电话通知不要到报馆去”。次日,邢也给李钰打过一个“留起的那叠副刊”的电话。另外,汤修慧在《被难后追述之事实》一文中,亦有邵被害当日三时许“得友人电话”一语。
可见,京报馆虽被查封,军警严禁人员进出,但一直维系着报馆与外界联络的电话却未被警方切断。也就是说,吴定九仍能通过电话与外界、报馆及邵家一直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邵被捕后事态的进展情况,交待和安排报馆事务,而随后为邵办后事的准备、布置和实施则更离不开电话。
即便报馆在26日上午已解封,吴可自由出入,但他不可能仅靠自己或手下跑腿来传递各种信息和商量事情。事实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中国,能够频繁使用当时最先进通讯工具之一的电话来处理日常事务的人,非报人莫属。
所以,在京报馆被查封后和为邵飘萍殡殓期间,打电话一定是吴定九、李钰、汤修慧、邵新昌、邵逸轩等人之间最方便快捷的联络和议事方法。另外,吴与祝寿南同样可用电话联系,因其与母亲和姐姐的住所,正是邵飘萍装有电话的“侧室”。
2.记者为烈士殡殓留下历史写真
所谓“活动中某关键动作”,即指拍摄者为殡殓场面按动相机快门这一动作。如前已述,马连良到现场拍摄照片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讹传,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拍摄者呢?按方汉奇教授的介绍,记录邵遇害后各种场景的十幅照片,有五幅是在临时掩埋处拍的,有两幅是在地藏庵的临时灵堂前拍的,有三幅是在其大殓前后的临时停放处拍的。
既然照片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拍摄的,这就不像是一人所为,而是数人为之。邢墨卿的回忆讲到他在二郎庙临时掩埋处“把这一块泥堆拍了一个相”,说明邢是现场拍摄者之一,而十幅照片中确有一幅拍的是“泥堆”,又说明他很可能就是这幅照片的作者。
至于他到地藏庵后有否再继续拍几个相,其回忆中并未述及,但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
除邢墨卿外,其他京报馆同事有可能是拍摄者吗?答案是肯定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京报社不缺会摄影的记者。例如,那幅照片上身着白孝服的人为邵逸轩和邵新昌二者之一,邵逸轩是美术专业出身的编辑,自然也懂摄影,如果身着孝服者为邵新昌,则拍摄者很有可能就是邵逸轩。当然,同样存在着邵新昌与其他京报馆同事也是拍摄者的可能性。
除京报馆同事外,其他报社同人是否也可能是拍摄者?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如前已引,《申报》4月27日下午1时由驻京记者发回电称:“今日邵振青遗体由永定门外土中挖出,送地蒧庵。记者等顷往襄相助成殓。”这说明当时有不少他报记者在殡殓现场,他们用随身相机拍照不就是作为记者的一种职业性习惯动作吗?当然,这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在当时不可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但事后,拍摄者将照片冲洗出后再交由京报馆和家属留存纪念,应该是合乎情理的一种结果。
至于五十多年后年事已高的照片收藏者无法说清拍摄者是谁,本不足为怪,但可以下定论的是,只有现场记者们才是十幅殓葬照片的真正拍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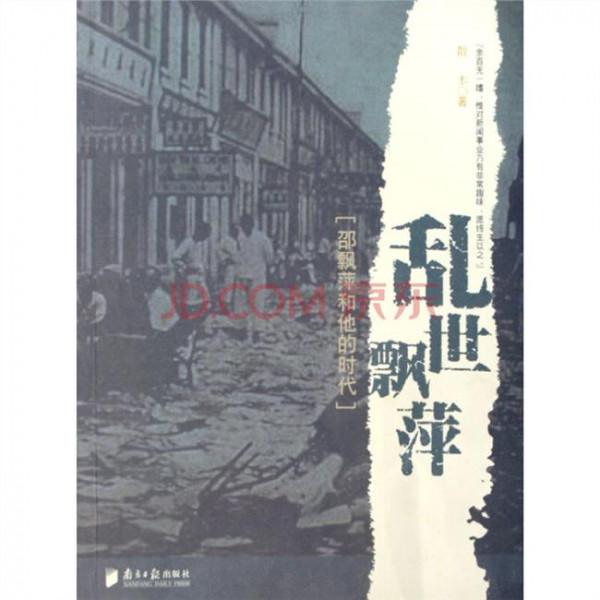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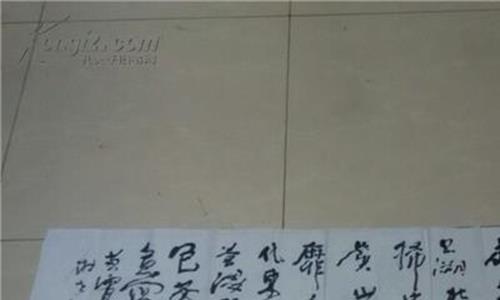
![邵峰妻子刘欣 [邵峰的妻子刘欣]刘欣:邵峰的滋养让我如此幸福](https://pic.bilezu.com/upload/1/6b/16bf81f57e6c81945df194b5207e1dd5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