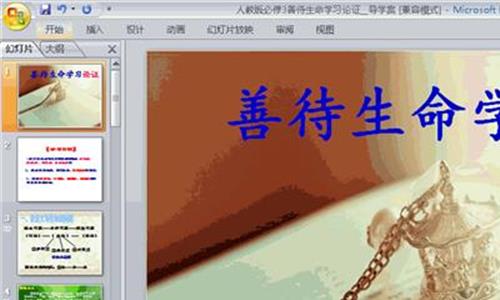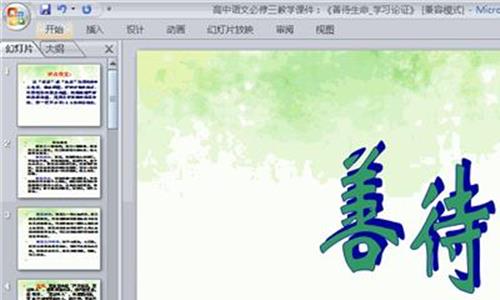罗点点我的生命我做主 生命的思考:我的生命谁做主
虽然谈论死亡的尊严与选择在目前的中国还显得有些前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关注这样的问题,不但关乎个人的生命和尊严,也关乎医疗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关乎社会文明进程的发展。
5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一条新闻: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判定可以尊重植物人患者的意愿,停止延长生命的治疗,任由患者死亡。
事件是这样的:2008年2月,75岁的韩国女性金某因脑损伤陷入植物人状态。她的子女表示,不靠呼吸机延长生命、“有尊严地死亡”是母亲的意愿。在摘除呼吸机的要求遭到医院拒绝后,金某的子女对医院提出诉讼。首尔西部地方法院2008年11月接受金某“尊严死”的请求,之后首尔高等法院也在今年2月判定摘除呼吸机。
5月21日,韩国最高法院9名法官以多数同意的结果决定维持原判。法院方面表示:“如果患者明显会在短时间内死亡,可以说已经进入死亡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治疗,会损害生命尊严,可以根据患者的意愿停止治疗。” 韩国媒体认为,一直备受争议的“尊严死”因此有望实现合法化。
这条新闻在中国反响平平,甚至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尊严死”一词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了解,甚至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恰好在同一天,一场名为“选择与尊严”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在会上讨论着同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在生前签署了表达自己死亡意愿的“生前预嘱”,他们能否在某种情况下对自己的生死作出决定?
由泰利事件引发的思考
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姥爷突发心脏病住院,医生告诉家属,病人病情危重,只能靠升压药支撑生命,但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是放弃还是继续用药?姥姥毅然决定:停药。她说,姥爷走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顺其自然吧。让他体体面面、安安静静地走。在家属同意后,医生拔除了维系姥爷生命的管子。
这个情节是真实的,是导演赵宝刚的亲身经历。剧中姥爷的原型就是赵宝刚的父亲,而做出停药决定的就是赵宝刚本人。
实际上,是否延续没有希望和质量的生命,早已经是一个全球关注的话题。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美国妇女泰利·斯基亚沃的死亡。1990年,泰利·斯基亚沃因医疗事故成为植物人,只能凭借进食管维持生命。她的丈夫于1998年向法院申请拔除妻子的进食管。泰利的父母表示反对,并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2005年2月,泰利第三次被拔除进食管,其父母提出上诉。最终,美国第11巡回上诉法庭做出裁决,拒绝重新为泰利插上进食管。13天之后,泰利在由她引发的巨大争论中死去。
泰利事件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医学的进步,许多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不能安详离去,反而要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等急救措施。而急救成功之后,很可能是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毫无质量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
反思医疗救治的原则
一位同事曾向记者描述家人的经历:婆婆患肺癌两年,花费医药费几十万元,终于不治。临终前,在家与医院之间转战多次的老人已经瘦弱不堪。虽然医生表示,如果继续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还可以延续几天,但老人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让医生停药,放弃治疗。
迁延病榻之上,对病人及其家人来说是痛苦、折磨,对社会来说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有数字显示,中国卫生总费用1980年是143亿元,到2004年达到7590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从近52亿元增加到1293亿元,而个人卫生支出则从30亿元(占总费用的21%)上升到了4071亿元(占总费用的53%以上)。中国脑库的周大力女士提供了一个数据:人一生的医疗费用75%都花在了最后的抢救中。
源于此,世界各国开始反思医学的目的,调整医疗救治的原则。作为重症医学专家,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经历过无数生死场面。据他介绍,1990年美国危重症医学会和美国胸科学会先后发表了两个标志性的文件,提出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当ICU医生确认无益时,应当允许停止全部治疗;二是病人和病人的代理人有权决定治疗。他认为,对濒死的患者提供什么方式的帮助,是危重医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我们的全部治疗无效时,当我们用经验和证据得出患者预后不良的结论时,我们的目的发生了改变,从治愈病人转变为让患者无痛苦地离开。由此,加强治疗的任务又扩展到帮助患者和家属选择‘最佳死亡’的医疗服务。这才是符合伦理的。”
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提出这样3条“缓和医疗原则”:重视生命并认为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痛苦和不适症的办法。这表明, 一种不涉及积极致死行为又给病重和临终者带来最大限度舒适的理想,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潮流。
谁有权决定病人的生死
虽然很多人同意不加干预的自然死亡,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谁有权决定病人的生死,特别是当病人陷入意识不清或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时?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回忆父亲因结肠癌去世的情景时曾触及这个问题:“父亲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不停地给他进行各种治疗,吸痰、清洗、翻身。他十分痛苦。我悄悄地问,能不能不抢救了?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既然大家都知道回天无力,何必浪费资源,让病人徒增痛苦?当时医生的回答我至今还记得。医生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说了算吗’?第二句是‘我们敢吗’?”
事实上,如果病人之前表达过自然死亡的意愿,就能给家人的决定找到依据。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回忆了婆婆临终前的经历。
“婆婆翻身的时候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停,医生第一时间用上了生命支持系统。我们去的时候,婆婆已经被插上呼吸机,虽然心脏还在跳动,可是没有自主呼吸,而且完全丧失了神志。医生说想恢复原来的生命质量几乎不可能,但是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还能拖很多时日,要求我们尽快商量一下,最好进入加强病房,因为在那里才能得到最专业的照顾。加强病房的费用昂贵,尽管婆婆单位很痛快,表示花多少钱他们都承担,可是,以婆婆目前的情况,真的要住加强病房吗?那意味着她要在这种生命毫无质量的状态下停留不知多少时间。婆婆要是还能表达,她会说什么?
“在我的记忆里,婆婆不是没有谈过类似的问题。和许多人一样,在一些场合里她不止一次说过,要是病重,她可不希望被切开喉咙,插上管子,又浪费,又痛苦。我是学医出身,深知婆婆已经陷入她最不想陷入的状态。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向我老公和婆婆的家人说明情况。无论多么艰难,是我们应该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婆婆的情况继续恶化,由于长期末梢神经营养不良,皮下水肿和溃疡很快出现,尿道和呼吸道也出现感染了。
“那天下午,我又去看婆婆。站在床前,我拉着她的手。虽然她处在深度昏迷中,我还是感到从她体内传来的温暖。当我轻轻呼唤她的时候,我甚至还看到她的眼球在半阖的眼睑下转动。我所有的决心在一瞬间崩溃。我问自己,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婆婆的愿望?我们到底是不是在保护她不受痛苦?我忽然觉得,生命和死亡是那么深不可测。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呢?
“当天晚上,我给所有的人打电话,诉说我的疑惑和动摇。我说我对之前的决定完全失去了信心。幸好,哥哥们比我理智,他们坚持了原先的决定。
“后来,在我们整理婆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她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张字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她对自己生命尽头时不使用过度抢救的要求。她还说,因为我是学医的,所以她把这些问题的决定权托付给我。”
虽然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放弃治疗的决定仍让亲人们内心陷入挣扎。让罗点点感到欣慰的是,她发现了婆婆夹在日记本里的那张字条。这可以被理解为非正规版本的“生前预嘱”。
生命尽头的安乐和谐
“生前预嘱”的发源地是美国。1976年8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atural Death Act),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而自然死亡。此后,美国各州相继制定此种法律。
“自然死亡法”允许成年病人完成一份叫做“生前预嘱”(Living Will)或“预先指示”的法律文件,对疾病末期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作出选择。这类文件必须至少有两位成人签署见证。医生根据病人的“生前预嘱”行事,对因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导致的死亡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病人也不再被看做是自杀,不影响其家属领取保险赔偿。
20年间,“生前预嘱”和“自然死亡法”扩展到几乎全美及加拿大。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亚洲地区,这种法律精神也日益深入人心。
韩国医学界法律专家说,韩国有80%的人认为“尊严死”是必要的。但“尊严死”涉及法律宗教伦理等问题,建议成立由政府官员、宗教界人士以及医学、法律专家组成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有关案例,帮助人们有尊严地、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1996年,新加坡制定了《预先医疗指示法令》,并于1997年7月实施。2000年5月,台湾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允许患者在疾病终末期拒绝心肺复苏术。2004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代作决定及预前指示小组委员会发布咨询文件,作出保留现有法律并以非立法的方式推广“预前指示”概念的结论,同时提出了在香港地区建议使用的预前指示表格。
然而在中国,死亡仍是绝大部分人不愿提及的话题。这使得“生前预嘱”在中国的推广显得比较遥远。然而,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罗点点和一些志愿者3年前开设了一个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致力于推广和宣传“生前预嘱”的知识和理念。网站得到了吴蔚然、胡亚美等专家学者们的支持。2009年5月,他们推出了首个“生前预嘱”的民间文本《我的五个愿望》,其中包括: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
罗点点希望通过《我的五个愿望》,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生前预嘱”,以及建立“生前预嘱”如何能在生命尽头帮助实现个人意愿,以促使建立“生前预嘱”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变成事实。“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需要被认识和维护。”罗点点说。
正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所说,要让人们接受“生前预嘱”,接受不加干预的自然死亡,就要让人们了解,它给人带来的是安乐、和谐;同时,为使这项制度不被恶意利用,有必要在符合宪法的前提下为其提供法律依据。唯此,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能真正“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死”。
链接一:报道泰利案时,中国媒体使用了“安乐死”概念。但此案与法律意义上的安乐死无关, 而是自然死亡。自然死亡在一些国家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在韩国被称为“尊严死”。安乐死与自然死亡的区别在于,安乐死是指为了减轻进入临终状态患者的痛苦,通过注射药物等措施使患者安详结束生命。自然死亡是指对没有任何恢复希望的临终患者或植物人停止使用呼吸机、进食管和心肺复苏术等治疗手段。
链接二:“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志愿者曾于2006年开展过一次关于“生前预嘱”的调查。在历时4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重庆共发放1200份印刷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98份。
调查结果显示,谈论死亡和临终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居民中已不是禁忌,绝大多数人合作;目睹过亲友临终不良状态的人能更积极看待临终,回答“谈论死亡,安排临终,生命尽头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问题态度更积极;医务人员和信仰佛教的人比一般人更愿意谈论死亡,听说过“生前预嘱”和愿意继续了解“生前预嘱”的人比例较高;想象过自己临终的人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医务人员比例略高于一般水平;想象过临终的人更愿意自己做决定,填写“生前预嘱”并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接受“生前预嘱”的主要障碍来自心理和观念,此次调查显示这种障碍似乎比预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