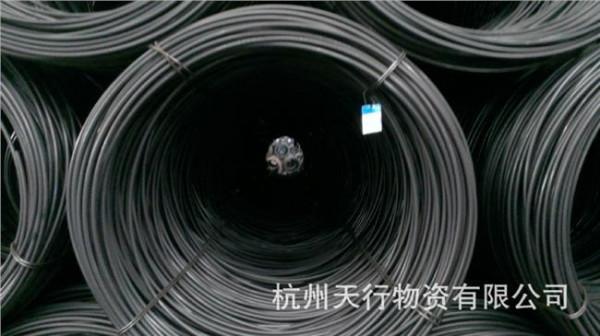梁祝陈钢 《梁祝》作曲之一 陈钢谈创作背后的故事
1958年,当时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那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每天的早报都会不断地刊登出激动人心的新闻。那年的春天有一天报纸的大标题上说“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自行车诞生了”(是永久牌的),大家都非常的激动。
几星期之后,紧接着“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小轿车”也问世了。那时全国上下充满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我国经济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作为那时的青年大学生,面对这样热火朝天的形势,我们也都是摩拳擦掌的,并思索着我们年轻人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
那时,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党支部曾组织过一些辩论,其中有个话题就是“我们的音乐创作该走怎样的道路”,当时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些从附中上来的,就像我们这些从1951就进了少年班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从部队或文工团等地方来进修的学生。
辩论会上,他们提出为什么每次考试都非要拉外国曲目,为什么不拉我们中国的曲子呢?对此,我们这些附中上来的同学都不太想得通,我们说:“外国曲子多好听啊,中国的曲子没有外国曲子好听,为什么一定要拉中国的曲子呢?”。
于是,就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辩论了好几天,其中我们讨论到小提琴作品,如马思聪先生的一些作品,有人就说:“你看,马思聪先生就是用了很多中国的民歌在里面,很好听”,然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的音乐与普通老百姓还有距离,老百姓不大能接受。
”。所以,当时就是有了一个群众化的问题,这次辩论辩论得很热闹,这也就是“梁祝”产生的大背景。
六月的一天,我正在琴房练琴,当时的何占豪同学他是浙江越剧团的一个演奏员,他是作为进修生来我们学校进修学习的,他比我们的年龄大几岁。有一天,他来到我的琴房,还带着一把琴,他把阿炳的《二泉映月》用小提琴拉给我听,还问我:“好不好听?”当时的我从来没接触过这样的作品,甚至对于瞎子阿炳还没怎么听说过,我觉得它太好听了!
何占豪拿来的是简谱,他说,你说好听,那么你今天晚上就不要回去了,你就把它配成弦乐伴奏、小提琴独奏,而且把分谱也抄好,明天早上7点半,我们同学就要来开始排练。
那时侯我还很想不通,不解的问:“为什么让我写?我从来没有学过作曲呀!”何占豪有点半开玩笑的说:“那我不管,因为你父亲是作曲家嘛!
”后来我才知道,可能那也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刘品同志的意见:“你就让丁芷诺去弄,她大概行的”。我那时还是蛮听话的,好象我就没有推脱的理由。那晚我真的就没有回家,就一直在钢琴上摸着曲子找感觉。
那时,虽然我学过一点和声,可是似乎也用不上,我就是凭着自己的一点感觉在钢琴上摸,摸了第一段以后觉得还可以来一个大提琴和小提琴有对位的声部,那么我就这样写了一下。那一晚我彻夜没睡,终于按何占豪的要求写出了也写完了,然后又把分谱也抄好了。
第二天早上,同学们都来了,我就很起劲,带着他们排练什么的。大家都觉得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兴趣都挺高。正当我们很起劲的时候,我的专业老师赵志华走过教室,他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把我叫了出去。
他问我:“这是不是你搞的?”,我当时很害怕,以为老师要骂我不好好练琴而去搞这些事了,我就硬着头皮点了点头说:“是的”,没想到赵老师过了一会儿竟然说:“非常好!”他一说这话,我们都非常高兴。
那时候,何占豪同学对写总谱还不是十分熟悉,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给我指一下,由我来完成。因为那时阿炳原来的曲调可能有6段,何占豪只选了其中的4段,总谱基本上都是我写的。
后来,等到作品完成以后,当他写署名的时候,他总是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而我写署名的时候我也总是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我想,虽然他当时没在五线谱上落下一个音符,但是这个创意还是他的,他不来找我,我是不会想到把阿炳的《二泉映月》写成小提琴的。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认识水平,对这种民间音乐的了解也是很不够的,我们都很尊重对方。这首作品演出后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好,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舞,我们又接连搞了几个。
当时另外一个叫王维一的进修生,他是个北方人,所以他搞了一个河南梆子叫《梆子风》,也是找我来配的器,还搞了一个小乐队的《早天雷》等,我很高兴的做完了。搞完的时侯正好是7月1日党的生日,我们就把这三首曲目作为给党的生日献礼曲目拿出来。
当时那个“献礼”的场面非常热闹。也有人做了一把提琴,也有人做了一个竹子的谱架,还有各种各样的献礼礼物。我们这三首曲目当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我觉得后来是我们的党支部,特别是书记刘品同志,看到何占豪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人物,觉得他很有创作上的才能,于是就建议在管弦系成立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当时这个小组由何占豪、我、朱英、张欣等,最初还有王维一这么几个同学,专门探索小提琴民族化的创作型小组,小组成立日是当年的8月9日。
又过了一个月,我们的作品已经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那时侯,我们也很激动。那时我只有19岁,当时我和何占豪开玩笑说:“咱们这个事不得了,连出版社也来找我们要求出版我们的乐谱,电台、电视台都来找我们去录音、演播了”。
后来我们还出了唱片,一下子弄的很热闹。特别是当那些谱子出版的时候,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印刷体,都觉得很高兴。
当时我们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也都很自豪。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这个小组也就形成了一种分工,我和何占豪主要负责创作,朱英和张欣主要搞理论研究,还有沈西蒂和后来的俞丽拿主要是担任演奏方面的工作。
这个事情我们在何占豪的带领下干得很起劲,我们还经常在一起去学习民间音乐,一起去上海的豫园城隍庙观摩江南丝竹,又去看甬剧、沪剧等各种地方戏,吸取民间音乐的营养。
这些对于从小受西方音乐熏陶的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崭新的天地。当时有件事很打动我,我们有几天几夜的辩论,有位进修班王蔼林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我记不得了,他总的意思是说只有民族化才能在世界上被承认,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如俄罗斯的强力集团,他们具有民族的特征才能被世界所接受。
在理论上就总结了我们那次的大辩论,特别是她最后有一段话说:“我们这一代学生中有的很有才能,为什么不把你们的才能和你们的精力贡献给创作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的事业当中去呢?为什么不投身到这个当中呢?”这篇文章当时我看了以后,我确实是激动的。
因为像我们这样从小学习音乐的学生,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学了音乐是为了什么?好象我们的印象就是学音乐就是为了考试,考试就为了有个好分数,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建立过一种信念,也没有想到我们能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应做出些什么贡献。
通过这次辩论和读这篇文章让我很受教育,特别是使我们这批人头脑中建立了这样一种全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事业观,这篇文章还启发了我要为事业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决心。
1958年底,学校组织了六支“六边”活动的小分队,我们就去了浙江队。这支队伍主要是由管弦乐的一部分学生,有声乐系的一个小组,还有个别作曲系的同学共同组成,其中陈钢就是作为作曲系的同学和我们编在一队里的,我也曾跟陈钢一起去采风,到浙江的少数民族的山里去听他们的那些民歌。
当时所谓的“六边”活动,就是边演出、边创作、边采风、边劳动、边学习、边宣传等。那时,我们经常一起去演出活动的内容和任务主要是慰问解放军部队,那个时候的交通也很不方便。
记得有一次,我们从上海坐船,坐了两三天的船到了温州,然后坐车一路上来,经过黄岩最后到了宁波。我们在去温州的船上我们的实验小组就开了个小组会,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提出,该拿出怎样的一部作品来向国庆献礼?”的话题。
那时我们都是一直就有一个心愿,很想写一部大型的乐曲,或者是小提琴协奏曲。在当时讨论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着,记得何占豪已经写完了一首“小梁祝”,最初就是个“弦乐四重奏”,何占豪当时就提出来:“我对越剧的曲调比较熟悉,如果在我的“小梁祝”的基础上写成一部大的协奏曲,我觉得可以考虑。
”我们当时也都觉得蛮好的,当时也有人提出来,现在国家整个都是大跃进,所以就应该写“大炼钢铁“,也有人说应该写个“全民皆兵”的题材等。
最后,是由何占豪给院党委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实验小组经过讨论,拟订了三个题材,其中“大炼钢铁”、“全民皆兵”,最后是“梁祝”。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是孟波同志,他看了这三个题材后认为:最接近、最适合小提琴协奏曲的题材就是这第三个题材,即“梁祝”。他说,梁山伯祝英台是比较有希望的,特别是何占豪对越剧非常熟悉,于是,他就把“梁祝”圈了起来。
之后,他还责令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刘品同志从上海专程赶到温州来看我们,要具体落实这个协奏曲的创作。刘品赶到温州后就直接跟何占豪住在了一起。
他只来了一天,时间是很匆忙的,何占豪当时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其实他的自信心和专业能力都不算很强的,他虽然提出来可以搞“梁祝”,但在这么大的任务面前,真要是干起来他的自信心也是不足的。我觉得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工作做的非常细致,也很落在实处。
刘品还和何占豪睡在一起,热情的鼓励他说,我看你行的。我很佩服刘品工作的细致周全,作为一个领导,刘品不断地鼓励他,他说,你就把你所熟悉的越剧都唱给我听,我们再来共同分析哪首可以做主题,哪些可以怎么样等等。
于是,何占豪就一段段的唱给刘品听,刘品也听的很投入。那晚,他们讨论的很热烈,也很晚了,这样就大大的鼓励了何占豪一番,毕竟当时刘品是党支部书记,何占豪还是个学生嘛。
那天他们谈的很兴奋,结果,何占豪谈着谈着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何占豪一觉醍来时,刘品已经悄然回去了,他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们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还给他留下了一些橘子什么吃的。
后来,何占豪就找我一起弄“梁”的初稿,我们开始时用的这个主题是现在发展部的一个旋律,因为他最先是想学门德尔松的开门见山的开头方式,结果效果并不理想,大家都觉得不是很满意。
最初我们是一起搞的,那时候,我配配弄弄还可以,但是一让我碰这种大型协奏曲,我觉得还是蛮吃力的,觉得自己难以驾驭这个题材。于是,我便跟何占豪说,这个梁祝真的要创作的话,还是应该找个专门搞作曲的来写,我说,我们俩都是拉小提琴的,特别是我对越剧也不熟。
当时刘品也有这个意思,他看了我们写出的“梁祝”乐谱,觉得还不大行。于是他就直接提出了可不可以让作曲系的陈纲同学也一同搞,对于这个建议我们都同意了,何占豪当时也同意了,并去找了他,可是陈钢说他当时正在准备来年的毕业作品,好象就没时间参与这个创作。
直到后来,我听说这个事情是通过领导反映到孟波那里,于是孟波找到了我父亲(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和作曲系教授),因为陈纲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希望由我父亲去说服陈纲。
我父亲当时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支持的,他说服了陈钢,说毕业作品没关系的,你要完成了这个作品,就可以算你的毕业作品了,于是,这个创作组合就这样形成了。
从那时后,陈刚、何占豪都是每个星期都到我父亲那里上课,每一次都是先由何占豪写出一段旋律,陈钢就给配一段伴奏,他们经常在一起商量。我记得他们当时商量最多的是,怎么能够让大型乐曲通过故事情节和曲式结构当中的统一达到完美的结合。
过去的小提琴协奏曲都是由不同情绪的三个乐章,这个作品根据故事情绪的发展,好象用单乐章还比较好,这一点我父亲也是作了肯定的,他认为这首乐曲可以采用奏鸣曲曲式,但采取单乐章的形式来写,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下来了,但在最后部分,民间故事是讲梁祝最后是化成了一对蝴蝶,他们在要不要“化蝶”的问题上曾产生过困惑,主要是担心会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而被反对。
但在这一点上,孟波说,我们讲革命,不能只讲英雄主义也要讲浪漫主义。
化蝶完全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境界。所以这个内容也就作为了一个再现部保留了下来。于是,那段时间里他们两位就在那里全力以赴的投入了“梁祝“的创作,一直搞到了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