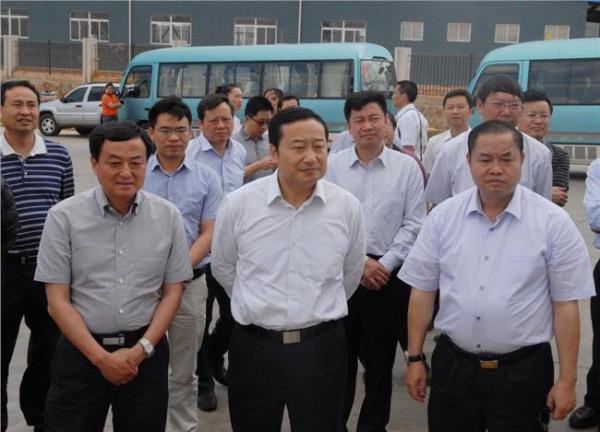张祥龙笔记 张祥龙教授现象学讲课记录(完整版)
为什么说科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切中对象的问题?这个要想透。当年我记得胡适先生讲“哲学要关门”——贺麟先生告诉我他们那时候在北大哲学系同事,贺麟先生搞黑格尔哲学,比较“形而上学”,胡适说“你们这个都过时了”,像这类哲学——他根本就不说“这类”,就说“哲学就要关门了”,以后用科学、用我们的工具论(就够了)——但是,对于胡塞尔不是的。
很多人说胡塞尔跟海德格尔相比,胡塞尔是“科学型”的、海德格尔是“诗人型”的,很不一样。
尤其是现在喜欢胡塞尔的,对海德格尔都是痛加挞伐的,海德格尔“悖师”呀(怎么怎么),其实不是。其实他们俩人,你看,胡塞尔是“科学”的,但是他有超科学的一面:(比划黑板)从这儿开始。那海德格尔后期讲“诗”和“思”,他的最基本的思想都开始“超科学”了;可是他前期一样讲逻辑,他的博士论文、那个什么“教职论文”都是跟逻辑有关的,也是从逻辑起源。
怎么讲呢,讲哲学作为一种“原本的科学出现”——也是怎么讲出来的。
所以这是现象学的特点。现象学就不像比如说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一上手已经“超科学”了,或者“超”得比较容易、“超”得比较艺术化。这儿可不是,这儿要一步一步来。问题在那儿?问题是按照胡塞尔的看法,你那么去“解决”——你通过讲了很多的经验过程来告诉我我怎么“看见”了一个东西,你这个回答完全不等于回答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你说这个“脑子里神经受损害就看不见了”,但是问题是(要说)“看不见”,你脑子的神经没受损坏你也可能看不见,对吧?所以“受损害”并不是你“看不见”的唯一的原因,实际上有很多原因让你“看不见”:光线亏了你也看不见(等等)——这些都是经验上的,有各种各样的“看不见”的或者“看得见”的条件。
这也是胡塞尔说这没有真正的回答——我们下面以后慢慢把这个问题再弄清——“如何可能”——难道你的视神经健全你就一定看得见吗?不然。所以你没有回答“如何可能”。所以这时候的你,用那个东西来以为你“回答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被漏过去了。
(提示翻到第7页)这个《讲座思路》里头它说“自然科学对认识可能性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它不是关心的“认识”如何可能,它关心的是这个东西如何能够解释——从生理学上或者什么上——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的实验室的条件下你能够“看得见”中的一个条件、或者是几个条件,它在追究;但是对认识如何“看得见”的根本问题,它是漠不关心的。
这是经验的一面。另外的一面是比如说柏拉图,他来回答我们的认识如何可能或者是康德的回答:他认为有一些“先天”的东西保证了我们认识的可能性——先天的“观念”、先天的“理念”或者先天的“形式”;但是我们看:先天的形式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之外的事物呢?康德想了很久。
我们先讲柏拉图最简单的一个情况。他说因为先天的东西不是我们直接能经验到的,我们经验到的是个别的东西——但是康德说我们经验个别的东西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以某种方式已经分享了先天的理念,所以“这个东西”才能对我“出现”。
那这个“个别的东西”如何“分享”了永恒的东西呢?这他又说不清了。或者是用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没有说清,所以后来有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批评——你总要再预设一个第三者,来使得这两个(东西有)连接的可能。
这个第三者和“我的认识”又如何能联系上呢?——再加一个第三者;所以“无穷后退”,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最原本的问题已经又被漏过去了! 上次我还讲到,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是最敏感的,他说你不能靠“分享”这种说法,来讲有一个原本的、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毕竟预设了最原本的,比如说“桌子”的理念,(板书)使得我们看见的世界上所有的桌子都通过“分享”它,来被我们“看见”。
他说这个东西你如何“分享”它?你又要假设某种东西在中间等等等等;亚里士多德说:不,我就要就这个“个别”来看到这个“永恒”,所以他说我要找到“个别的形式”,它叫“其所是”——“透、梯、艾恩-阿伊那艾”,这是古希腊文;(英文是)what make it is——或者就是(德文的?)“佛-艾斯汀-梯-艾斯汀”——那个“使得它是它”的“这张桌子的”那个独特的本质。
这是一个提得很深刻的问题,是一个现象学的问题。
“这一个”桌子怎么能对我显示我能看得见“它”?“我看见了”——(当然)在他看来人能看见的只是它的“形式”了,但这个形式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不是一个普遍的、被它分享了的形式。但是他怎么讲清楚这个“其所是”,而且是在“个别的东西”的其所是——实际上就是“个别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没有真正讲清楚。
讲着讲着一下把这个“其所是”就讲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形式”。最后这个“其所是”成了一个“纯形式”,没有一点质料的“不动的推动者”。
所以这是,我说实际上这就是像“摁住跳蚤”的一种问题,这个“跳蚤”就是这个问题——“如何可能”的问题、“如何认识它”的问题。它是特别根本——你一旦认识到它,它——怎么说呢,按照胡塞尔看来,——下面要讲哈——你应该能够“直观”到它,你不能靠“推”,你一靠这个“推”——哦,它“分享”它——你“分享”,怎么“分享”啊?个别东西怎么“分享”它?!
哦,我靠它分它的其中一部分?靠它“分享”了全体,(“yueyinwanquan”,听不懂)?柏拉图后期自己都意识到这是荒谬的。
比如说这是个“大桌子”,它这个桌子的“大”,为什么它是大的呢,因为它分享了一个“大”的观念;分享“大”的观念?可是如果我只能分享它的一部分、只不过能分享它“大”里面的一个“小”的观念,这个“大”只分享了一个“小”,它居然还成为“大”怎么怎么的——你只要搅到这种事情里头,就是说里头你能搅出来很多很多的自相矛盾的或者是很麻烦的东西,永远解决不了的“往后退”东西。
——这里某种意义上我预设你们有某种哲学史的功夫,但是我现在不要求,尽量把它讲得让你们能够理解。 所以传统的哲学,它也在追求一个“万物的本原”,或者这个地方叫“认识的本源”,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到近代以后慢慢的它就合成一个问题了。
尤其到现象学,你所说的“万物、世界的本原”实际上是你如果认识不到,这也说不上是万物的本原。你不能设定,你怎么认识到你认识的本源,使得认识——如果你脑子里这个东西能够切中了一个对象,尤其是科学的——不是你胡思乱想?这个问题相当于一个“幽灵性”的问题。
而传统的哲学认为自己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了,甚至像康德这么聪明的人,他的科学革命的,用哲学的革命性的东西,在胡塞尔看来除了他走在现象学道路上那一小部分,也还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演绎”那一部分——康德也漏过了它。
所以在第10页倒数第一段,胡塞尔讲传统哲学它对于这个问题是一种“问题的推移”,推来推去最后总不能“切中”、“命中”。
打个比方,传统哲学去追求它的那个方式、它的那个力量,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掩盖了或者挡歪了、挡开了,就像水中月你去捞,一去捞,那个月亮就碎了。这个我就不多讲了,要讲可以有很多很多讲的。
所以这里边对胡塞尔来讲,主要还不是一个“找确定性”的问题。传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哲学)它倚重科学,科学能找到一些“确定性的真理”,我哲学里也要找“确定性的真理”——而且到胡塞尔这儿他还是要找“确定性”的,不会错的——当然(这是)我替他解释,而且我觉得胡塞尔这个意思也在这儿——光“确定性”不够。
数学是不是确定的?2 2=4;逻辑学是不是确定的?A不能等于非A;毫无疑问。
但是这个“确定性”,1、我说它无法直接针对认识论的问题来说话,它没有涉及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毫无疑问!2、如果你想把这种确定性的关系移到认识论的问题上,主体认识客体,比如通过我刚才说的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你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本源的唯一的答案。
这些我刚才都讲了,就不重复了。 所以胡塞尔在这儿要讲的就是,好像表面上一个很简单的“我们不预设任何东西的存在”。你想,他就是想通过这个——人,你先不要预设它的存在,也不要预设这一边你的主体的存在,而是说让它们——“这个东西”的存在和“它”的存在以及尤其它们的关系——当场对你“显现出来”,你才算真正“切中”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我们这一讲里,25页第二段,他讲:“这种研究……但哲学却处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一种全新的方法。
” 好了,这个问题我想就先点到这儿,以后我们碰到它具体的例子慢慢再回来消化。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地方肯定还不能算讲透,在这个阶段。
下面我们主要是逐渐看他认为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所以我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他的一起手处它有一些东方哲学的味道。这一点他本人是不是意识到,我也弄不清楚,但他有的地方甚至他都提到(板书)某种“神秘的东西”,而且是以肯定性的口气提到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用禅宗一句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要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任何推论、任何靠预设某些东西的存在都失效。
你要像你饮水一样直接体验到这样一个“切中”的事态和关系。这样才算进入到了现象学的态度。 这个地方一个重点就是,传统西方哲学号称都是“反思”的,都是说“你们平常大家不意识到的前提,我去探讨”,这一点到了近代简直是无以复加的被强调了。
尤其是到康德这儿,都是要探讨“认识的前提是什么”、“认识如何可能”。我说了他这本书受到康德的影响,但是呢,他认为他是超出了康德。他把康德的问题以一种“超康德”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在一个重心,就是说他对于“如何认识到”——他强调的是“直观体验”,而不再是像康德这样“反推”出,从我们认识到我一定要反推出我有先天的认识形式:“感性形式”、“知性形式”,再有一个“先天的统觉”。
我要靠它们的什么一起的、合作的这种运作,然后产生一个“现象”——推出来的,不行。只有(板书)“当场看到的”、“直观到的”才行。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看来讲的还是比较快,可以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