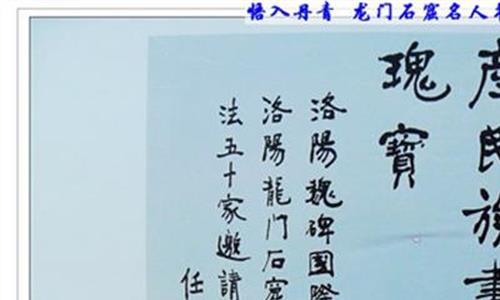前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宁谈父亲:不后悔被定为林彪死党
2011年9月4日,北京举行九一三事件40周年文史研讨会。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 、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多个单位的学者和独立学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真相,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甚至心理诸多层面进行学术探讨。在这次研讨会上,九一三事件时任空军副参谋长兼党办主任王飞的儿子王鲁宁,介绍了他父亲的情况和想法。王飞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被隔离审查,1981年获保外就医。虽说是一家之言,很有参考价值。
林立果的“小舰队”:那个词本来是开玩笑
我也没准备,原来就以为空军的几个子弟聚一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有一些话现在还不好说,还不敢说。但是我想有一些事,既然是这种座谈,也想说一说。
我父亲王飞九一三事件时是空军副参谋长兼党办主任,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这些人的直接领导。我九一三事件时在部队,是武空13师飞行员,是运输机的副驾驶。
我听到传达的时候感情肯定跟在座的不一样,因为这些人都是我身边的人,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叫着周叔叔、叫着小于叔叔,叫刘沛丰是刘叔叔,就这样长起来的,他们怎么变成了什么“十恶不赦反革命”,要“谋害毛泽东”什么的,简直不可思议。我对这些人的印象,跟大家听到传达文件是不一样的。像林立果1967年从北京大学入伍到空军以后,当时我只知道空军来了一个挺能干的吕秘书叫吕果,我们以前听说、后来也听到一些情况,都是说很平易近人,很有一些进取心,愿意学习什么的。当时我父亲觉得不好安排他给某一个首长当秘书,所以说就让周宇驰带他,叫“一帮一”,让他们组织一个调查研究小组,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跟他说部队里边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你们先去调研一下,查一查前因后果,提出一些改进方案什么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什么“新三军”、“老三军”斗争比较复杂、比较激烈,他在当中都见识到了,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我父亲讲,“小舰队”那个词,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就是党办这些人在一块聊天吹牛的时候一句玩笑话,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核心力量”、“核心组织”了。当时西郊机场有两架飞机要上广州,后来就是凡是上了飞机那个名单的,就都是“死党”了,当时就是这么给框的。
按这个框,我父亲因为正好是林立果他们的顶头上司,所以说给他定“林彪死党”—他觉得也不冤,确实他跟这些人很熟悉,这些人想搞一些什么,他说我都听到了,或者说我也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跟他聊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九一三事件、这些人实际上应该分成两块,黄吴李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可能是对林立果他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些事情确实是不知道,是被冤枉的。
我的感觉,像周宇驰、于新野、林立果他们那一块,经常通过调研小组发现一些问题,通过自己认真思考分析,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指向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后台是谁?一目了然。
“不解决毛泽东,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
所以说这些人最后的仇恨—当然我说的“仇恨”也是一点一点地认识—就觉得不解决毛泽东,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就认为“文革”就是中华民族的……那个时候“浩劫”这个词没出来,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要想制止这场灾难,那不得不采取一些现在认为不可思议的行动。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可能就是在他们几个人当中出来了。
我们也是跟我父亲聊天聊到这个事,他讲《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他都没见过,是在进了学习班以后,给他看那个影印件他才知道。他一看完这个,说我相信这个肯定是真的。于新野的字他很熟悉,另外平时说的一些话,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些内容都说过,所以他认为是真的。但是这个里边后来讲到什么要谋杀毛泽东之类,这个问题,他觉得肯定林彪不会知道这些事情,黄吴李邱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像空军吴司令员在九届二中全会被批以后,很多事情上边都那么关注了,底下的一些事情怎么还敢向他汇报、对他交待?不可能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算是给黄吴李邱一种解脱,他们实际上没在一块。
我父亲卷入九一三事件,比较关键的就是因为周宇驰在直升飞机被迫降以后,撕掉了手里的两张纸,一个是林彪手令,一个是林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信,那个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说“有事可与王飞面洽”。我父亲进了学习班以后,人家也是死追这封信:你跟黄永胜最后怎么“面洽”的?你向黄永胜交待一些什么任务或者什么事情?
我父亲讲,林彪这封信也是他后来进了学习班以后才知道的,事先他并不知道。“手令”他说也不知道,我说那不可能,我听传达文件,里面有你写的“王飞笔供”,都由你亲笔签字的,你的字我也都认得。他讲,他说的有一些内容是不得已,当时纪登奎、郭玉峰给他讲这些事、让他写这个“笔供”的时候,起码是跟他说了八九遍,他说跟小学生听写似地写了“笔供”。里边有多少不实之词我就不说了。
我父亲1981年以后,就算离开秦城了,身体恢复得比较好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他骑车来到钓鱼台,到国宾馆门口时,我说:“你看,那就是钓鱼台,文件上说,你也承认,你当年和关广烈来这里看地形,要组织空司警卫营的人来这冲中南海。”我父亲来回看了半天说:“哟,我今天才知道钓鱼台在这。”他说根本没来这勘查过地形,也没有要冲中南海。当时就是一说,后来任务就解除了,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文件里确实有不真实的地方。林立果他们所谓的“小舰队”和老一辈黄吴李邱是有区别的。公审时老的都说,我们都没这些事,一无所知。
毛真正害怕的是林彪,更害怕林立果
我想毛泽东对林彪是比较害怕的,林彪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死活不检讨,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反毛的错误。底下黄吴李邱,毛泽东压得很厉害,他们又是从小跟着毛泽东搞革命起来的,都是很听话的。所以毛对黄吴李邱是不害怕的。
毛真正害怕的,一个是林彪,一个是林立果,更害怕的是林立果。林立果很年轻,不受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你管得住吴法宪,管不住林立果。当然毛泽东也想管住林立果,我曾问过豆豆大姐,当初干嘛给林立果找对象选妃搞得那么大张旗鼓,现在老百姓一提都非常反感,很愤恨。
她说,就是毛泽东提出来要给林立果找对象,林和叶才害怕了,赶紧说空军谁有合适的,赶紧给找一个,千万别用毛泽东给安排的那个儿媳妇。林立果调研小组成立以后,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应该说他们顶多到叶群那儿,叶群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共同蒙蔽了林彪。否则不可能叶群接周恩来一个电话,就那么仓惶地上飞机了。现在的谜团简直太多了。包括刚才张大哥(张清林)说的李文普那一枪。
我问过我父亲,他那时思维还清楚,他说九一三事件事情出来以后,他正好在指挥所,他说飞机走了以后,他们几个人轮流看着标图员标的航迹线向李德生汇报: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李是周恩来派他到空军的。我们的雷达因为有限嘛,出了国境以后飞机就消失了很长时间,雷达就搜索不到目标。
我父亲就跟李德生讲,现在雷达全程开放,能不能除了值班雷达开放,其他雷达就请示关机了。李德生说,我不懂你们空军的事情,像你们自己的事情该管就管,这种事不用向我汇报。
我父亲听了这种话以后。就还想听情况,就像贺铁军刚才讲的:空军截获了一个情报,因为间隔时间比较长了,递上来时,三分情报变成一份情报了,就是:“大型目标入侵;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
”我父亲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在目标消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后,情报就传上来了。别人可能不太清楚飞机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我父亲说他都猜到了,他说林彪一家包括林立果都在飞机上,这个飞机在天上就着火了,然后就坠毁了。
他就想象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情况转给李德生。他把这个情报就退给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他说既然李德生说了,你们空军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就不用事事都请示。这件事就等于给瞒下来了。后来中央文件编的故事说,飞机迫降爆炸起火。我父亲讲,他心里很明白空中已经着火了,空中着火了以后,飞机才迫降的。
林立果和同伴不是凶神恶煞的法西斯分子
林彪的飞机为何会空中着火?到现在我和我父亲聊天时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看到资料、看到书,最可能是两种:
一种是这飞机被人做了手脚。—“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被炸时,安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微型炸弹,只要把油箱炸开,在油箱附近,这个飞机就得着火。当时“克什米尔公主号”因为是在海上,就让它慢慢自己烧着,或者在哪个岛上迫降,或者让它坠海。有的资料说256号飞机在山海关加油当中做了手脚了,所以在天上就着了。
再一种可能,从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有可能是驻蒙苏军用什么武器,比较轻型的地对空武器击落的,或者是一个霰弹的碎片碰到飞机,正好碰着引擎就着了。
我问我父亲哪种可能性最大?—只能说是“可能性”,他不置可否。
对于九一三事件,我想说两点:关键人物,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不是凶神恶煞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当时和周宇驰在一块,他很年轻呵,周是党办副主任,穿四个兜军装,他穿两个兜军装,他们俩骑着摩托车到处去调研。人家只知道他是个司机或者是个小兵,跟着首长,去为首长服务。到哪去安排什么活动,他不愿出头露面,都是往后闪。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现在讲他,都以为是提着手枪、凶神恶煞的那种人。周宇驰也一样,面目弄得也是凶神恶煞的模样。50年代末,周宇驰是刘亚楼的秘书,永远是笑眯眯的,一笑两个大酒窝深深的。而且这些人都很能干,能文能武,开汽车,开飞机,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是周宇驰写的,就发表了。我父亲说周宇驰是唐山乐亭人,全村最穷的贫雇农,40年代参军。
于新野8岁就在上海当共产党的交通,最后填档案,何时参加革命工作都没法写,最后填了个12岁,最后到了部队。
刘沛丰,跟着飞机走的那个,我父亲说,刘沛丰刘叔叔那是解放前的正牌大学生啊,很有本事。给我的印象,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文武双全。他们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除了谋害毛泽东那种提法有些过于残忍,其他的那些分析都是比较准确的。
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想说受九一三事件牵连和影响这个事,波及面太大了,对军队和党的工作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当时我在13师,武汉的部队,也受空军九一三事件的影响。一个13师运输机部队,应该说不受什么影响,我们的师长、政委全都给抓起来了。师长王宏志(音)是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在牡丹江跟日本人学的九九高练的第一批飞行员,开国大典驾驶运输机C46通过天安门检阅的驾驶员,是开辟拉萨航线、飞跃天险的功臣,在青岛抓起来了,拿白布单子给他一蒙,手枪往后腰眼一顶,扣上手铐就抓起来了,从青岛押回武汉。
我们师政委郭学师(音),就因为过去是刘亚楼的秘书、和空军的人关系比较熟,也就被捕了。从副师长到团级以下干部,包括我当时是训练大队,从大队长到大队政委,所有的人全都关起来了。当时叫“学习班”,现在应该叫“双规”,四五个人陪一个,然后门口坐一个端冲锋枪的战士,守着你那间房门,不许进不许出。我们部队很快陆军接管,连我们大队都是陆军,政委都换成陆军的人。我们师在湖北,调来高炮17军,跑道两头都是,只要飞机起飞降落就瞄,当时只要搞演习,陆军马上就跟你对着干,挖战壕,马上枪对枪。把空军和陆军搞得对立成这个样子,要是擦枪走火,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这些部队战士的基础都是一样的,海陆空军都能认得老乡,最后陆军部队与我们关系非常好,也成了“兄弟部队”了。当时这种部署和安排,用心是比较险恶的。
九一三事件牵涉的人实在太多,太不应该了。像我父亲被牵涉进去,那没的说,觉得给他定“林彪死党”,他自己也不后悔。他1975年、76年就被从卫戍区转到了秦城,他也很绝望。贺部长也被送到秦城,后来听贺部长讲:“我进秦城,听见监狱有人在大喊大叫,我一听是王飞,哦,我不孤独,秦城不是我一个。”后来我问过我父亲,你在里边喊什么呀?人家那都是些小战士,你就不知道给人留下个好印象?您就不能表现得文质彬彬一点,有风度一点?我父亲说,实在是不行,在里边我的监号可能是在最后一个,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政治犯。政治犯伙食有一定标准,应该是不错的伙食,结果到他那什么都没有了,汤汤水水就递过来了,他表示抗议,结果那个小战士说:“你是反革命,给你这些就不错了!”我父亲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亲手活捉过日本鬼子,你懂什么呀你!”
我们每个季度可以到秦城看他一次,他后来已经不是正常人了,身体非常虚弱,走路、说话都不行了。
1981年7月底。公审林彪和“四人帮”之后,王飞专案组来找我们,说把他“保外就医”,让我们四个子女签字,我们不愿意签—我们在北京没有家,没有住的地方。他们说,你们只管签字,没地方住,我们代表中央,给你们安排一个地方。一个星期之后就出来了。他说出来和进去都感到非常突然。专案组通过海淀区在西三旗给安排了一间农民房,房租我们自己出。
我父亲他们这些人很悲惨,不许叫自己的名字,保外就医化名“王玉”,否则还不让出来。只有叫王玉,药费才可以报销。后来我看贺龙当年也化名王玉,送火葬场,骨灰盒上写着。我问公安部:你们是不是只有一个“王玉”的化名,谁倒霉就安在谁头上?
直到1994年,总政给军委打了一个报告,要把我父亲交给空军。当总政来人和我父亲谈的时候,我父亲说:我王飞就是王飞,绝不叫王玉,你们爱叫什么叫什么吧,我以后一定叫王飞的名字。现在好在他恢复了王飞的名字,否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军委给他一个批覆,安排三居室的一套房子,每月300块钱,看病在空军总院,按照军人团以下干部待遇,免费治疗。三居室安排了,在南苑,很远,不方便。三百元一直到五、六年前,调到一千块钱。他现在床上吃,床上拉,风烛残年,没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保姆市场上,照顾这种人,月薪不低于三千块钱,我们为了提高他的待遇,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写信,提要求,得到的答覆是:“已经处理,不再处理”。
我父亲只是九一三事件受牵连中的一个,现在连对逃荒要饭的、打工仔,报纸都要呼吁提高人格尊严,送温暖,但是九一三事件这批人枪林弹雨做过贡献,又有谁关注过?我父亲已经四次脑出血,人已经不行了。我想呼吁,还有一大批九一三事件的受牵连者,应该改变他们的处境,给以人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