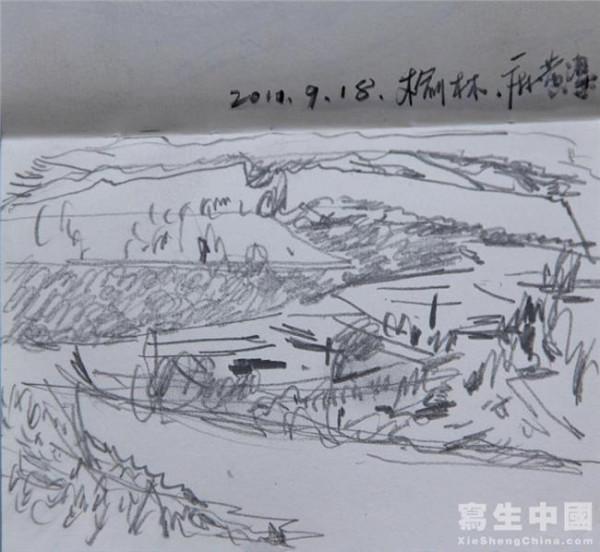杨福东的影像艺术论文 影像艺术家杨福东:不再妄谈乌托邦
[ 杨福东(微博)刻意削弱作品的叙事性,以支离破碎的剪辑和非线性叙述营造出远离现实生活的虚幻境界 ]
理解杨福东的影像叙事,是一个缓慢而悠长的过程。播放室是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黑暗空间,墙上悬挂了十块投影屏,没有座椅,挤满人群,悄无声息的压抑;屏幕上浪头涌动,悠长的小号声划破黑暗。屏幕上,两个年轻人,试图在浪花拍打沉船的过程中找到逃生之路。
没有对白或旁白,甚至没有剧本。在长达19分钟的影像中,你面对的,只有画面上油画般的色彩张力,奇异、梦幻,甚至是流露出的某种神秘主义情调。但能清晰地看到,这对画面上的年轻人,在交流理想、憧憬,以及面对死亡时的挣扎与信念。
这是近日在北京香格纳空间杨福东个展上播放的影片《靠近海》。是杨福东在国内首映的两部影片之一,另一部名为《等待蛇的苏醒》。
凭借优美而感性的图像,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杨福东成为新锐一代中用影像叙事的佼佼者。批评家们说,杨福东的作品反映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与日益匮乏的精神世界时所感到的困惑和失落,以及他们对自由的追寻。
杨福东是敏感而细腻的,语句清细,带着偏寓一方江南小文人的调调——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出身北方部队大院里的汉子,竟沉迷于营造各种烟波湖面、江南竹雨、断桥残雪的极致美感。
杨福东的电影刻意削弱作品的叙事性,以支离破碎的剪辑和非线性叙述营造出远离现实生活的虚幻境界,他的镜头,记录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城市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所感受的疏离。目前,杨福东是国内最炙手可热的影像艺术家,参与过卡塞尔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等多个重要展览。
“人物风景画”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你很重视影像的背景音乐,并且把每个演奏者也各自以一个单屏幕的方式录进你的整个装置电影作品中,让人身临其境,这些音乐对于理解你的影像是否有帮助?
杨福东:这片海,我是找了舟山附近的一个海滩。那边可能一天两次潮起潮落,不同季节不一样,这种味道让你很感慨。《靠近海》从创作上看是有讲究的,音乐上,潮水的潮落配合着管乐的变化,尤其是后半段,有小号的吹奏。
我们都是在下午偏黄昏的时候去海边录的,所有的声部是单录的,而且都有指挥。我们日常所看的影像有一个很大的迷惑,套概念的时候,它是影像,但很多人关注的是内容,不会考虑内容之外的东西。因此很多导演都是第一部电影很出彩。之后他可以拿到很多钱,剧本可以更多地维护外围的评论,过多关注于剧本反而让他失去了对影像本身的把握。
日报:国外评价你的影像,认为具有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怀,而你的影片关注点,也大都是城市里文化青年在城市中的迷失和自我赎救。
杨福东:我不会给自己扣知识分子的帽子,也不会强调这个。我更觉得我的作品有一些精神生活的考虑,跟知识分子文化的气息有所靠近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有些意思的。乌托邦是很理想的,让人憧憬的。我不可能再妄谈乌托邦。
现在很多人在夸夸其谈,但你需要实实在在的存在,要实实在在思维,要还原真实的自己。比如我2006年拍《断桥无雪》,断桥残雪是很漂亮的风景,下雪之后还没化干净,是冷。但断桥无雪是暖,是一种期待,这里面偏重文字的气息。事实上,我更多是讲述可以化为风景的一对男女,有点类似人物的风景画。
日报:你的影像,没有对白或旁白,伴随着支离破碎的叙述,给人感觉有些神秘主义。
杨福东:我不是刻意想把它神秘化。你拍的东西,你期待的东西,最后形成了所谓的带冒号的神秘感。所有的这种期待,或者你呈现的神秘感,无非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东西。你要呈现出来,那肯定很有意思。艺术表面的链接,可能什么都不考虑。一个人坐出租车很晚回家,你可能就在想这个事,然后这个事可能就真发生了。思维的链接触点是不确定的。但你的所思所想是一种潜意识的存在,它推着你往前。
日报:用十个屏幕来呈现你的故事,和用单屏来呈现,有什么不一样?
杨福东:多屏跟单屏是殊途同归。所谓的录像艺术或电影,就是放映方式的区别。艺术电影就用这种媒介做的电影。潜台词就是,电影是娱乐产品,作为精神消费产品。这时候艺术家希望用影像这个媒介,做一些个体化的自我阐述,呈现他理解的东西,或者是一群艺术家用这个东西去表现。
这里面,就会相对区别于作为一个产品的出现。比如我拍的《离信之雾》,它是空间电影的概念。在其中,艺术家的自由度和发挥的程度,往往不同于电影院里放映的单屏。所谓的多屏,也不在乎你屏幕的多少。而是对空间关系的考量,基本框架的安排。
看不见的剧本
日报:你走向成功而为国际熟知的还是《竹林七贤》那部系列片,为你赢得了很多荣誉,你拍了五年的时间,每年拍了一部,有没有回头想过,当时为什么要那样拍?
杨福东:拍过了,不会去想,事实已经发生了。再给我5年,我会拍另外一个七贤。有时候你都不太了解你自己。对未来,这种不了解,会很有意思,它会让你有所期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但不是和过去说再见。这是最重要的观点。接下来拍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对我很重要。当你准备拍的时候,大致的结构、大致的方向都已经定好了。随着时间改变,细节会改变。中国现实发生的内容会影响你看不见的剧本。
日报:你的电影中的时间维度很缓慢,现在人们看到你的电影,就很容易把它归纳为“杨福东的电影”,你现实中对于时间的衡量也是如此?
杨福东:这是时间的跳跃。时间的跳跃每天都有。你睡了五分钟,外界看就是五分钟,但是你在睡梦中可能已经去加拿大玩了一个月了。看你自己的定位,哪个维度。是以人为标准,还是以人站在山的旁边为标准,看你要不要给自己找参照。只有生老病死是在客观的维度上的。
日报:你的敏感形成了画面的细腻唯美,这种敏感对于你现实题材的展现,究竟起了多少影响,并形成你现在的风格?
杨福东:敏感的东西,是不经意间从身边飘过的东西,没办法抓,你千万别苛求,这东西你一苛求就麻烦了。艺术家作为个体,应该更有生活和觉悟。有些东西实际没有好坏大小之分,只有生活的内容、方式、环境不一样。艺术、艺术品、收藏,很多人谈艺术的时候,反而觉得艺术不重要了。尤其这几年,有些过分了。那些有钱人,你觉得他们投资艺术,他们真喜欢艺术吗?很多房地产商投资足球,他们真的爱足球吗?
日报:如果让你给自己的影像下个定义,你觉得什么才是影像?
杨福东:看着有点像虚词,不靠边,包含了数字、网络平台、技术革命之后的一些观念更新和理解。未来代表了一个方向,另一个可能是很意会的,就是很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方法,比如竹子不仅是竹子,而是代表了情志。我将来也许会用到绘画,绘画是影像。
现在有个词叫草图电影,我可能勾画一个人的线,它有个思维的电影框架,给大家呈现一部电影。这是属于电影前期的一部小电影。有的时候我也会画一些复杂的东西。摄影我也不会放弃,图片和摄影是在一个画面的。所以还是有很多东西去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