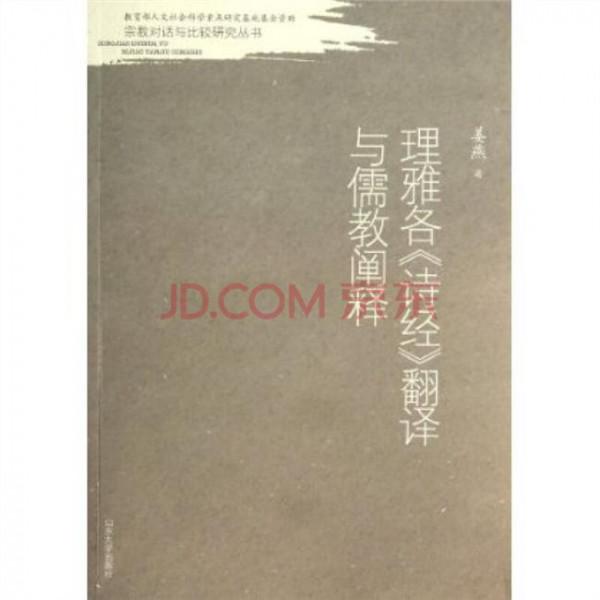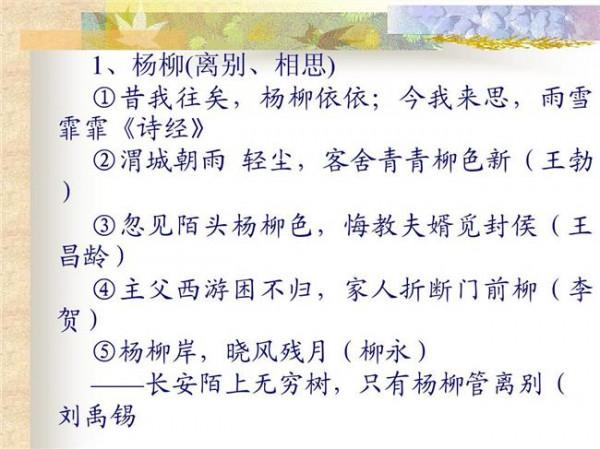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歌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有哀与乐吗
【核心提示】具体到《采薇》一诗,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证明“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的艺术理论,则有以今人之意强加诸古人的嫌疑。
《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有谢安与侄子谢玄讨论《诗经》中名句的一段内容:“谢公(谢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玄所举名句出自《诗经·小雅》中的《采薇》。
《采薇》以退役归来的士兵回忆和追述戍边生活的口吻,多层次、多角度地描绘、展示了军旅行役之苦。最后一章写戍卒回家途中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其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因借景抒情、以景衬情、情融于景,充分体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成为千古绝唱。
历代品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者络绎不绝。在评论者中,王夫之《姜斋诗话》“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评价,因新颖独特,广受称誉。然而,《采薇》最后一章并非以“哀景写乐”。
“今我来思”的背景是“雨雪霏霏”,征人留给读者的背影是“行道迟迟”,征人的生理感受是“载渴载饥”,征人的内心独白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整个末章,除了悲哀之外,何曾有半点快慰和欣喜?因此说,王夫之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云云,并不完全符合《采薇》末章的原意。
《采薇》一诗的征人在归家途中的心情是沉痛的,“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对照《木兰诗》中木兰回家时的“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欢乐景象,后人可能很难理解《采薇》中的征人何以对归乡没有丝毫的欣喜。
和中国古代许多小说与戏曲一样,《木兰诗》不但具有传奇色彩,同时也有着大团圆的格套。现实生活中,像木兰那样幸运地凯旋而归,受到天子封赏,而且有亲人在家伫立等候,毕竟过于理想化。
《诗经·豳风》中有《东山》一诗,内容也是写征人归乡,其中有“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描写经过战争的蹂躏,农村屋宇破败、耕地抛荒的景象。从《东山》的内容来看,征人也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几句为途中所见。
沿途景象如此,家乡是怎样的情形呢?“妇叹于室”、“洒扫穹窒”为征人悬想之辞,“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看着沿途萧索的景象,“不可畏也,伊可怀也!”因惦念家中的亲人,征人回家的心情显得很迫切。
《诗序》:“《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东山》中有“于今三年”之语,与《尚书大传》所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相符。《诗序》对《东山》时代背景的解释,当属可信。周公东征,后方应该还算稳定,《东山》中的征人对与亲人相聚尚抱有希望,故悲哀低徊之情较《采薇》为轻。
《汉书·匈奴传》:“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猃狁患周,非止一世。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宣王即位后的前十年,不但与西戎、猃狁开战,五年(前823)秋八月方叔率师伐荆蛮,六年召穆公率师伐淮夷,宣王亲征徐戎,等等。
宣王之前,厉王暴虐,国人暴动,厉王被放于彘,王位匡绝14年,国势已经是每况愈下。再经宣王连年用兵,农村破败当远甚于《东山》所述。
《汉书》认为《采薇》作于懿王时,魏源《诗古微·小雅宣王诗发微》将之定为宣王时诗。无论《采薇》产生于懿王时还是宣王时,总之当时的社会已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征人实在不敢想象回家后看到的是怎样一个情形了。
一同被魏源《诗古微·小雅宣王诗发微》定为宣王时诗的还有《出车》。《出车》作战的对象也是猃狁,采取的也是车战形式。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出车》中有这样的句子:“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征人回乡的时间与《采薇》完全相同。
关于出征的季节特点,《采薇》说是“杨柳依依”,《出车》说是“黍稷方华”。有人以为“杨柳依依”,时间当为春天,其实未必。古人折柳送别,主要取其依依之貌,春夏秋三个季节都适合折柳表情达意。
那么,《采薇》中的“杨柳依依”具体指的是什么时间呢?《史记·宋微子世家》载《麦秀》之诗,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中原地区的小麦抽穗期一般在农历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上旬,抽穗后2—6天开花。
据《麦秀》诗,此时“禾黍油油”,黍稷尚未开花。但既已“油油”,离抽穗开花当亦不远。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黍稷》:“(黍稷)种以三月为上时,五月熟;四月为中时,七月熟;五月为下时,八月熟。”约略推算,四月播种的黍稷,于六月前后抽穗开花。依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述,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伐猃狁至于太原,这个时间符合《出车》描绘的“黍稷方华”的物候特点,自然也是《采薇》“杨柳依依”所描述的时间。
先秦有一件不其簋,上面的铭文也记载了与猃狁的战争。其铭曰:“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朔)方严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汝御追于,汝以我车宕伐严允于高陶,汝多折首执讯。戎大同从汝追,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我车函(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
"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诲(敏)于戎工,锡(赐)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不其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用丐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
”不其簋铭文“来归献擒”与《出车》告捷献俘的内容相同。不其簋,据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讲,其年代是周宣王八年。铭文记载了班师回来封赏的时间为“九月初吉戊申”。征人还乡的时间,《采薇》说是“雨雪霏霏”,《出车》谓“雨雪载途”。《豳风·七月》有“九月肃霜”的句子,则九月封赏事毕,征人还乡途中,正是“雨雪霏霏”、“雨雪载途”的时节。
在《采薇》一诗中,作者并未像后代诗人那样,有意识地分哀景和乐景来抒情,虽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确具有“以乐景写哀”的艺术效果。六经皆史,《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出车》中的“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今我来思,雨雪载途”,忠实地记录了宣王伐猃狁出征和归来时的季节特点。王夫之“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的说法,无疑是具有辩证思想的艺术理论。然而具体到《采薇》一诗,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证明“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的艺术理论,则有以今人之意强加诸古人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