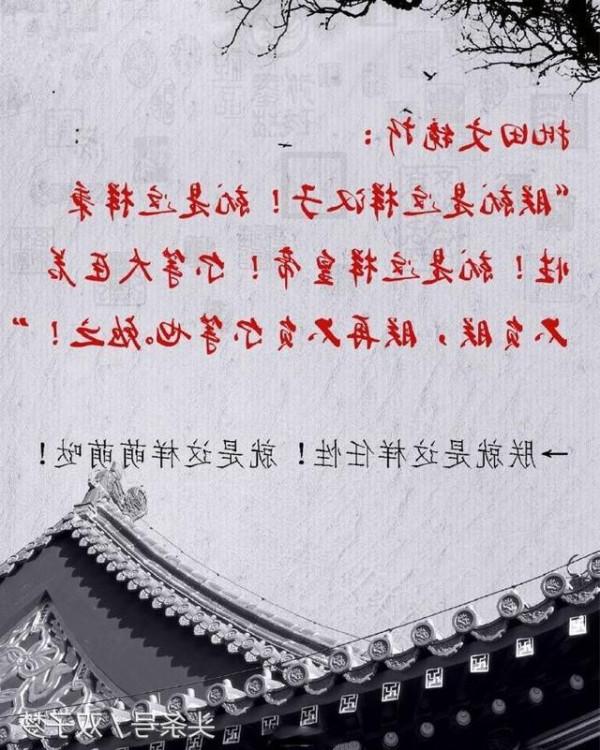黄声远田中央 黄声远:“田中央”的赤脚建筑师
如果说伊东丰雄是以东京为自己建筑的试验版图,安藤忠雄是以大阪为自己建筑的试验据点,那么台湾建筑师黄声远则是以宜兰作为自己建筑理念的尝试舞台。1994年,台北人黄声远只身来到了宜兰,从礁溪林宅起步,开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生涯。
结缘宜兰
作为土生土长的台北人,留学耶鲁大学,并在洛杉矶Eric O.Moss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过,像大多数出身于这个含金量极高专业的年轻人一样,黄声远开始了日夜颠倒飞来飞去的生活,为大都市设计它们的摩天大楼。但他很早便知道这并非自己所欲。
1994年,宜兰县政府与仰山文教基金会发起了一个推动"宜兰厝"的活动,希望与建筑师一起寻找一种适合当地气候条件和景观特色的现代民居。宜兰位于台湾岛东北部,盛产稻米和葱蒜,北回归线穿过此地,在北宜高速开通前,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化失乐园里最后的故乡。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宜兰贯彻着"文化立县"的发展策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对其与环境的调和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声远
黄声远敏感地觉察到,在这里他可以做的正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他刚从国外来到宜兰,日本的象集团在做冬山河亲水公园,让黄声远觉得台湾的公共工程是有机会做好的,有一种曙光乍现的感觉。因为之前台湾的一些知名建筑,比如国父纪念馆,都需要与高官政权有关系。但是在黄声远的时代,就变成了要为大众服务的建筑,这让他产生了莫名其妙的使命感。
黄声远喜欢在宜兰观察动物、植物,观察老建筑和老地址。他觉得这种观察就像一首民谣,将居民的心愿,凝聚成集体对未来的想象。他心中的田园生活,应该有足够的留白,能让每个人过自己的生活。他觉得一个地方的幸福应该是大合唱。
我们不难看出,宜兰礁溪户政事务所,梅津栈道都似乎凝聚了黄声远本人心目的田园生活风光。值得一提的是梅津栈道,作为一条依附在旧桥之下栈桥,它刚好能够支撑不太宽的桥面栈板,最狭窄的地方,只能供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经过。栈道的围栏种满了花草和藤蔓植物,在灯光和水汽的滋润下,植物不需要人养护,可以自由生长。踏上由钢隔板和木条铺成的桥面,一低头就能清晰地看到脚底下的河水,颇有一种"水上飘"的感觉。设计师最巧妙之处是在桥的中央设置了一处供人休息的平台,需要弯腰穿过旧桥底才能进入,是不是有种小时候进入秘密基地的感觉?头顶是苍茫的蓝天,脚下是潺潺流动河水,在桥的两侧靠近桥墩部位的地方,吊着几个秋千,孩子们在上面挥霍着童年,美的像一个遥远的梦,却又真实存在着。
"田中央"的田园生活
很难得会有一个建筑师将自己的团队起名得如此充满乡土味,"田中央工作群"是黄声远设计团队的名字,也是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场所的生动描绘。这个事务所坐落于田地的中央,"我们刚刚在宜兰工作的时候,经常就坐在稻田旁边讨论和开会。"黄声远这样描述,"熟悉这里的环境很重要。我认为要做好一个地方的建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扎根在当地。"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扎根在宜兰的设计团队。
黄声远的家到事务所只需十分钟的路程,田中央工作群一般只有车程在半小时内的工作。这样,他们可以随时赶到现场与当地使用者讨论,随时发现不妥就修改。工作起来严谨而自在。
黄声远经常的装扮是一顶斗笠、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一双拖鞋,所以被人称为"赤脚建筑师"。放弃了外形的束缚,工作更显方便自在,在施工时很多设施都鼓励年轻人亲力亲为。提到田中央工作群的生活状态,黄声远介绍道:"大自然可以教给我们更多。我们工作室中午饭后会自己处理食物残渣,我们乐于做些农事,比如尝试过收割稻子。在水灾后年轻的同事主动积极支持,做些专业规划,同时学会了解水。"
面对日益成为流水线机器的建筑业,田中央工作群做建筑就显得太慢了。建一间普通的住宅,其他人大概花一年,他们愿意花六年的时间。对此,黄声远这样解释:"我一直怀疑效率这件事情是把多样化变成单一化,我们想以手工艺精神面对当代材料,从而培养出一个因为慢所以多元化,因为慢所以能了解的城市。还好甲方了解后也认同,我可以慢慢把事情想清楚,慢慢修改。"而这样的架构一旦掌握住,黄声远的目标是,能够面对数十年的变化有能力调整,与时俱进。
在田中央工作群,他们并不把自己做的建筑看成所谓的项目,而是将其视为整体生活背景的铺陈活动。"项目是有工期,有限制,有始有终的。而环境的改造如果进行得不顺利,就先停在那儿,暂停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别的事。其实在这里个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紧迫,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有特别大的压力,如果是对的事情多数总有一天会再动起来,这段多出来的时间一边修改方案,一边再找经费。"黄声远这么说,田中央工作群通常是在停工的阶段,找到了更完善的想法,在修改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挣扎,慢慢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仔细想想,人生不也是如此么?愿意修改,才能真正面对机会。
对黄声远来说,最后的阶段性成果已经不完全是建筑师或事务所的作品,而是工匠、村民、业主所有人的安慰。他相信绝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不会特别顺利,也不会真的失败。要的就是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一直不放弃。宜兰火车站到2012年止花了八年多时间,黄声远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够按照多数公众而非少数人的想法,慢慢照顾一个环境成长,让它趋于完善。而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建筑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
心系自然的公共建筑设计
黄声远在美国期间曾供职于洛杉矶一家名为Eric O`Moss的建筑事务所,经历过专心的生活在一个小区域中,然而在去美国之前,也像很多年少有为的高材生一样生活在台北大都市,并在办公室为远在台北以外的地方设计公共建筑。但他很快便知道这并非自己的强项。"从内心里,我无法有冲劲持续这样为建筑而建筑的工作,我觉得建筑还有其他,最好不要只因为设计者常被限制的片面理解而太快地诠释周遭环境或居民的习性。如果它是一种陪伴多好,与环境谱出共鸣。"黄声远回忆,也开始四处去寻找新故乡。
这种谦卑的态度体现出了对人和自然的尊重。在黄声远看来,"农民往往比我们更懂得生命,大地中源有限,人人都知道必须做出对的事情。比如修栈道时,当地居民建议将路修得比较窄,法令上容易解释,不会有人占用,也可以让人们有机会打招呼。路灯不要那么亮,否则住在附近的水鸟会孵不出来。"
在宜兰最别具一格的建筑要属户政事务所了。整栋楼灰灰绿绿、歪歪斜斜的,各层房顶上都长了树木,走廊的扶手好像是钢筋剩料的再利用。但是不能否认,这栋建筑的可爱和平易让人会心一笑。户政所主要负责管理户籍事务,这样的一个政府机构没有选择严整而庄重,而是接受并认同如此"自然、颓败"的建筑,也许本身就传达出某种开放的心态。"做公共建筑的初衷,是营造一个谁都可以进出的空间。建筑师创造一个建筑不是为了否定日常生活的价值,不能让人进去后有挫折感,一下子变得缩手缩脚。好的设计和好的环境,其实是不造成压力的。"黄声远这样解释着他的设计。他就是在这样的点点滴滴中践行着自己提出的让行政机构和城市建筑与人友善的理念。
提到理想中的城市,黄声远这样表述,"应该有足够的留白,能让每个人过自己的生活。一个地方的幸福应该是大合唱。路要窄一点,人才会相遇;灯要暗一点,鸟才可以歇息。自由,是最窝心的生活质量,相互支持、体谅。原来,田园早已跟在这群年轻人身边"。他希望城市回到"原来"——"那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小孩可以安全地骑脚踏车,进出政府机构像出入自家后院一样方便。发生过的故事,在以后都可以找到痕迹。"
我们不难看出,黄声远对自然是一种热爱,是超乎你想象的热爱,那种热爱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上,也渗透在每一个设计作品的骨子里。他不像赖特对自然的偏执,他是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表现自然,去反馈自然。他用色彩去表现自然,他用钢铁去表现自然,自然在他眼里不仅仅只有绿地,更多的是一种人在环境中的互动,是一种将人的欢声笑语融于环境的做法。
在宜兰市,社会福利大楼一直向河边蔓延,那条梅津栈道就漂浮在环河道路上。往相反方向,旧城墙旁的杨士芳纪念林园则依照旁边遗址岳庙厢房的宽度,被设计成两栋长形建筑。就这样,田中央的建造设计延伸到历史遗产改造、河流整治、城市规划等,也包括马路街角一处旧枕木搭建的花坛。在黄声远的构想中,从生活细节往上构架的城市规划,才不会让城市一直膨胀。自由的城市可以让小孩安全地骑车,而且,以前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同时,黄声远对于建筑中的无障碍设施格外关注,"建筑物的无障碍精神可以是一种美,是价值观的呈现。如果我们觉得对任何人都接纳的感受是美的,那无障碍的设计就是指向美。我们期许自己一定要做,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付诸行动。一些体贴,其实不难,但是要愿意付出。除了关注建筑物本体,在建筑物与户外空间之间,有很多的模糊地带可以更友善,至少要做到有障碍者在有人陪同下,可以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做到无人陪同时也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更是努力的方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恺曾经这样评论过田中央:"他们的方法很有趣,不赶什么潮流,像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如果一个建筑师对自己熟悉和关切的生活环境有持续设计的态度,那是更加由衷的感觉。"
宜兰对黄声远,是一种无限包容的态度。很多人也许未曾想过在这么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里竟然会冒出如此之多充满着创意却又包含着浓浓人情味的建筑设计。黄声远说道:"创意本身需要善意走在前面,不是古灵精怪的乱想。好在我们在宜兰这么久,有社会的支持。像宜兰没有大山大水,但任何一块土地都被认真照顾,每个沟边照样种菜搭丝瓜棚,在台北可能寸土寸金却没人理你,而宜兰是每块土地都被认真经营。"
"不要怕把别人的梦想讲出来,讲的时候还得去建立别人的信任,如果我们不怕去讲别人的梦想,就真的会有别人来帮忙,如果是多人的梦想,就会有很多人来帮忙。为什么要做公共建筑,就是不晓得该帮谁的时候,就给公共,这会造福更多人,最后包含自己的家人都能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这就是黄声远最淳朴的想法,也是他做公共建筑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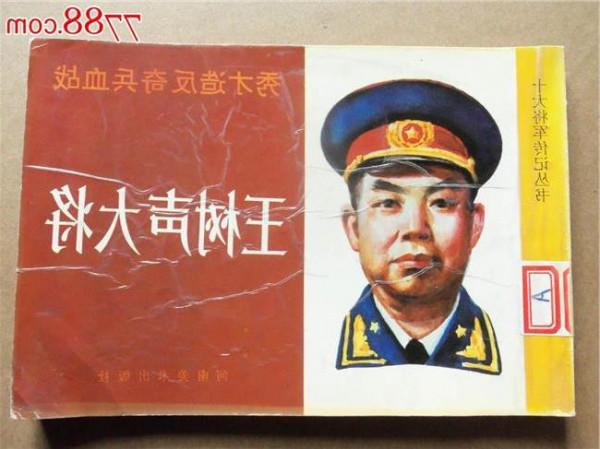

![黄声远建筑 [建筑]黄声远也许敲响了一场新建筑运动的前奏](https://pic.bilezu.com/upload/0/a3/0a30b4a87f293170d2c51c1d80c7cf4e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