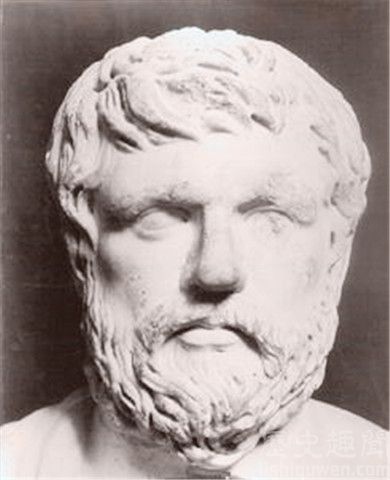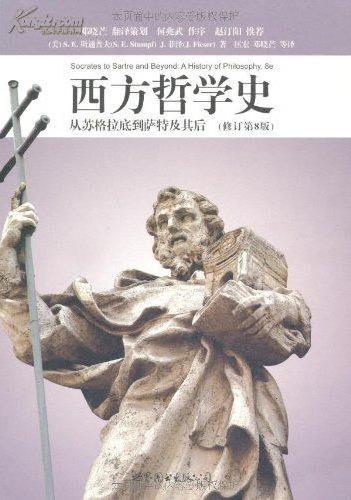苏格拉底之死引发的现代政治哲学思考
摘要:公元399年,哲人苏格拉底被号称自由、民主的雅典判处死刑,这引起了之后两千多年的争议。本文从三个角度解析了苏格拉底的死因: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动荡过后的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看法改变;不完善的雅典直接民主体制。而如何既避免苏格拉底与雅典人的冲突,又能使苏格拉底的哲学助益雅典政治?借鉴施特劳斯的智慧,“走向哲学的政治引导”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关键词:不虔敬;德尔斐神谕;话语权;直接民主体制;成年苏格拉底
一、难以在民众中普及的苏格拉底哲学
公元前399年,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在雅典状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之事,败坏青年。于是,苏格拉底被传讯,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作了著名的申辩。但申辩并没有挽救苏格拉底的性命。他最后被判处死刑。
“败坏青年”作为一项道德指责,更多的只是为了引起人们的义愤,“不虔敬”也就是所谓的“引进新的精灵”才是莫勒图斯诉状中状告苏格拉底的最主要罪名。这个精灵并不是超越雅典城邦诸神的另一位新神,正如施特劳斯指出的,苏格拉底引进雅典的不是什么新神,而是哲学的理念。这也正是让雅典的政治家和诗人等等无法接受的:苏格拉底似乎把哲学放在了比诸神更高的位置上。苏格拉底似乎真正崇拜的是“好”的理念,其用理念这个新神取代了雅典传统中固有的诸神。然而究竟什么是“好”的理念,苏格拉底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苏格拉底如何会崇拜自己不知道的“好”?
在《斐多》中谈论他的次航的时候,苏格拉底有一段关于“理念”的明确表述:“我做的是这样,我在每一次把我认为最有力的说法当成假设,凡是我认为与此相合的,就是真的存在,无论是关于原因的,还是关于别的一切,否则就不是真的”。其实,苏格拉底从不会宣称真的存在一个“好”的理念,而只是以一种假定的理念,辩证的接触各种意见,从而一一指出各种意见中的谬误。宣称有一种“好”的理念只是为主动地、不断批驳虚假知识以提升对话者和一旁青年德性而提前预设的假定。
以这个假设出发,在雅典城内,苏格拉底四处游走、演讲,成天在大街小巷和人辩论,其中包括政治家、诗人、匠人。辩论中,冲突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这也正是柏拉图“洞穴喻”中的问题:
处于洞穴之中的人,只能看到洞壁上晃动的影子,当其中一个人转过身,看到洞外的光时,他才感到影子是不真实的。当他奔向这一光亮时,后来发现了太阳之光,这种光也就是真理。这时他也就走出了洞穴中的世界。当受到了真理熏陶的人想回到洞中,告诉人们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假象,而真理之光处于洞穴之外时,他既与洞中之人产生了陌生感,而洞中之人也不可能接受他的指导。苏格拉底强调德性为伟大城邦的必要条件,企图说服雅典人按其哲学思想实践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此时,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冲突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终于,苏格拉底惹恼了雅典城内的四万公民。苏格拉底以“好”的理念对雅典人的常识发起攻击,深刻的质疑了诸神的传说、诗歌的智慧等等几乎关涉到了雅典文明的根基,妄图将自己的哲学置于雅典诸神之上。的确,这可以称作是一种对诸神的极大不虔敬,于是,满怀义愤的年轻人莫勒图斯一纸诉状将哲人苏格拉底送上了民众法庭。
二、审判苏格拉底的现代政治哲学视角:启蒙与传统的之争
公元前594年,雅典人委托以睿智闻名的贵族梭伦为雅典立法,雅典民主开始正式启程。通过废除“六一汉”制度和债务奴隶,梭伦一方面帮助农民获得了自由身份,由此奠定了民主城邦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划分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界线,这一界线对于界定雅典的公民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公元507年,克利斯提尼上台执政,其用人为地方式划分了政区,通过打破旧有的亲缘及义务关系,他构建了新的合作网络,使雅典民主体制渐趋牢固。到伯利克里时代,雅典民主已近顶峰。经过百余年的民主实践,雅典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达成了一些政治共识:他们信仰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政府,要求这部分公民积极地参与政务,并通过频繁轮职保障这一点,他们认为普通人有能力做出政治决策。他们信奉陪审团审判,他们对小团体与生俱来的腐败的恐惧,更胜于对威胁到大团体的群众心里的恐惧。他们认为城邦的稳定至关重要,在陶片放逐法制度下,将一个没有从事过任何违法行为的人流放10年是合情合理的。
尽管许多雅典人将其民主政体等同于法治,希腊知识分子有时候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苏格拉底排斥平民政治,认为应将权力交给那些真正懂得政治(拥有哲学智慧)的人去行使。其鼎鼎有名的徒弟柏拉图,更是常常将民主制视为暴政。
在苏格拉底看来,或者说是在《申辩》、《美诺》等著作中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看来,政治家们没有真正地智慧,但还是能处理好对人民有益的政事,他们靠的是中肯的意见。也就是说政治是和一种真正的智慧没有关系的职业,政治家并不需要智慧来处理政务,而这种哲学上智慧的缺失正是苏格拉底所遗憾的。政治家除了治理城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生活,而只要是生活中的人,智慧和哲学都是有益的。一个城邦如果没有有德性的公民和领袖,其政治再英明也无法塑造一个伟大的城邦。这也正是在前文中提到的苏格拉底提倡的德性哲学与雅典现实政治的冲突。
德尔斐神谕作为苏格拉底哲学使命的起点,也标志着苏格拉底哲学与雅典民主政治决裂的开始。称拥有“无知之知”智慧的苏格拉底是雅典最聪明的人,这不是在政治、军事、艺术等方面,而是指苏格拉底掌握了哲学的智慧、城邦的真谛,知道并能指导雅典人过一种经过审查后的有意义的生活。在苏格拉底对雅典人进行启蒙事业的辩论中,雅典的政治家、诗人、匠人等皆无法战胜苏格拉底,而他们或者说是在雅典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派却达成了一个共识——苏格拉底派的言行有害于雅典民主。面对雅典人近两百年所形成的关于民主政治的共识,苏格拉底的启蒙是无力的,尽管他经常在辩论中使挑战中哑口无言,但雅典人只会认为苏格拉底在诡辩或者是疯癫的哲学家。
福柯在论述知识形成的问题中谈到:“问题不在于改变人们的意识,即人们头脑中的东西,而在于改变有关真理生产的制度、政治、经济规则。”从知识的产生原理这一方面讲,苏格拉底最应该做的是去改变雅典人知识产生的规则,而苏格拉底对政治向来是冷漠的。苏格拉底派的智慧怎敌得过统治者雅典的近两百年的制度、规则,这也注定了其启蒙的失败。柏拉图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为了哲学而审判了政治,将诗人放逐,设计出“理想国”。在“理想国”中,“哲人王”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再也不会有人对哲学家产生危害,哲人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建立一个他认为是伟大的城邦。
在早已深入人心的雅典民主传统中的共识面前,苏格拉底意在促使雅典人追求更有意义生活的启蒙不可避免的失败了。
三、苏格拉底之死:作为争夺“话语权”导致的——民主派对极端异议者的绞杀
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诉讼,为什么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不能容忍思想或信仰自由?孔多塞:“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观念。”这并不是说雅典人没有自由,而是指雅典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有很大的区别。关于这两种自由的区别,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自由比较》一文中指出,在古代人那里,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的参与集体权力,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自由则表现为: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
既如此,“苏格拉底之死”这个事件是否可以解释为积极自由的雅典民主制对消极自由的剥夺?问题并没有那么明了,雅典人是有言论自由的,否则就不会到公元前399年才将已经70岁的苏格拉底送上审判席,更不会有璀璨的雅典文明,只不过雅典人的言论自由是以容忍为保证的,而不是以法律。从德尔斐神谕开始,苏格拉底便开始了他不断找人辩论以探求真知的生活。不过,随着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越来越多,还是有很多有闲的青年加入了进来,和他一起,或学着他省察雅典人,我们姑且称这个省察雅典人的群体为“苏格拉底派”。从某方面讲,苏格拉底是孤傲的,与政治家、诗人、匠人的对话让他觉得这些人的智慧不值一提,并真的相信了德尔斐神谕:世界上没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
于是他开始显露出唯有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绝对真理,并号召大家脱离现在公认的生活方式,按照他的想法来实践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方面苏格拉底犯了一个错误,没有任何生活可以宣称建立在绝对真理的基础上,人们只能一步步的前行,不断探索并试着去改变。或者说,苏格拉底陷入了建构理性的陷阱,过于相信了自己的智慧,新保守主义者哈耶克对建构理性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其是通向奴役、专制的道路,并试图以一种演进理性主义的方式将其代替。从苏格拉底的反雅典人社会生活方式的言论,再到《理想国》中所设想的共产制度、一致性生活乃至哲人王的理想,无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在其著作中加入了多少自己的思想,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路线或多或少显现着对雅典民主制的颠覆色彩。
苏格拉底在他的申辩中强调,他从未参加过任何颠覆政权的秘密集团,的确,苏格拉底总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批判雅典民主,他对政治活动是冷漠的,然而,他并不能保证“苏格拉底派”也不这样做。正如斯东先生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所说,就是在苏格拉底受审前十年多些所发生的三次“地震”,动摇了雅典的内部安全感,使得它的公民害怕起来。在这三次颠覆民主政权的社会动乱中,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中地位显赫的那种有钱的年轻人起了领导作用。三次动乱过后,苏格拉底并未吸取教训,依然以其哲人的姿态质疑雅典的民主。10终于,公元前399年,雅典人不再宽容。
正如福柯先生认为的,话语即权力。话语权给了说服甚至煽动民众的机会,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引导舆论,在民众中制造偏见,争取民众的支持和信任,进而甚至利用其力量改变这个社会的现有架构。苏格拉底不是一个人在从事这项事业,整个苏格拉底派都在通过辩论省察雅典人,倡导去过苏格拉底所声称的那种生活方式,这或多或少对雅典民主思想乃至民主体制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苏格拉底派以其哲学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与雅典现行的民主生活方式对抗,并因此导致了与主流民主派所主导的雅典舆论方向针锋相对,苏格拉底派的雄辩让雅典民主派感到了“话语权”的丧失,于是,民主派与苏格拉底便只能法庭上一较高下。因此,苏格拉底之死与其说成是“积极自由的雅典民主体制对消极自由的剥夺”倒不如说成是“作为争夺‘话语权’导致的——民主派对极端异议者的绞杀”更为贴切。
四、苏格拉底之死引起的对雅典政制的反思:直接民主体制之殇——投票中迷失的雅典城
公元前415年初,雅典人讨论是否出兵西西里。尼西亚斯陈述利弊,再三劝阻雅典人不要远征西西里。野心勃勃的将军阿尔西比亚德斯却煽动民众,通过了远征的决议。11几乎每个人都充满了热情。老者对胜利满怀信心;青年人希望开开眼界,看看远地的风光;一般人知道自己可以在远征期间得到工钱,而且,如果雅典的势力扩大,他们将会获得永久的薪给工作。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怕被说成不爱国,也就缄口不言了。狂热的雅典人最终出征了。结果众所周知,雅典人为这场被修昔底德说是到那时为止希腊城邦最昂贵的远征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是什么促使雅典人进行了这场远超出自己能力的远征?伯利克里曾经警告雅典人,扩大帝国的尝试会降低他们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但是伯利克里已经斯人长逝了,他的战略也与他一起烟消云散。伯利克里以后的领袖没有抑制民众的野心,这是远征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审视直接民主体制下的以热衷于分享国家权力为自由的雅典公民,不难发现,西西里远征和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有莫大的关联。直接民主体制下公民大会的人员构成形形色色,既有贵族、地主,也有匠人、农民等等,可谓鱼龙混杂,其中普通或者智力水平一般的人占了大多数,受于智力水平、公民素养的限制,他们在决策时常常围在几个有学识的政治家周围,其决策受政治家的演说影响极大,而面对阿尔西比亚德斯这样好战而又杰出的演说家,很难不受其极具煽动性的言语蛊惑。关乎国家命运的决策交给了这样的群体,自然免不了做出愚蠢的决策,这正是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提出扩大选举权,但又建议给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更高智力水平的人超过一票的权利的原因。
公元前407年,极端民主政治的再次错误决策将使雅典在几年后沦为二流国家。将军们赢得了希腊人之间最大的一次海战的胜利,却仅仅因为没有营救一些雅典的水手而被送上了审判席。在这一年,由缺乏远见的公民组成的民众法庭处死了雅典一批最有经验的军事家,这也注定了随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投降结尾。
公元前399年,民众法庭处死了哲人苏格拉底,这自然也和民众法庭组成人员的文化素养脱不了干系。(由抽签选举产生的民众法庭组成人员相比公民大会的人员组成在公民素养上不会有任何提高,换言之,民众法庭只不过是公民大会的简缩版,实质未变。)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对雅典民主的评价。的确,雅典城的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然而,无论公民大会还是民众法庭都难以像代议制那样实现知识和才智上的集中优势,这样的体制下的决策就很难有效避免受辩论术、群体情绪、决策时特定的氛围等因素的影响。
五、避免哲学与政治对抗的方案:浅论施特劳斯“走向哲学的政治引导”
施特劳斯在分析古代和现代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时指出,存在一个“少年苏格拉底”和一个“成年苏格拉底”。第一个苏格拉底就是以哲学和真理自居而激烈批判政治共同体、攻击城邦视为神圣的一切,而雅典日后处死的也正是这个苏格拉底;第二个苏格拉底则为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其已由鄙视政治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施特劳斯由此提出了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深刻意义就是从“癫狂的哲学”走向或返回“清明和温良的常识政治”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政治哲学”是要“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的问题。12
前文中讲到,在强大的政治传统面前,哲人苏格拉底的启蒙哲学失败了,而政治哲人也就是施特劳斯所说的“成年苏格拉底”式启蒙哲学会成功吗?
施特劳斯给出古典政治哲人的三重身份,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政治哲人的目标是最高的政治知识即“立法”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的政治哲人是立法者的导师。13因此,政治哲人在政治方面的工作是去教育立法者,教育立法者认识到本国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去完善他们的政治制度。
重要的是要去改变规则,施特劳斯与福柯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体制赋予每个参与者以权力,权力以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的形式运作,个人在这个网上流动并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这种权力制造知识,知识则又以权力的形式发挥功能,传播权力的影响。正如福柯指出,“我们也许应当抛弃这样的信念:权力造就癫狂,同理,权力的放弃是知识的条件之一。我们倒应当承认:权力产生知识;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含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14所以,知识的改变不在于放弃权力,也不在于去改变既成网络下的人们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而在于去改变产生这种权力运作方式的制度、规则。
教育立法者去审视城邦并追求更好的政制,而不是直接与政治家们对抗,政治哲人便可以无阻力的将“德性”注入了政治,使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权术的庸俗、权力的不合理运作,然后,便逐渐接近崇高的目标——雅典作为一个伟大的城邦。政治哲人的哲学成功的引导了政治,使政治拥有“德性”并趋向于“善”,这便是施特劳斯称之为“走向哲学的政治引导”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