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发的诗歌 我最喜欢的《口腔医院》等
《口腔医院》 ——我们的语言?某种遗物。 在唾弃,和它日夜磨损着的笼子里。 ——陈先发,2008年4月 “那年。婚后”,我们无法投身其中的 一次远游—— 在暴雨冲刷过的码头, 堆满了催人老去的易燃垃圾。
啊,暴雨。暴雨过去了, 昆虫忘忧, 小窗子跳出很远。 黄昏的蚌壳,旧钟表店,幼龙,尖蝝,和玩世不恭的海藻, 在我们脚踝上闪光。 凝固了的伐木工人, 他们的放肆暂时歇下。 我将为他们竖立打牌,抽烟,胡闹的雕像。
巨幅的海鲜广告牌下。问: (当你一粒又一粒地嚼着阿斯匹林, 在“牙疼即真理”一类的谶语前。) 此刻,还应期待一些别的什么? 不远处,一只黄鹂和一只白雀在枝头交换身体。 是的。我们闻到了。 看到了:就在那里。
它们大张着嘴, 喳喳地——嗓子里烧焦的檀香木, 从尾巴上跳跃着的, 几点光斑得到平衡。 而擦着鼻血的卖花小姑娘,由一个忽然变成了一群。 正好,我有闲心来描述她们的篮子。 瞧瞧这些吧: 叫人渐悟的小松枝,和 夹竹桃花的欲言又止。
戏剧性的野菊? 和百合的某种“遗址气息”。 有着恶名的银桂; 秘不可宣的小叶兰。 矢车菊的弹性,和五雷轰顶的 昙花: 虽然只有那么几秒—— 我在办公室,也曾种过一盆。
我用复杂的光线帮它们生长。 而螺旋状片片叠起的紫罗兰, 总是相信色情能创造奇迹? 还有,“不需要定语”的鹤顶红; 侧着脸像在悔过的菖蒲与紫荆…… 石斛,在这一带很少见, 为了保持形式感牺牲了香气。
有时我担心“说出”限制了这些名字。是的, 这些刚摘来,很鲜嫩。 我尚欠她们一个成年, 当盛开只为了被拒绝。 我用这死了千百次的句式来描绘她们, 写下第一句了,就等着第二句来宽恕。 宽恕我吧,浓浓的 福尔马林气味—— 当我的口腔里一个词在抵制另一个; 单义的葡萄藤,在覆盖多义的葡萄藤; 双重的傍晚在溶入单一的傍晚。
我知道这不过是现象的某种天性: 像八岁时,医生用塑料手电筒撬开我的嘴, 他说:“别太固执,孩子。
也别 盯着我。 看着窗外翻空跟头的少女吧,看她的假动作。 再去想一些词!你就不疼了”。 他把五吨红马达塞进了我的口腔, 五吨,接着是六吨…… 好吧,好吧。我看少女, 她另一番滋味的跟头。
我想到两个词是:“茄子”和 “耶路撒冷”。 当年老的摄影师喊着“茄子”—— 一大排小学生咧着雪白的牙齿。 像啣着一枚枚失而复得的指环。 我知道世上的已知之物,像指环一样都能买到。 付一半零钱,请卖花姑娘擦干鼻血。
另一半塞进售票窗口, 得到一座陌生的小镇: 在四川,一块灾后的群山里? 你捂着外省的脸。 泡沫一般的杂辞。 我整日的答非所问。 而所有的未知之物——请等一等, 如果天色晴朗, 我愿意用一座海岬来止住你的牙疼。
站在那儿俯瞰, 视线甚至好过在码头上: 檐角高高翘起的宫殿,在难以说出的云彩里。 是啊。所有未知之物正如一个人在 精确计算着他的牙疼。 谁还有一副多余的身体? 哗变了各省只留下口腔, 弃掉了附属仅剩下牙疼。
在那里。我们与模糊的世界 达成一体。 整整一个夏季,当我们在甲板上 练习单腿站立和无腿站立。 海浪翻滚的裙裾。 红马达轰鸣的福尔马林。 闭着眼。闭着嘴。 当一些东西正从我们口腔中远去。
如同, “蓝鬣蜥绝种了。而——那个词还在”。 转身,而后失掉这一切。 窗玻璃上崩溃的光,贞节的光, 伴随着气象的多变, 在这个出汗的下午。 味觉在筷子上逃避着晚餐——正如奥登在 悼念叶芝时说道: “水银柱跌入垂死一天的口腔”。
水银柱在哪儿?它纯白的语调中慢慢 站立起来的又是什么? 我们所讲的绝对,是否也像在雾气中 显出的这一株柳树在敲打 它的两岸。 哦无用的两岸引导我的幻觉。
这凭栏远去的异乡, 装满白石灰的铁驳船。小镇。方言。人物。在街上 跑来跑去的母鸡。 一样的绸缎庄,一样的蝴蝶铺。 一样盖着油毛毡的铁路局老宿舍。 一样冲动的片断和 一致的风习的浪费。 早上从瓶中离去,傍晚又回到瓶中的, 正是这些, 不是别的。
是无限艰难的“物本身”。 但我从未把买来的花儿, 插在这只瓶子里—— “那年。婚后”,当我买来一只黄鹂和一只白雀 养在雨后小山坡上。 我还欠她们一个笼子。
是笼子与身体的配合, 在清谈与畅饮中分享了辩证法的余火。 就像这不言不语的小寺院,在晚风中得到了远钟的配合。 我给你摘下的野草莓, 得到了一根搓得滚烫的草绳的配合。 我们虚掷的身体, 得到了晚婚的配合。
在山坡上。你一点一点地舔着自已的肢体。 红马达轻轻穿过你的双耳, 开始是五吨,后来是六吨…… 哦你的小乳房: 两座昏馈的小厨房, 有梨子一样的形状正值它煮沸之时, 听收音机播放南面的落花。
对于随牙疼一起到来的某次细雨, 我欠它一场回忆: 当四月的远游在十月结束, 漫长堤岸哗哗嘲笑着我们婚后的身体。 那些在语言背后,一直持弓静立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在码头上我有着不来不去的恍惚。 那么多 灌木丛中的小憩,和 长驱入耳的虫鸣。
如此清晰又被我的记录逼向了假设。 碗中的蟒蛇正引导着我餐后的幻觉。 哦,红筷子夹住的 蟒蛇和红马达轰鸣的旅途—— 当你闷闷不乐举着伞, 在雨水中旋转的街角, 迎来了一个庸医的配合。
他说:“想想看吧。这口腔并不是你的。 是一只鸟的。 或者一个乏味的圣人。这样想想, 你就不会疼了”。 “也可以想点别的。街道很安静, 一只球被踢出京城”—— 是啊我见过这样的景象: 一个乏味的圣人和一只鸟共同描述 他们面对的一颗雨滴。
他们使用了一个共同的词——不管, 这个词是什么, 嵌在他们带血的牙龈上。 这个词得到了迷惘的配合, 像你离去后空椅子的移动。 ——在枝头,两只空椅子在鸟的口腔里移动。
我的观看是为了它们的加速。 是的。我不疼了。 我看见我坐在另一座 雾中的码头上。另一场晚餐里。 另一个我可以叉开双腿,坐小树桩上 吹吹口哨, 为这二元论的蒙昧河岸干一杯。
呵莫名其妙的柳树。 莫名其妙的寓言。 对于奥登与叶芝可以互换的身体:我只欠喊它一声 “茄子”——像这些鸟的口腔 只欠一些误入其中的虫子。 这个庸医只欠一个假动作。 我的观看只欠一个小姑娘的鼻血; 这张手术台只欠一场病因。
分辩的眼睛。并非区别的眼睛。 这只眼睛看到, 一只不祥的旧球被踢出京城—— 在它的运动中,拥有身体, 不再需要新的容器了。 像一滴汗从我的耳根滑过, 在谵妄中拥有一个新的名字。
喊一声试试?瞧瞧她在 哪里应答—— 在河的对岸, 还是在一枚幽闭的钉子里面; 在骨灰盒中, 还是在三十年前某个忧心忡忡的早晨。 或者像婚前那样,迷信四边形的东西, 躲在柜子里写了一夜的短信。 用声音的油漆, 把自已刷一遍。
用胆汁把房子建成穹形,在小凳子上 摆放了形形色色的盒子。 喊一声试试?瞧瞧哪个盒子 会打开自已: 从那里找到一个词。 顺从这个词!一切由它说了算。 让我们在廉价店铺里谈论它。
在死前攥着儿子的手留下它。 并最终藏在棺材里抚摸着它。 我们发誓忠于它: 一个词。 像码头上的青年军官发誓忠于 他白癫疯的妻子。 我们愿意毁掉其它所有的词并 忠于那个盒子里的一切: 它的旧衣服。那些不可捉摸的红色。
闭着眼。闭着嘴—— 听从这个词来瓦解窗外的荒野。 听从它将幼龙变成老龙。 听从这些和解:在线与线之间; 在心电图和它的隐喻之间; 在柳树和榆树之间; 在阿房宫与水立方之间…… 随清风达成口腔中的史学, 像秦始皇完成了对美色的勘误。
让这个词告诉你我们将抵达哪里。当你寻欢的 脚步像鱼击的锡鼓 在松针撞出微小的回声。 听从这个词,像一个老妇人在展览馆里 拔着它一无所附的灰烬。 听从它在维斯康辛的白烟滚滚,当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 轻于纸张的诗句也 听从它在头顶的石榴中 传来爆裂的噼噼啪啪声。
听从其中的盐。听从这座“霜刃未曾试”的课堂。 听从它的名下之虚。
当你连说一声谢谢都很难了, 这码头在转动, 你坐在椅子上朝我眨着眼睛, 这是“忘我”和吞咽的眼睛。 当体内帘子的拂动,遮蔽了婚后的卧室。 小窗子在直觉中跳向柳树。 炊烟露出充满经验的弧形。 我告诉你这个词已经找到了—— 当我喊到“柳树”, 便有一株在某个角落醒过来。
像摆在膝上的《坛经》, 从某一页涌出了合唱。 当我喊到“蜘蛛”, 灵魂的八面体就来了, 我拒绝了其中的七面。 像一幅画着墙的画挂在墙上, 里面的门仿佛从未有人开启。
当我喊到“花儿”, 花园卡在了我的喉咙中, 这包含了椭圆,路线,和单音节的悲悯。 因为讲不清的原因,我们在交换着身体。 我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三个词。 是别的一些什么东西。
是另一座码头上,你的踯躅和植物性的悲欢。 在“那年。婚后”—— 当小瓶子只容得下两具啼笑交集的身体。 我们所追逐的词将回到那里。 我会放弃说出,口腔里堆积的 那些名字。那些机体。那些过时的谎言。
在全部的硬币涌出瓶口之前。 我要的不是一次苟同众议的婚姻,当 我手中的鞭炮需要满街的鞭炮来否定。 我虚无的牙疼在 找回那个词像小姑娘 卖光了花儿后放下她的空篮子: 当一群又恢复为一个。 这是绝望的哲学, 也是清新的雨滴。
远游中我崩溃过一次, 也仅仅承认过这一次。 我知道我爱的并不是你—— 我一个人在暴雨后的锯木场闲逛着。好吧, 我知道有“某个东西”: 不管它在哪里, 我将一直环绕着它。由它来宽恕遭遇它的人们。
在杜冷丁一样口腔中。在杜冷丁一样的夜空下。 从未有过完整的柳树。 我曾经那么害怕它的完整, 如今我受够折磨, 再也不用怕它了。连同一旁的田垄, 新长出的瓜果, 也已不足为惧。 从未有过红马达。
当语境的口腔医院在我的口腔中建成。 从未有过晚餐: 谁又能像这 盘子里烤熟的蟒蛇 一样做到物我两忘? 从未有过故乡。 孔城:江淮丘陵的一个小镇。 四月的孩子在青石板上玩着亚麻色的 螃蟹、老龙和旋木桨。
他们将一直 玩到秋天:我不在其中。 这本身就是一场拒绝。 但从未有过拒绝。在它嘈杂的街道上, 我走过了,却没有力气再走一遍。 那些老竹竿搭起的狗肉排档上, 夜间赌酒,吸毒的少女, 从不谈起自已的父母和姓名, 只给我们摸一摸她刺了靛青虎头的腹部。
从未有过另一个人—— 让我在公园长椅上醒来时变成他。 当啤酒中捷足先登的岛屿, 混合着夜里越来越稀少的鸟鸣。 从未有过一堵墙。 脸上写着“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 二胡从它的背后探来, 带给我一个声音。
一个满月的声音。 一个老女人在旧皮箱里整理儿子遗物, 小溪水顺着她的脚踝攀登的声音。 我们从这个声音中穿过去的 声音—— 从未有过“下岗工人”。
当他们的80年代全部用于在废墟中 寻找自已的女儿。 从未有过他们的煤油灯。 和一毛三分钱一斤的早稻米。 从未有过穷人的天堂。 也从未有过我的目的地。 当我对它的一无所求演变为 诙谐。
并对这种诙谐有了不可抵御的憎恨。 从未有过一种语言练习, 可以完成那屈辱的现实。 从未有过挖苦。 从未有过鲁迅。 从未有一封信。它写道: “我造出过一只笼子。从那里飞出的 鸟儿永远多于飞进去的鸟儿。 从那里出生的女儿, 要多于背叛的女儿。
她们的口红。她们绷得紧紧的牛仔裤。她们的消化器官。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在家里总是难以隐身”—— 从未有过这个家。也从未有过放置这封信的角落。 从未有过窗外葡萄藤和 它们体内歌唱轮回的乐队。
从未有过历史。 从未有过秦始皇。 当他在带箭的车辇上豪迈宣告了 万物的臣服, 宣告了锯齿状的墙垛和群岛的逶迤, 宣告了神秘的珠算。 从未有过更远的世界,当蓝眼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他们对别人疆域的征伐, 必须由失败者记录下来。
从未有过镁光灯的频闪, 当你喊着“茄子”,那些骨灰盒中的脸, 沉淀在硫磺冲洗的底片里。 从未有过浮云, 从未有过斜塔。 从未有过孔雀。
为了开屏寻找那恒定的观众, 她必须依赖主题公园, 长出一年三熟的丑脸。 从未有过一种远游,像 空气中的高头大马, 当她绕着树干大叫三声, 树下的僧侣走向了圆满。 从未有过“田纳西州”和“陶渊明”, 当他们结出的篱笆是瞬间的,山巅, 坛子里的晚霞再也不能安慰你。
从未有过一个词是我们这双手的 玩物, 当你找到它。你知道了, 它也从不是我们这颗心的玩物—— 从未有过“那年。婚后”像 我们并不信任的医生一样, 当他醇练的手术在某个早晨消失, 我们的口腔如何才能不辜负, 那偶然闯入的天赋…… 从未有过对立。
也从未有过和解。 从未有过一把必然的椅子在我死去后, 能如此长久地这么空着。 连此刻的喘息它也再记不起。
2008年5月 《街边的训诫》 不可登高 一个人看得远了,无非是自取其辱 不可践踏寺院的门槛 看见满街的人都 活着,而万物依旧葱茏 不可惊讶 2001年9月 2005年6月 《青蝙蝠》 那些年我们在胸口刺青龙,青蝙蝠,没日没夜地 喝酒。
到屠宰厂后门的江堤,看醉醺醺的落日。 江水生了锈地浑浊,浩大,震动心灵 夕光一抹,像上了>铿锵的油彩。 去死吧,流水;去死吧,世界整肃的秩序。 我们喝着,闹着,等下一个落日平静地降临。
它 平静地降临,在运矿石的铁驳船的后面,年复一年 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垮了。我们开始谈到了结局: 谁?第一个随它葬到江底;谁坚守到最后,孤零零地 一个,在江堤上。屠宰厂的后门改做了前门 而我们赞颂流逝的词,再也不敢说出了。 只默默地斟饮,看薄暮的蝙蝠翻飞 等着它把我们彻底地抹去。一个也不剩 2004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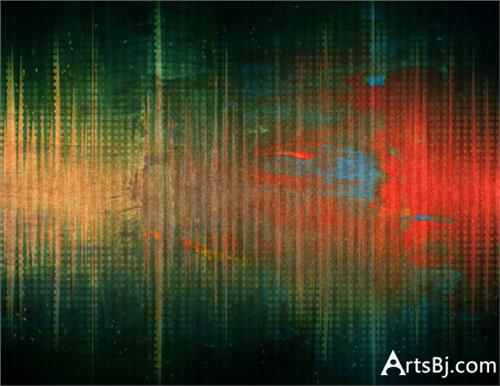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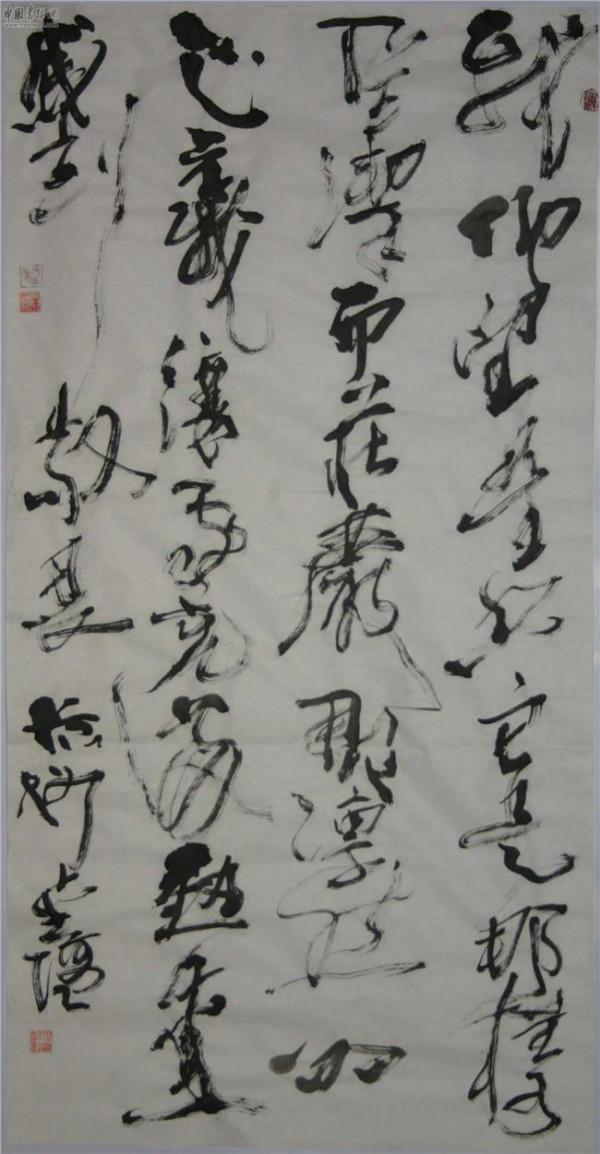
![>陈先发诗选 [诗歌]陈先发诗歌选萃之一:](https://pic.bilezu.com/upload/c/36/c3636de9701fa2ad312d6402cb8e2e76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