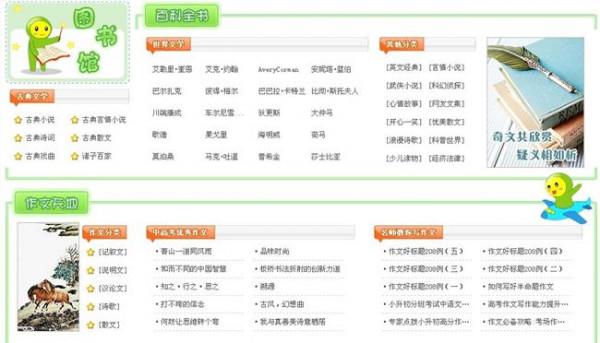舌头乐队朱小龙 舌头乐队为什么令人如此怀念都市快报
当年崔健在北京是不能公开演出的,他也是舌头现场的常客,有一次被问起怎么看舌头这支乐队,他回答:“你看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了。”——他们的眼神都像刚刚从熔炉里出来的刀子。
文 张晓舟
舌头乐队为什么令人如此怀念?为什么他们的重组复出在微博上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响?
或许这正说明最近十年来的中国摇滚少了一点什么。这十年我也喜欢不少乐队,但我几乎再没重温过类似世纪末和世纪初(1998-2002年)的舌头乐队那样令人迷狂的现场。前不久和杨海崧(P.K.14乐队主唱)聊起来,他说他迄今为止看过的国内最佳现场,一次是舌头,一次是木马,都是在十几年前。
舌头乐队在吉他手朱小龙回归后目前集结于丽江排练,准备复出和录制新专辑,一个月前我和李志、张玮玮在丽江见到他们,还相约六月中旬去杭州西湖音乐节看他们的演出。张玮玮和李志在早年还没正式搞音乐的时候,都是舌头的铁杆粉丝,张玮玮每周必去一次五道口的开心乐园,充当舌头的剖狗(pogo)党徒,而李志说当年他只知道狂听平克·弗洛伊德,直到看了舌头的现场,才知道吉他可以这么弹。
现在西湖音乐节也邀请了李志,他正好在舌头前面演,两个时代终于可以干一杯。
很多当年舌头的乐迷后来成了乐手,我问过好几位对当年舌头现场的感觉,都是说:危险,甚至说:有点害怕。这首先是时代氛围,当年的摇滚乐手可没有匡威鞋铅笔裤,没有炫酷T恤,没有文身,天一热就光着膀子,皮带上还挂着一大串钥匙,而乐迷也差不多都是那一副操性,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摇滚屌丝共和国,不,屌丝不能用来形容当时的世纪末铁托,不是屌丝,而是吊死——用北京土话来说就是所谓“死磕”,在压抑,迷茫和绝望中爆发,而舌头引爆了这种暴烈的情绪。
当年崔健在北京是不能公开演出的,他也是舌头现场的常客,有一次被问起怎么看舌头这支乐队,他回答:“你看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了。”——他们的眼神都像刚刚从熔炉里出来的刀子。
舌头的现场有时候容易引发意外,比如打架(我就在舌头现场打过一次架),以及pogo受伤(2006年舌头重组那次在杭州就有两个人因pogo摔伤了腿)。但是光用“狠”或者“狂暴”,远不足以形容和解释舌头的现场,他们从来不是简单的愤怒,也不只是单向的批判,吴吞歌词的特质始终是反讽与抒情的合一,而其他乐手即使在疯狂乃至病态的情绪间歇,也不乏甘美,清澈而出神的时刻。
比如朱小龙具备典型的摇滚吉他英雄的特质,但他那些貌似简单的旋律动机和音色有时候更令人难忘,他十几年前曾经也是左小祖咒的吉他手,假如没有那段二两拨千斤的悲怆的吉他solo,《苦鬼》这首歌几乎就不成立;现在在舌头新版的《喀什的天空》(原来是吴吞个人作品)中,他中间的一段吉他solo完全呼应了“当一条河干涸的时候,它会停在喀什的天空”的意境。
舌头从来不只是死磕,而是灵魂出窍。
木刻版画家刘庆元十年前在广州看过舌头演出后,刻过一张画叫作《放养者》:一个戴草帽的农夫举起镰刀收割,而下方是一群默默低头的人。刘庆元认为这就是看舌头时,人们应有的姿态:默默低下头。这不是膜拜臣服,也不是盯着脚丫子自赏,而是像成熟的麦穗感受到灵魂的重量,而向大地俯首。舌头不只是让人雀跃,让人飞翔,也让人低头。
十年过去,如今吴吞又戴上了草帽。与其说这是怀旧,还不如说他一直在前方等待人们赶上来,站在那里,像一个时代的宠物。
有很多乐队令人激动,但很少有乐队既令人激动,又令人感动。究竟少了点什么?在信息超载情绪爆炸技术膨胀的这十年,或许中国摇滚乐少了一点饥饿感和一点赤子情怀。这十年,摇滚乐变得花枝招展,而当年的舌头犹如光秃秃的树,从地平线刺向天空。
十几年前在树村,吴吞住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准确地说连屋子都不算,只是一个简陋破旧的小隔间。一张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烂沙发,一坐下去会陷进一堆烂棉花里,一张小木床,床上一把贝斯,而墙上——四处贴满了涂写着诗句的纸片……
(张晓舟:著名乐评人、专栏作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