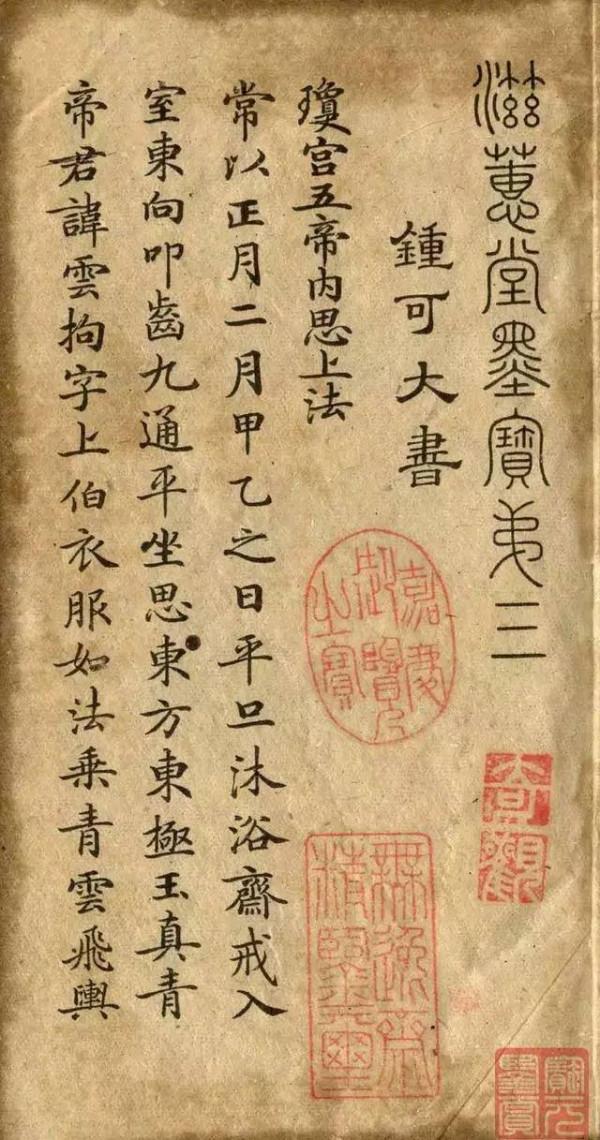上海人李劼 老上海人:苏州河北岸是“浜北” 曾代表褐和黑
拆迁后的浜北人,像盐溶入水一样,融化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李其纲常常在想象,他们现在在哪里,继续着怎样的生活;也常常在思索,他们的精气神最终会给这座城市添加些什么。
老上海人管苏州河叫“浜”。以苏州河为界,北岸是“浜北”,主要在普陀境内;南边叫“浜南”,后来泛指黄浦、静安、长宁等区。
浜北有三道湾、一条浦。湾是朱家湾、潘家湾、潭子湾;浦叫彭越浦,当地人叫“大洋河”。大洋河畔有个平江村,1954年,李其纲就出生在平江村。
多年后,李其纲在小说中这样描写自己出生的这片区域:“补丁接补丁般的棚户密密麻麻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地拥在一起,足有十华里见方。”
——朱家湾、潘家湾、潭子湾、平江村、药水弄等,连绵一体,人称“三湾一弄”、“三湾一村”,正是上海历史上最集中、最出名的棚户区。
浜北棚户区的形成并非偶然,其直接成因更与吴淞江有关。
吴淞江发源于苏州吴江,蜿蜒进上海后得名苏州河,最终汇入黄浦江。大工业时代,水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1889年,苏州河南岸即开设了第一家大型工厂。此后,实业家们依河傍水,开办了面粉、榨油、纺织、造纸、印刷等工厂,继而又开设为这些工业配套的机器制造厂。外商——主要是日商,凭借《马关条约》中的特权,亦在此开办工厂,发展纺织业。
随着公共租界的扩展,道路、船埠和铁路的建筑,这一带的工业愈加发达。至上世纪20、30年代,苏州河两岸工厂林立,大批工人汇聚于此,其中便有大量来自苏北、安徽、山东等地的移民。无处栖身的他们,就在工厂附近的荒地、废墟、垃圾场上,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搭建草屋、芦棚,棚户区便逐渐成形、壮大。
浜北的棚户区,除少数为砖瓦平房外,大部分是草棚、简屋。另外还有极为出名的“滚地龙”——几根毛竹片弯成弓形,插入地里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棚,挂个草帘当作门,弯腰才能进出。没有窗,没有家什,没有水电,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臭水坑,瘟疫时常发生。
直到解放后,这非人的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水电通上了,“滚地龙”消失了,草屋拆掉盖起了土房、瓦房。然而,这里仍是出名的“下只角”,一间棚挤着一间棚,一间屋和另一间屋的形状绝不会雷同,小巷曲折而逼仄,如迷宫一般。
在少年李其纲的眼中,浜北的色泽是灰、是褐、是黑:
平江村错落蔓延的低矮寮棚和瓦屋,是一片深灰和褐黑;每天偷摸着去捡煤渣的潘家湾煤场,高高堆着的煤,像黑色的金字塔;闲来无事爬上的苏州河水泥堤坝,是灰色的;眺望苏州河对岸,上海面粉厂、申新九厂、大隆铁器厂,数不清的工厂和仓库,泛着钢铁的灰白……
浜北的居民多是苏北人。近代以来,淮河多次泛滥,家园被毁的苏北农民,沿着水路逃荒到这里,登岸、聚集。
与同一时期移民上海的宁波人、无锡人等相比,这些苏北难民既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鼓鼓的腰包。要在大上海生存下去,能依靠的,只有一双手和一身力气。
即便同为城市平民的浜北人,无形中也分为三六九等。“上档次”的是民办小学的教师,中药房配药的药工,人力三轮车工会的干部,苏州河对岸的纱厂、面粉厂、啤酒厂、制鞋厂等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工人。李其纲的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是纺织女工,在浜北便属于条件最好的。
接下来是集体企业的工人,比国企工人差一些,算是二等;三轮车夫、拉橡皮塌车的车夫、码头搬运工、马路清洁工等卖苦力维生的,属于第三等;最底层的是那些没有单位、没有劳保、没有固定工资的人:街头擦皮鞋的、磨剪刀的、卖爆米花的、菜场里刮鱼鳞的……
浜北底层生活的艰辛令人难以想象。李其纲有一个同学,从小拾荒,六七岁那年在附近遗留下的碉堡边捡到一枚手榴弹。他只知道金属值钱,便拿着手榴弹在火上烧,想把木头烧掉拿去卖钱。“轰隆”一声巨响,左眼没了,大夫给安上了狗眼,从此有了“狗眼”的绰号。
然而,艰辛归艰辛,浜北人生活得坦然,也比外来者想象得快乐。他们用满口的苏北话,有意无意地筑起了与外界之间的屏障,形成了与其他上海族群迥异的文化性格——
他们行为处事十分“抱团”,人与人之间亲近、紧密;他们重情、爽直、仗义,弄堂文化中那些鸡零狗碎、暗暗戳戳在他们身上是不大看得到的;他们崇尚武力,习武风气甚浓,年轻人拜师傅、结兄弟、练武艺、打群架;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尊重知识,对有文化的人始终高看一眼……在这座移民城市中,浜北人似乎始终是一种异质的存在,领受着异样的目光。
若干年后,李其纲成为了一名作家,浜北是他源源不断的灵感。
他笔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叫“燕青”。李其纲在他的身上融合了许多当年浜北小伙伴的身影。
燕青是一个典型的“苏北小鬼”,生活困苦,无忧无虑。当苏州河上的昌化路桥还是一座橡木桥时,燕青和伙伴们常常趴在栏杆上看来往的船只。客船一艘铆着一艘,从桥下穿过。燕青的尿便“恰逢其时”地憋不住了。纷纷扬扬的液体,穿过昌化路桥桥面上用来渗水的方孔,洒向船上探出脑袋看风景的人。突遭“甘霖”的人甩来一串热骂,无奈船开远了,只剩下燕青肆意的笑声荡漾在水面上。
这是一个林语堂所赞颂的“放浪者”的形象——他既是顽皮的,也是聪慧的;精力充沛,生命力旺盛;热爱自由,活得恣意淋漓,似乎无法拘束,也难以处置。然而,当与真实的外部世界短兵相接时,被歧视、被边缘化的“放浪者”必然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不断重复着“冲突-和解”、再“冲突-和解”的循环。浜北人“燕青”也是如此。
17岁那年夏天,燕青在平江桥头练起了石锁。当石锁像灰兔一样在身上上下蹿跃时,一位浜南姑娘的目光也在他充满青春荷尔蒙的身体上打量着,爱情,在这个夏天躁动了。然而,拉橡皮榻车的苦力的儿子,和住洋房的小姐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巨大的阶层差异面前,这段“焦大与林妹妹的爱情”尚未开始便只能结束。
被刺激而绝望的燕青,决定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远征。他约上一帮兄弟,来到了外白渡桥。夕阳中,十七八岁的少年们沿着钢铁跨梁慢慢地爬到了外白渡桥的顶端。居高临下地朝着浜南方向睃望一番后,燕青腾身而下,一朵巨大的水花砸在了苏州河河面上。在围观群众“小赤佬胆子忒大”“准是江北人”的议论声中,少年燕青用这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仪式结束了浜北与浜南的第一次爱恨情仇,也开启了更多的对峙、冲突与和解的序幕。
在平江村住到了14岁后,李其纲搬入了工人新村宜川新村。1970年,他到江西插队,返城后,在街道生产组、印刷厂做过工。1978年,李其纲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萌芽》杂志工作。
如果把当年的浜北棚户区比作水泊梁山,“燕青”是浪子燕青,那么李其纲便像极了“智多星吴用”——聪明,读书好,计谋多,也颇得人缘。若干年后,借着努力勤奋和知识的力量,“吴用”率先脱离了梁山——浜北棚户区,其他小伙伴也陆续离开,只有燕青留在了这里,插队、返城、做工、下岗,直到迎来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大拆迁。
在这轮巨大的城市改造过程中,苏州河沿岸的大型工厂陆续搬离,棚户区也陆续拆迁。1998年,潭子湾、潘家湾和王家宅“两湾一宅”动迁改造启动。当这场上世纪末上海旧区改造工程中最重要的战役结束后,“三湾一弄”在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中远两湾城、平江新村、地铁中潭路站等。
当然,浜北人不会随着“三湾一弄”的消失而消失。拆迁后的他们,像盐溶入水一样,融化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李其纲常在想象,他们现在正在哪里,继续着怎样的生活;也常在思索,他们的精气神是否给这座城市添加了些什么。
人们说,上海这座移民城市,既积淀了中国传统的江南文化,又接纳了西方文明的重重冲击,它的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元的。然而,当布尔乔亚式的小资情调为太多人津津乐道时,代表底层民众生活和思想状态的普罗文化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李其纲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属于上个世纪的浜北人的爱与哀愁,是值得记取与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