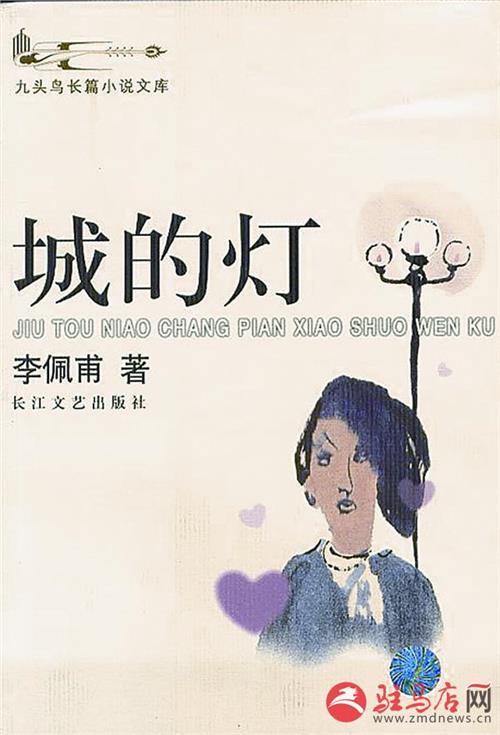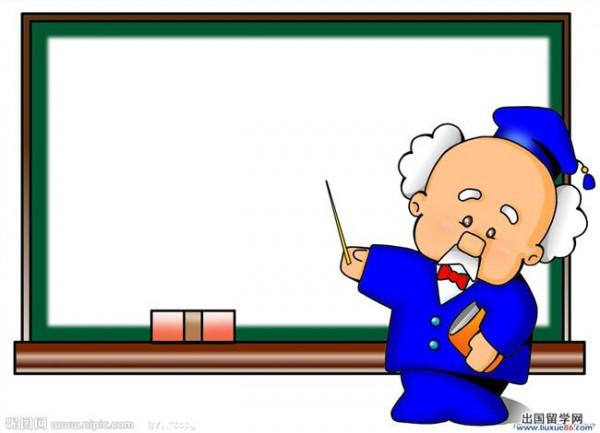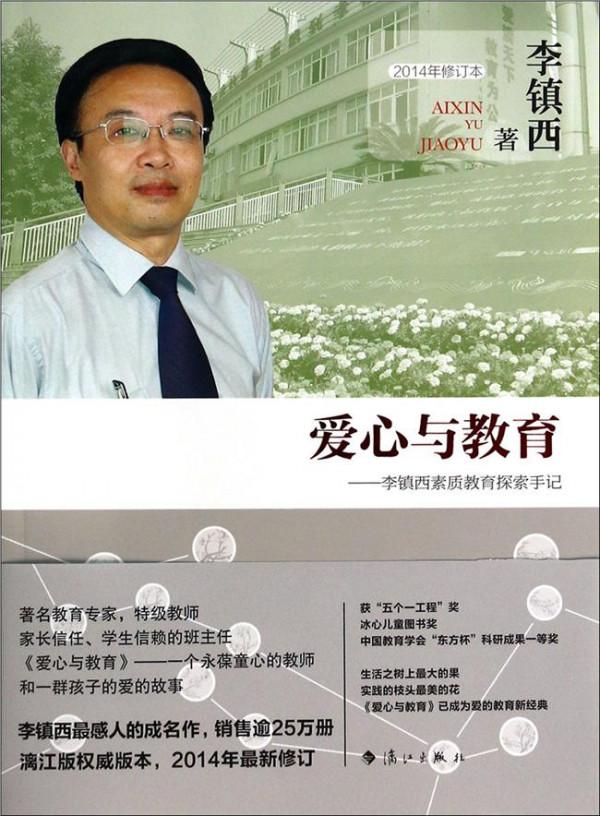等等灵魂李佩甫 《等等灵魂》试读:李佩甫访谈录:一个时代的口号
记者/黎延玮记者:从《李氏家族》开始,你的长篇小说大多是表现乡村与农民题材的。你这次创作的《等等灵魂》却以都市商战为背景,与前几部小说比较,这部小说有什么异同?在题材和人物刻画上,有什么新的追求?李佩甫:许多年来,在我的创作意识里是没有题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
这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不是要翻题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记忆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创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认知的“大地”,是我创作的源泉。
“平原”是我在心中划出的一块“宝地”,并非特指乡村。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乡村是记忆的根,我也一样。可我毕竟出生在城市,五十年来,大多时间也生活在城市,人的精神变化是随着时代重心的转移而变化的,我的记忆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先后研究了上百个商海中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金钱已成了压在人们头的上一座大山,一个“卖”字,象溅着火星的烙铁一样烫在人们的心上。
如今,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舞蹈……这部长篇,对于我来说,只是在精神“平原”上另开了一个“窗口”而已。记者:你以往的作品,对官场、对农村政权的阴暗面大多持批判态度,主要人物多是灰色的或多色调的。
在这部长篇里,你实现了从“官场”到“商场”的成功转型,在小说中塑造了任秋风这样一个商人形象。这其中寄寓着什么理想和思考?李佩甫:从文学意义上说,我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批判”,而是另外两个字:“丰富”。
社会生活的丰富,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和“坏”的问题,是精神指向的多元。在“大地”之上,人,做为一种“植物”,我关注的是一种生命的过程,是“植物”生长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比如“树”的长势和纹理,在一定的气候和土壤之中,它的生长状态等等。对于任秋风这个人物,我突出的是一个“变”字,这是一个变化中的人物,是一个本意要走向伟大和崇高的人,在金钱的压迫和冶炼中一步步“投降”的过程,那“白旗”是怎样一点点举起来的。
有很多个夜晚,我的确是在这个城市里走来走去,像一个游魂。我看着灯下的脸,我一直在阅读人的“脸”,期望着能破译出一点什么来。
对城市,我已读了很多年了,这算是我的一个读本吧。记者:小说描述了任秋风和上官云霓、江雪、陶小桃、苗青青几个女人之间的情感,这些人物在特殊的际遇中,从性格到命运都发生了许多不可控制的变化。
你将悲悯的情感更多地藏掖在暴力化的灾难场景之中,使亲情之爱、人道关怀等更多地成为苦难的支撑点,成为反人性的历史境遇中一种奇特的救赎力量,从而使故事在人性的揭示上变得非常开阔,也非常丰富。
所以,《等等灵魂》给我的感觉是,你试图在重构一种具有中国经验的、比自己以往的小说更具历史丰富性的“叙事”。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李佩甫:生活是很复杂的。比如,单一的年代,我们渴望多元;多元的年代,我们渴望纯粹。
可单一了,自然会走向纯粹,但同时也会导致极端;多元了,自然会走向丰富,但同时也带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写了这个时代的四个女性,这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生长的四个都市女性。
她们是多么美丽,多么敏感,又是多么柔弱!写这四个弄潮儿,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四个都市女性一旦出现在纸面上,就已经不归我控制了,她们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和目标……我眼看着她们在情感生活里越走越远,而无能为力。
这是我无法控制的。所以,我只有任她们按自己的轨迹行走,是她们自己在讲述各自的情感故事。这部长篇是贴着生活走的,我不想进入荒诞。记者:你十分注意小说语言的提炼,从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开始,就形成了自己清新蕴藉、耐人咀嚼的语言风格。
在《等等灵魂》这部小说中,我注意到你的语言更加圆熟、具有诗性的张力。音乐般的节奏,诗歌般的句式,细致入微的描绘,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术氛围。
你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美的语言?你刻意追求这种对比强烈的语言效果的目的是什么?李佩甫: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就是思维,形式就是内容。时代就像是一艘颠簸的船,在一片嘈杂声中,在一片晕眩里,在波及每一个人的“买”与“卖”的漩涡中,在灵与肉的切片一张张挂出去之后,我已顾不得语言的问题了,我只是跟着走。
当然,有时候也停下来,把笔尖磨一磨,使它更锋利些。但是,坦白地说,在这部长篇的表达里,我几乎已忘记了语言。
记者:小说最具震撼力的是对细节的精心处理。譬如在叙述任秋风转业回来看见妻子和别的男人上床时,任秋风的冷静,尖锐,惨烈;而在叙述任秋风的第二任妻子上官云霓面对任秋风情感变化之后的一系列表现,以及上官云霓和陶小桃之间的友情等,则呈现出《城的灯》之后所恪守的温情化特征,亲切,温馨,坚韧。
这两种不同叙事策略的相互整合和统一,使小说在表现场景和人性面貌的复杂性上,具有一种异常灵活的审美效果。对于这种细节的处理方式,你是否有着特殊的理解和思考?李佩甫:是的,自写了《城的灯》之后,我对生活的视角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也许是看的多了,这里边自然就多了些包容和理解,多了些暖意和温润。
已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了,所有的细节都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
说来,我的写作环境也很特别,我住在动物园附近,每天每天,我都听见狼在哭,象也在哭……我想表现的是人在疯狂之中的静态,人在潮水中的挣扎与呼喊。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人们正在经受的、或者叫享受着一种新的病症。
这是人们从物质匮乏中走出之后,第一次享受高级动物(人)才能享有的精神疾病——来自灵魂的“SARS”。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部病相报告。记者:鲁迅先生说,所谓的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毁给人看。
从这点出发,我在读到《等等灵魂》中的某个情节时会忍不住地愤怒和悲伤。随着事业渐抵巅峰,任秋风盲目拓展,要建一座全球最高、象征着“金色阳光”巍巍大业的摩天大厦,但大厦在打地基的时候却遇到地下暗河,由此激发了各种矛盾,导致资金链的断裂,“第一商业帝国”全面崩塌,跟随任秋风创业的“商学院三枝花”亦分道扬镳……这其中寄寓着什么样的理想和思考?李佩甫:在我们的生活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悲喜剧……这里所写的是一部精神成长史,也是四个都市女性的情感史,是四位都市女性在情与欲、爱与恨的裂变中的精神成长历程。
四位都是知识女性,也许在生活里失去了什么,但她们的精神在一天天强大,都各自在寻找或者已经找到了疗救的方法……对一个时代来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
社会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时代在一天天进步,所以,这里有悲有喜,是悲喜剧。记者:你为什么将这部长篇的题目定为《等等灵魂》?通过这个题目,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李佩甫:对于题目,我考虑了很久很久,大约一直到完稿时,仍在犹豫。
也许,还有别的更合适的名字。可后来,我还是借用了印第安人的一句话: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虽然用这样一个名字略显突兀,可我期望着这是一部反省书。同时,在文学意义上,给这个时代提一个醒,也是给自己提个醒:等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