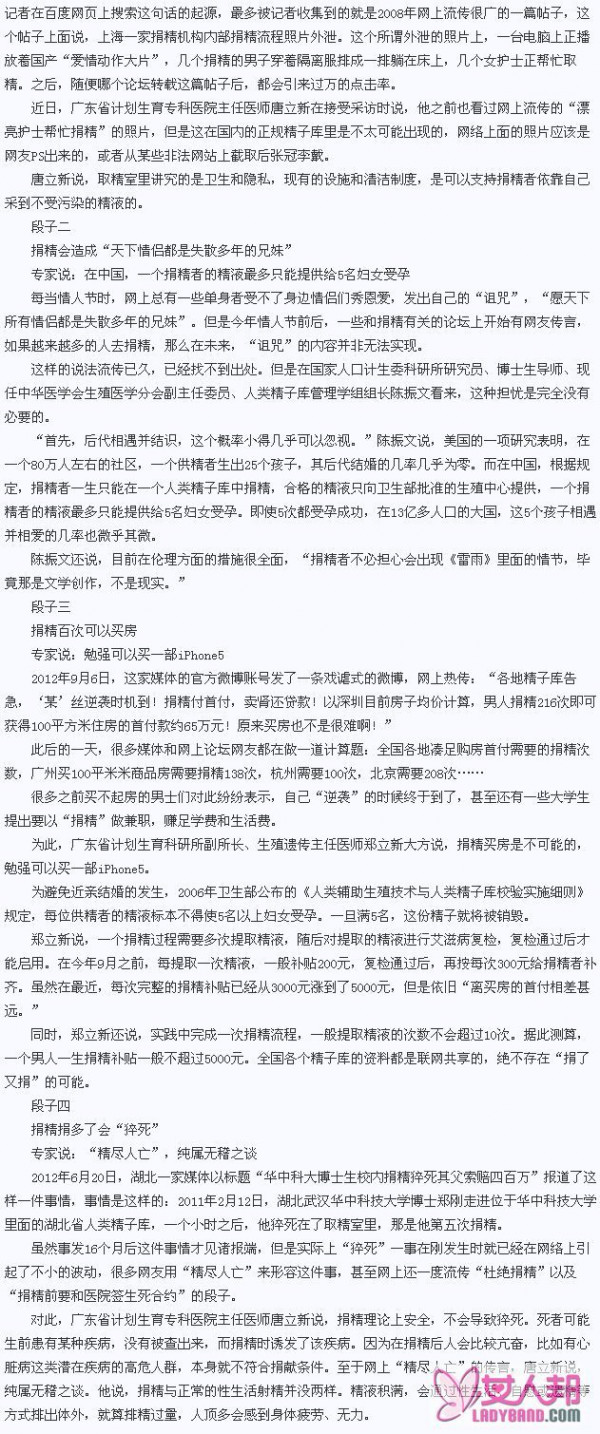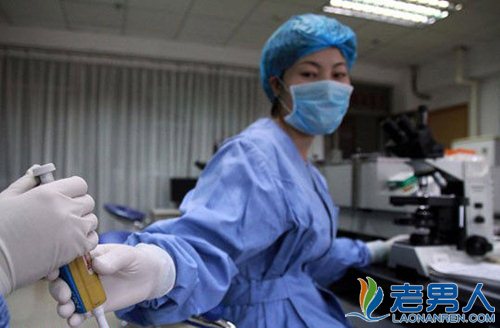揭秘广州地下捐精过程:直接与女方发生性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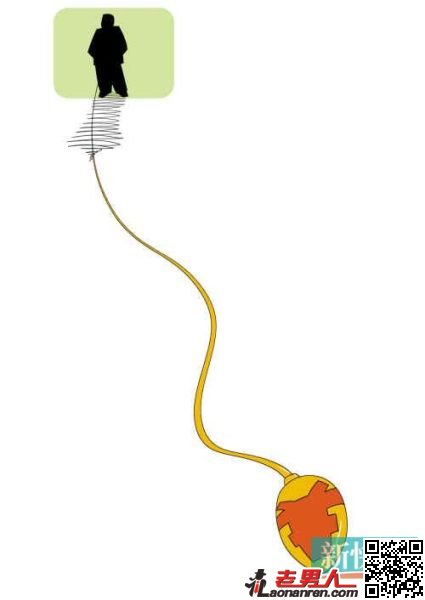
这句话很快被酒吧里强劲的音乐声淹没。
这不是什么色情交易,其背后甚至略含温存。一对结婚多年无法生育的夫妇,在尝试各种办法之后,依然不愿放弃,他们想要一个孩子,然后就通过“自助捐精”qq群找上了段暄与。
后者所要做的就是在类似于酒吧这样的公共场合取出自己的精液,用含有冰块的冷冻箱包好交给那对夫妇,再由女方用注射器将精子推送到自己的子宫内,以让其怀孕。当然,段暄与在这段关系中会得到一定的报酬。
也有的时候,他们会采用更直接的方式,就是捐精者和女方直接发生性关系。
而卫生部门对此明令禁止,任何不通过正规精子库的私下捐精和授精,都属于违法行为。
不光是段暄与,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人,白天忙于高档写字楼或者市井之间,夜晚降临时,则流连于酒吧昏暗暧昧的灯光下,等待着再一次捐出自己的精液。
他们是一群地下捐精者,闪烁不明的酒吧灯光下,他们黑暗中的身影,折射出的是中国大规模“精子荒”的现状和焦虑。
用儿子的照片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
从与记者的对话中来看,段暄与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部总监。在短短二十几分钟的qq聊天对话中,你可能无法看出他身份的真实性,但是当他把一张他办公用电脑的桌面截图发过来时,你会看到,桌面上密密麻麻的文档标志,标示着“策划”或者“素材”等字样。
而桌面的背景,则是一个一岁左右小男孩对着镜头甜笑着的大头照。那是段暄与三岁儿子曾经的照片,拍照的初衷是为了庆祝孩子满周岁,现在则被父亲用来向形形色色的各路求精者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
给新快报记者展示儿子照片的时候,他不忘说明孩子的来历,“我和老婆结婚前只做了几次,我记得好像都带套了,没想到她还是怀上了,我们就结婚生子。”这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
在网聊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地就没有回应,过一段时间后抱歉地说,刚刚去给下属开了一个小组会,“这段时间两家食品公司新品发布了,赶着给他们做广告策划,所以有点忙。”说着这话时,他又签完了两套广告的初步方案。
这个在公司里被称为“段总监”的男人,有一辆价值14万的代步车,一套70多平方米的按揭房产。他的所有家人和同事都不知道,“段总监”除了自己的儿子之外,他还是另外两个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
公开而且光明正大地
谈论和“性”有关的东西
已经有两年捐精史的段暄与说,当初自己还在深圳工作,本来打算响应政府号召,为广东省精子库提供精子,但是打了两次电话过去,精子库的工作人员都以深圳距离广州较远,往返捐精耗时耗力为由拒绝了他。
这让段暄与有点郁闷,为此,段暄与决定“自力更生”,几天之内加了六七个广东省的捐精qq群,在里面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只要他有空,就不断查看其他群员的信息,“只要资料上面写的是女性,我都会和对方私聊,询问她是不是需要精子。”
一段时间之后,段暄与发现自己已经逐渐迷上了这种忙里偷闲的“勾兑”方式,因为在群里,他可以公开而且光明正大地谈论一些和“性”有关的东西,“要是在平时,我和一个陌生女人讨论精子,或者谈论她丈夫无法生育,肯定要被说成是耍流氓。”
而另一个让他着迷的原因是,他逐渐发现,通过非正常渠道捐精,来钱很快。
段暄与所说的“非正常渠道捐精”就是指精子的供求双方私下见面,通过个人或者非法经营的民营医院进行授精手术,而不是通过正规渠道的广东省精子库进行授精。
记者通过捐精qq群了解到,群里普遍流行着这种非正规渠道的捐精方式,每个捐精者只要提供了精液,无论对方受孕成功与否,都会得到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酬谢费用。
慌得差点连报酬都没拿就夺门而出了
镜头上移,2012年2月份,30岁的段暄与完成了自己第一次“捐精”交易,他躲在一家酒吧的卫生间里,沾满水渍的洗手台上放着一个带夹层的塑料盒,夹层里塞满了已经半融的冰块。他用颤抖的手端住冰盒,转过身去……
十分钟后,他从打开的门缝中将装着“小蝌蚪”的冰盒递给一个34岁的中年女子,然后走出来,“我当时慌得差点连报酬都没拿就夺门而出了。”
那一次,段暄与拿到了500元的酬金,不过半个多月后,求精的中年女子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告知授精失败,自己没有怀孕,之后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那次失败的经历,让段暄与开始研究如何才能更高效率地让授精成功,他通过看评价,了解了淘宝网上哪种试纸能更好地检测出女性的排卵期,甚至会发来几张网购图片,让扮成求精者的记者选择合适型号的阴道注射器,以便更顺利地将精子推送到体内。
有了这些经历,他很快就在众多捐精者中“脱颖而出”,为一位结婚5年的女子提供精子。
依旧是在酒吧里进行,段暄与说,酒吧里黑暗的环境和嘈杂的音乐声让他觉得安全,不必担心自己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瑕疵毕露,更不会因为环境的安静而感觉尴尬。
那一次,他在酒吧的厕所中,和女子的老公一起帮助她将装满精液的注射器推进体内。他只记得,一只苍蝇在洗手池的玻璃上不断地停了又飞,自己因为紧张而汗流满面的脸垂下来,在女子的身上投下大片的阴影,汗珠一滴滴砸到女子的肚子上,其他的他什么都没有看清。
厕所门外,是强劲而嘈杂的音乐,夹杂着醉汉因为等不及厕所,而在门外呕吐的声音。
这一次,受孕又失败了。
最后
他们采用直接受孕的方式
一个月后,女子又赶到广州,这次,他们采用的是直接受孕方式,即捐精者和求精女性发生性行为,使后者怀孕。
段暄与说,那次女子的老公没来,他和女子在一家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小旅馆里开了房,进房间之前,他们相互关掉了对方的手机和所有可以拍照的设备。段暄与说,他把那次性交,看成是一种“仪式”,因为是第二次“补救”行为,所以自己没有收取费用。
两个多月后,就在段暄与以为又失败的时候,女子在qq上发来一张B超检验的图片,显示女子已经怀孕。
两天后,一桶蜂蜜被快递到段暄与的单位,作为酬谢。
付钱能给双方提供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
有了一次成功的经历后,段暄与在捐精qq群里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总不忘在最后加上一句,“2012年成功让一个女子怀孕”。
除非有人很仔细地问,否则他不会说出那次怀孕的真实经过。“毕竟直接发生性关系让对方怀孕,这事说出来会让很多人有顾虑。”
段暄与在潜意识里,始终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和群里那些只想占女人便宜的猥琐男不一样。”
他所指的“猥琐男”,是捐精qq群里一些只愿意提供“直接捐精法”的男子,他们喜欢在群里发布色情图片,甚至自己的私处照片,见到女性群员则热情地鼓动其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助其怀孕。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段暄与之前的“成功经历”,确实给他加分不少。他说,一些女性群员甚至开始主动找他聊天,询问之前成功助孕时的各种细节。
水涨船高,段暄与此后的捐精费用也照比之前有所增加,“之前捐一次,可能就几百元钱,后来捐一次,我会要更高的价码,例如1000元甚至更多。”
相比群里很多捐精者打着“免费捐精”的旗号,段暄与则有自己的主见,那就是双方都付出一定的代价,会让这种捐精的行为更像一种交易,而这种交易则给双方都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
“这么说吧,如果我说自己免费赠送精子,那么求精方可能觉得这事不靠谱,甚至事后觉得会亏欠我什么。但是给我一定的酬谢,让双方明白这只是一场交易,就像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事后双方都没有什么责任和负担。”段暄与说。
这种“交易”,段暄与至今已经做过6次,他成功地让其中两个求精者怀孕。
想捐精
还要拼学历和身高
事实上,在所有的自助捐精qq群里,很少会有女群员主动发布求精信息,更多的时候是想要捐精的男士们在图文并茂地进行自导自演。
在一个100人左右的qq群里,经常说话的也就是那么十几个人,他们撑起了群里日常的交流活动,而这些人,也几乎都有着曾经捐精成功的经历,“就像拼资历一样,捐精成功的人是老大,才有资格在群里发言。”一个捐精qq群的群主说。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他人没有行动。加入qq群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有十几个人给记者发来了私聊,提示加好友的“小喇叭”也响个不停。
和群里那些“老大”相比,这些人打的是自身优势牌,学历、身高、相貌,甚至工资待遇等都成为他们搭讪的资本。
“211院校博士在读,身高176cm,家中父母都很健康,外婆前年癌症去世,其他亲属都健在。”一个叫“176博士”的群友首先向记者伸出“橄榄枝”,他称自己已经31岁,之前因为忙于科研,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成家,“不知道自己这辈子会不会有老婆了,所以希望在年轻的时候留下后代。”
而一个广州大学城某高校的男生小陈相比之下则略显羞涩,因为缺少生活费,所以他想到用捐精的方式解燃眉之急。
这个自称之前“把所有的精子都捐给了德艺双馨的苍老师”的男孩,既不懂得捐精之前需要提供体检报告,甚至不清楚捐精的流程。他所能提供的优势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所有科目都是80分以上。
在记者没有时间理他的时候,这个已经大三的男生会用一种向教授求教时略带紧张的神气,连续三天,一遍又一遍地在qq上问记者,“姐姐,你还在么?能向你请教一下么?”
一切就像一个捐精qq群的群主所说那样,这个捐精的群体其实并没有表面那么单纯,背后有可能充满了谎言和欲望。“你不知道你面对的那个捐精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有可能是博士,可能是企业高管,也有可能是在逃的通缉犯,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一个个验证他们所说的是否是真话。”
每次捐精
他都要分给“蛇头”1000元
如果把地下捐精看成一个江湖,那么段暄与他们只算得上是这个江湖中的小卒,那种一对一的个体捐精,毕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而曾经的捐精者阿游,接触的是更高层次的捐精体验。今年夏天,有一段时间,他直接给白云区一家民营医院“对口”提供精源。
流程是这样的,阿游只和那家医院的一个行政合伙人单线联系,在捐精市场的黑话中,那个行政合伙人被称为“蛇头”,起到的是一种中介的作用。
首先,医院先打出可以做授精手术的广告,等有消费者“上门”之后,“蛇头”会和阿游联系,通知他来捐精。
“医院方和消费者说精源来自广东省精子库,但是我们内部人员知道那些都是扯淡。”这个35岁的东北汉子谈到那段经历,有点不屑。
每次捐精,阿游都会用院方给的一种特制容器提供自己的一份精液,那份精液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送上手术台,并在十几分钟的手术中,被注射到求精女子的体内。
事后,阿游会从院方的财务那里获得3000元的报酬,这笔钱是由求精者提供。拿到钱后,阿游还有从中分出1000元给“蛇头”,作为酬谢。如果这次求精者没有怀孕,那么下次再来做授精手术时,可能就换成其他的捐精者来提供精液。
阿游说,医院主要赚的是手术费和求精者来体检的费用,属于地下捐精市场中的上层结构,“蛇头”负责拉人,并协调精子供求双方的关系,从中提成,算得上捐精市场的中间人士。
“捐精那么多次,有几例成功呢?”阿游说,医院方和“蛇头”都不会告诉他捐精的结果,“我反正是拿自己的那份钱,其他的都不需要管。”
阿游说,实际上,医院方的谎言并不是让所有人的信服,“其实很多来求精的人心里都明镜着呢,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但是心甘情愿被骗,有些被骗完还要送锦旗过来,呵,‘送子神医’。”
这在阿游看来,和通过正规渠道太难得到精子有关。“每年到省精子库捐精的人就那么多,但是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又那么大,所以肯定要催生一些不法的个人个行为。”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但是那么多人都这么做,他们(求精者)本人也愿意啊,我们从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帮助了他们完成生子的心愿,所以我没有道德压力。”
不过,今年8月份开始,阿游还是换了手机号,“辞掉”了之前的那份捐精的工作。他说,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不能总靠这个活着,他打算用手中的积蓄,回到东北老家去做点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