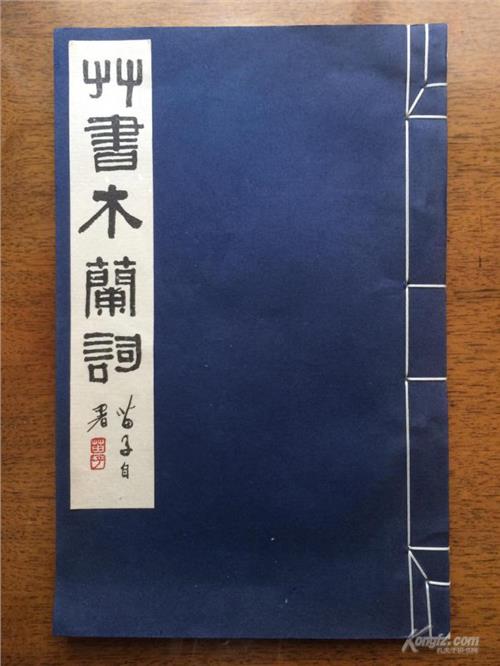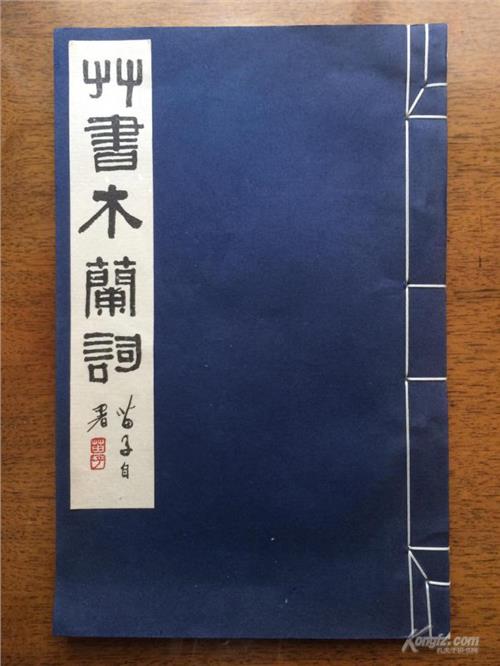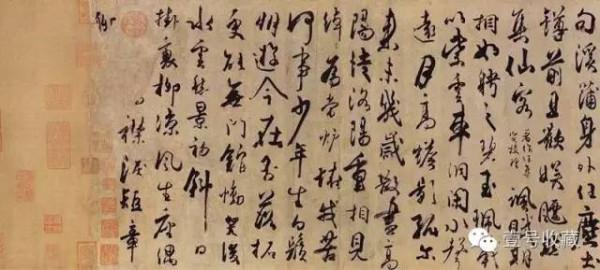冯亦代卧底 章诒和:冯亦代怎样成了我家的卧底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父亲看了他的几篇译作后,说:“亦代呀,翻译水平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母语水平。你的中文要从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脸蓦地红了,什么都没说,大概也没跟老刘说。
母亲则认为他的字写得太差。说:“亦代,你的字怎么没骨头?”冯亦代随即说:“李大姐,你来教我写字吧。”
“我找些碑帖来,你先临摹一段时间。”母亲说罢,没几天就把碑帖给他准备好了。
父亲借给他的古书,冯亦代是还的。母亲借的碑帖,不还。催了多次,他只是笑着说:“我还在练习呢!”二十年以后,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都气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树要皮,人要脸。文人要紧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脸面、体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虽属无意,但冯亦代还是很受伤。所以,朱正先生认为在他的日记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怎么能没有敌意呢?
父亲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1957年前,毛泽东就知道章伯钧在背后骂共产党。因此,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绩了!
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无偿劳动了。“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1961.
8.7.p332]某部内部举办电影晚会和干部晚会,破例叫他参加[p324、p353];赠送最热门的世乒赛票[p312];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124元[p340];老刘多次与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刘冯两家人吃全聚德烤鸭,他“心里十分感动,喝得醉醺醺的”[p291]。
如此看来,他们几乎成为同志加战友了。冯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长期性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刘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p254]。他立即表态:“为了工作,公不公开不是问题。”[p254]
尽了心力之后,冯亦代觉得自己应该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请。以后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请入党。
”[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记里,他写明“党的四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拿什么献礼的问题。我想再提一次入党的申请,把我的余生无条件地献给党,献给革命。”[p323]不知为什么,他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1978:他结束了黑暗
1967年,父亲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关进机关的牛棚。母亲天天下午去探视,去的时候,不忘带些吃的。第一天,因为毫无准备就拿了一块红薯。此后,母亲就专门去买些罐头、水果、饼干。父亲总把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对母亲说:“亦代和我关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么不来看他?”“一次都不来看?”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所以,你送来的东西,我要乘人不防备,偷偷给他一半。”
我和冯亦代有单独的往来。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他送我许多书。如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钱锺书的《管锥编》、爱伦堡的《人生·岁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来京,在东华门的儿童影剧院演出。
全剧用上海话对白,他见我不懂,就在耳边当起翻译。一路看下来,很辛苦。我喜欢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也舍不得,到火车站送行。我也忧伤,时间一点点积攒着依恋和难舍。
到了四川,给父母写信的同时,也给他写信。即使到了监狱,也不忘问候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总要附上一句:“冯伯伯好不好,还来咱们家吗?”母亲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说:你现在是犯人,不要询问别人的情况。我知道,这里指的别人,就是冯亦代。
1978年我出狱回京。他陪母亲一道在火车站接我,见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红了。母亲告诉我,每年父亲的诞辰日,冯亦代都会陪自己到老山纪念堂扫墓。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亲去扫墓,冯亦代早早到了。见到我,他说:“你回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祭扫。”
他的目光望着远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语:“伯老,真是好人,他对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编《读书》杂志,锋头极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每一期都送给我,我们也恢复了通信。几十年间,冯亦代给我的信函有数百封,但自这段时期起,他的信越写越好,因为他走出了阴影,也结束了内心的黑暗。
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总得凭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虚无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时我有各种美好的希望,我迷恋于一个新的社会,最美满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动乱,使我幻灭,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来了。
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个传人,我一直喜欢你的灵气,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动笔的人……我到车站去迎你,看见你那双呆涩的眼睛,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场。我怕你这十年的坎坷毁灭了你的灵性。我知道一个人幻灭的痛苦。我要弥补你心灵里的伤痕。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着,他去美国访问,又给我写了长信,说:“飞机在高空长驱又盘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爱的小愚……”
1990年代,冯亦代与演员黄宗英结婚的前几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发如雪,鬓已霜,屋里响着小提琴曲,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小愚,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你来给我出版吧。”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