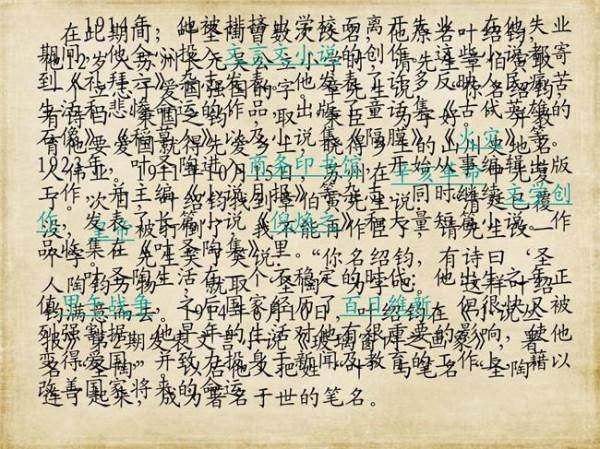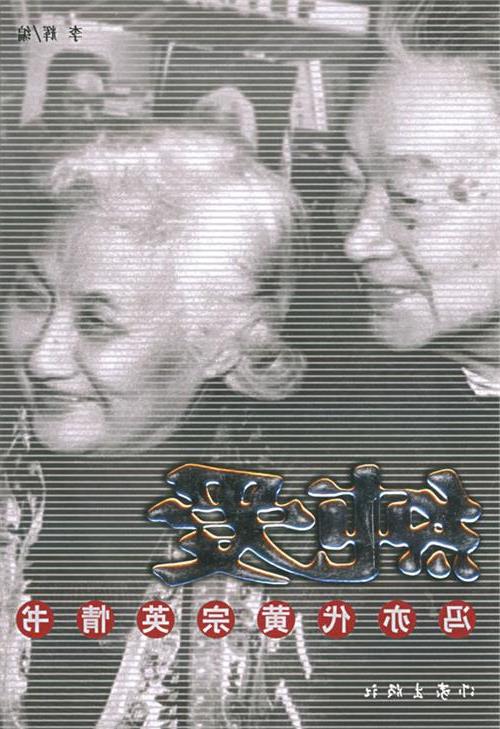冯亦代书癖 《窃读记》推荐阅读作品——忆读书(冰心)书廦(冯亦代)书的抒情(柯灵)
导读:忆读书,冰心,一谈到读书,就开始读书,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读书好,多读书,而且教我读书,到上海读书以后,忆读书冰心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4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
忆读书
冰心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4 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7 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笸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逼民反”的《水浒传》大加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勉强强地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我11 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有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1986 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传》,看了人物栩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吟,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那怕只有几百上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已!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有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1989年9月8日清晨
国际扫盲日 中国教师节前夕
书癖
冯亦代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变了个爱书成癖的人,只要闻到新书里散发出一阵纸张与油墨的扑鼻清香,我便欣喜若狂,不啻是嗅着一捧鲜花。即使在旧书店里,屋底里透出阵阵霉味,但只要我打开书叶,也是可以闻到旧书所特有的气味来的。这一种爱书的怪癖,我不知别的爱藏书的人有否同感,也许只是我特有的吧!
爱书必须逛书店,首先是爱逛书店,才能养成爱书之癖。我一生第一次踏入书店的经过,却不是个愉快的回忆。那时我不过七、八岁,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商务印书馆杭州分店做事,分店开在清和坊,离我家还有一大段路,但是那位比我大两岁的同学带我去了。一走进这书店,门后四壁都是玻璃书橱,竖摆着一本本的书。店堂里进除了有一列算帐的柜台外,便是店堂中央有四张玻璃桌面的桌子,桌面下平摆着一摞撑的书。初进去时看见同学的父亲不免有些羞涩,但过不久,便为书橱里陈列的童话书所吸引了。有如入宝山而见宝藏,我一本本翻看起来,竟不知时之云暮。倒是同学的父亲催我快回家,怕家中人着急,而且还亲自陪着我,走到我家的街口。
我事先并未告诉家里要去书店,怕告诉了大人不让我去。如今放学后多时不归,祖母大不放心,先是以为我被老师留校厂,后来派我奶妈去学校找不到我,全家就着急起来。正在祖母牵肠挂肚的时候,我却突然回家了。祖母是既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我终于站在她的面前了,生气的则是我居然敢事先在家里不作一声,而和同学跑到老远的清和坊去。祖母倒拿着鸡毛掸子要打我,我便在八仙桌周围,和她转起磨来。她当然没有我跑的快,所以鸡毛掸子只在桌面上敲出声音,而打不到我身上。我起初害怕祖母真的打我,便又喊又叫;后来祖母也追我追得累了,便坐了下来。我停止了叫喊,却看见祖母端坐在圆椅上,竟然老泪纵横。这一下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只见祖母一面抽抽搭搭,一面数落我说,如果我妈在世,她才不操这番心,只因为我妈早死,才使她到老还要管一个孩子,惟恐有所闪失。我便泥在她身
上,说以后一定听她的话,不叫她生气。这才使她破涕为笑。一场风波就此了结,可是以后我也别再想到商务印书馆去了。不过我心心念念是那几本童话书,终究还是祖母差了我的大表哥给我去买回家来。
我再进书店门时已有十一二岁了。离我家不远的保佑坊开了一家新书店.叫光华书局。开幕日我的一个同学便带我去了。这里面卖的都是新文艺和新社会科学的书籍。我想我之日后爱书成癣,与这家书店不无关系。我在这里买到了郭沫若、郁达夫的书,以后又买到鲁迅、茅盾、巴金的著作。我当时的头脑正如一块会吸水的海绵,这几位大师的著作,滋润了我的心田。我不但读他们的书.而且从他们那儿学会了写作。当时我说是写作,不免有些夸大,事实上,不过是涂几笔而已。写了东西便向报纸投稿,也居然受到杭州《民生报》编辑的青睐,不但采用了我的稿件,而且还约我到报馆见面,从此有—个时期我便成了他的小助手。这位编辑名张人权,他不但教我编报画版样,而且教我读书。他是念法语的,对法国文学颇有研究,中国最早出版法国都德的《磨坊文札》就是他译的。
跑书店竟使我日后成了一位弄笔头的人,实非我始料所及。不过因为弄笔头,就更增加了我对书的兴趣。杭州的湖滨路有三两家旧书店,我于跑光华书局之余,又去跑这几家旧书店了。记得首次使我去旧书店的,是郁达夫先生写的小说《采石矶》,我读丁之后,深为清诗人黄仲则的身世所感动,便想一读他的《两当轩集》。我在旧书店居然找到了这部木刻的集子,买回家来念了,不时为他一掬同情之泪。这部诗集我一直自上海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又从重庆带到上海。最后则随我到了北京。一直到“文革”初期,始作为四旧“呈缴”给当时的“英雄好汉”们。
跑旧书店使我有机会遇见了郁达夫先生,他那时常来杭州,一来必到旧书店。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在书店漫游书城,他是达夫先生的亲戚,因此介绍认识了。我记得那天达夫先生还请我们到陈正和酒店喝老酒,听他大谈黄仲则,他是非常喜欢黄仲则的,每每以黄仲则自况。
到上海读书以后,星期六或星期日有暇,也常到法租界一家西文旧书店去跑跑。那时使我看入迷的是一本美国白耐特·塞夫谈外国藏书故事的书。过去我对国外的藏书一无所知,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们藏书也是十分讲究版本的。这本书是美国《现代文库》中的一本,1980年秋我访美时也去跑了几次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旧书店,遍访此书不得,只买了一本琪屈罗·斯坦因的选集。这几家旧书店真是旧书店,店面既破败,藏书亦很杂乱。10月的天气,纽约还不凉快,钻在旧书堆里密不通风,竞使我挤出一身汗来。但我以获得一本斯坦因的选集而喜不自胜。她虽然是20年代的人物,而且开创了美国一代文风,但曾几何时,在美国似乎是早被遗忘了的人。“文章千古事”,在美国不过是夏日雨后的长虹,虽然光彩夺目,亦不过刹那间事耳。
上海被日寇侵占后,我南行避地到香港。香港也有几家书店,大都是出售英美新书的,但偶尔也杂有几本旧书和过期的杂志。当时我和徐迟、杨刚、乔冠华等经常去盘桓的,是设在摆花街的李全记书店。海明威写西班牙内战时马德里却柯特酒店所发生的三个故事,我便是在这里买到的旧《老爷》杂志中发现的。这三个故事竟成了我步入翻译界的敲门砖,实非始料所及。日后读到海明威的《第五纵队》与最初49个短篇小说集,已是在80年代了。这本书在纽约的旧书店里也没有买到,东道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诗人白英说可以复印一本,也因页数过多未成事实。倒是最近在老友徐成时处看到他收藏一本,不免又引起我
的怪癖来了。成时乃以此书作赠,对于我来说这岂是一书之赠,这里面包含着成全一个人的盛意在内,所以我也不以言谢,只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
我到重庆时已是1941年,重庆早巳被炸成一堆瓦砾。除了几家大银行商号之外,城里多的是饭馆小吃店,只是在两路口有一二家旧书铺。到1942年,日寇的轰炸大为减少,雾季时竞可成月不闻警报声,我出城有便时就去浏览一番。
有次吴宓先生到重庆,我有个朋友是他的学生,常和我谈起吴先生的诗词。一天,我偶尔在旧书店里买到了他的诗集,厚厚的16开一大册,以后几年中我经常翻读,我觉得他的诗自有一种空灵的气氛。另外买到的两部书,也是非初意所想到的。
一本是D·H·劳伦斯的《恰特莱夫人的情人》,还是翻印本。这本书在英美当时都是禁止出售的,但中国的书商将该书翻印了。在大学时我曾经托一位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同学买到,但以后大家传阅,再不能有物归原主的机会。
这次我遇到了这本旧书,缅想在烽火中不知流亡到何处的赠书人,为之悒悒不乐者久之。另一本则是英国法兰克·海里斯的<我的生活与爱情),如照金圣叹的标准,这是本奇书。因为海里斯在这本书里,上至英法政治人物,下至市井鸨妓,无一不包罗在内。对于邱吉尔他倍加称颂,对于萧伯纳则刻意调笑。特别是英文之漂亮,自成一家,令人叹为观止。
有次在—家旧书店里看到一套15本的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英译的,呵惜我现在把这位翻译者的姓名忘掉了。这套书原主人固有急用而在旧书店里寄售,我站在昏暗的店堂里读了10多页,简直爱不释手,碰巧身边带的钱不够买这套书,而原主又不许书店削价出售,只得怏怏而回。
第二天再去看时,则已经为他人所得了,心里的懊丧简直无法描述。就在这天晚上,故友顾梁背着一大布包书来了,说是专门买了送给我的。打开包袱一看,则从我手底下漏去的<追忆似水年华)赫然出现眼前,我那个高兴劲儿也是无法描述的。这套小说随我自重庆到了上海,又北行到北京,可是卷帙浩繁,却使我不能读毕全书。50年代初,我把它和其他的爱书,送给了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前身)的图书室。经过十年动乱,不知这套书是个什么下场,我不敢去问,惟恐听到不好的消息。
抗战后回到上海,那时我正热衷于电影,便把上海所有新旧谈电影技术及艺术的英文书,都收集到了。后来陈鲤庭和何为等办电影文学所,我便全部99送给他们。据鲤庭说这些书在“文革”中,也全部散失了。这里面有些书当时即已绝版,今天再要搜罗,显然已成难事,惜哉!
我的书癣大概在50年代初叶,达到登峰造极;因为解放后出版事业蓬勃发达,许多书如<鲁迅日记)的影印本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的文集都相继出版,使我可以闲坐书城,摩挲观赏,亦人生一大乐事。但好景不常,奇祸迭降。为了儿女衣食,不得不将这些伴我岁月的典籍,尽行出售。另外则还有一种心情,觉得文章误我,今后再不做这种生活了,就此卷铺盖上千校去也。
不想我这甘心在干校落户——辈子的信念,在1972年11月忽然奉“令”改变了,于是又卷铺盖回到北京。夫妻重逢,首先谈到生活,不愿月圆人寿,但愿多有时间读读想读的书,以了宿愿。于是原来已经放在厨房使用的书架,亦重新升格,回到居室为藏书之用,不再每日与油盐酱醋为伍了。我又能重亲新印书刊的纸墨清香,其乐也陶陶。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不会好的常好,坏的常坏。正在我们离休之后,认为今后可以多得时间,亲炙楮墨的时候,本本买来的或送来的书刊竟占领了我们的整个居室,屋内四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