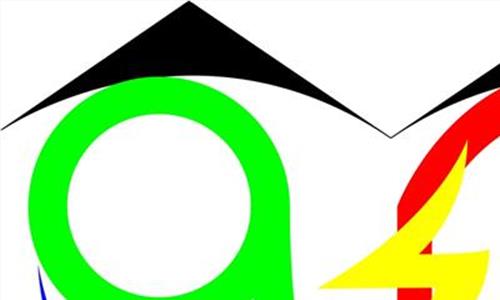“蜀中神屠”自述传奇“刀江湖”[图]
他8岁开始从父解猪,公元1982年封刀,50载屠猪几近二十万头他识遍猪身血脉骨骼,掌膝掐断猪身血脉,闭着眼时,全凭感觉进刀。
江湖最后一个刀客:全凭感觉进刀
大洋网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爷爷,你的江湖呢?我已经没有江湖了。在一个八十岁老人的眼中,江湖不比一盏淡黄的茶水更有味道。
有江湖就有刀。
那你的刀呢?
我已经没有刀了。在我随手的一抛中,刀已经沉睡在湖底。
一个没有江湖和刀的老人,他还有什么呢?骄傲。
还有呢?
鄙视。
鄙视?
是的,不尊重刀的人都将得到鄙视。
———《刀江湖》
落寞 那一个不如清茶的江湖
墙是断墙。茶馆是一家无名的小茶馆。
椅子是三条腿的残椅,桌子是堆满油腻的木板,甚至可以怀疑歪声恶气的堂倌抓来的到底是茶叶还是灰尘。
夕阳从烟熏火燎的断墙照进来。阳光似乎也脏得满身油腻。
有茶馆的地方就有人喝茶,所以这里也有很多人在喝茶。茶馆和菜市场一样,是最有趣的地方,因为你可以在茶馆找到很多奇怪的人,甚至三条腿的人。
当然,在这家茶馆你要觉得无趣了,这里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普通。事实上,这里像成都城所有的下等茶馆一样,来的都是走卒贩夫之流。
而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样的人是无趣的。岂但无趣,简直无趣至极。
如果在这些人中一定要找一个稍微有趣一点的人,有人会说是那个粉擦得往地上掉的女人,也有人会说那个对着女人挤眼睛的汉子,甚至有人会说是那个跑堂的小伙子,因为他有两撇小胡子。
没有人会说是那位默默喝茶的老人。
这个老人岂但无趣,简直无趣至极;岂但无趣至极,简直面目可憎。他脸上的油腻不比他身上的衣服少,他衣服上的油腻不比桌子上的少,而桌子上的油腻,刮下来炒一顿菜还有余。
而且,他剩下的两颗牙齿就像霉烂了的花生,他肮脏的胡子上面还挂着几片茶叶。
你说,这样的人还会有趣?没有人知道,老人堪称“蜀中首席杀猪匠”———一个真正的刀客。
老人曾洪根,1924年生人,祖习屠术,8岁开始从父解猪,公元1982年封刀,凡50载,屠猪几近20万头。
他杀猪如麻。
现在,老人只在夕阳残垣下,捧一盏清茶,将日子慢慢啜吸,过着日啖猪肉逾斤的日子。
骄傲 那一瞥凉入骨的藐视
近日江湖,刀光闪耀,纷纷有屠者扯旗而呼,自号第一刀客。
老人啜啜茶:“你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些呢?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江湖会比一盏淡黄的茶水更有味道吗?”
老人的眼睛里有一抹冰凉,面对这一抹眼神,你会有冷水漫过每一寸骨骼的绝望。
因为,那里面写着藐视。真正参透江湖,就是远离江湖。东瀛围棋老人加藤正夫有言,在那些真正世外高手眼里,或许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可笑,我们真的懂围棋吗?
因为,真正的围棋是道。
那么屠艺呢?
在老人眼里,那些扯旗而号的刀客真正懂屠艺吗?
老人说,“不谈这些,我们喝茶吧。”
怀恋 那一头无法释怀的猪
“我已识遍猪身血脉骨骼,掌膝掐断猪身血脉,闭着眼时,全凭感觉进刀!”
“寻常两三百斤的猪,不会让我的目光作超过一分钟的停留,因为,在我的眼里,它们和一只苍蝇或者一只蛾子没有区别。”
老人8岁学艺,其始,老人父亲只许老人观摩,不教持刀。老人之父如此训诫:“刀乃珍重之物,轻动不祥。”如是三年,一日,老人之父欲屠解一肥硕之猪,老人出语:“肩胛之肉过肥,不算好猪!”老人之父赞叹:目无全猪,技成!
此后,老人开始独立屠猪,是公元1935年,老人年方11岁。怀揣雪亮一刃,杀遍古城成都,从东门杀到西门,从西门杀到北门。见过民国的青天白日旗,掠过抗日的滚滚烽火……
一路杀来,雄鸡一唱天下白,老人成为人民共和国成都肉联厂一屠宰师,有什么杀不了的大猪、歪猪、恶猪,待到老人持刀而去,迎刃而解。
人言,老人屠术已至化境。解放前,川中名人刁文俊每到年关,必重金迎纳老人解猪。
某年,刁夫人刁难老人,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算功夫,白进白出方显本领!”老人不作一言,面对二百余斤之猪,欺身而上,膝压猪腹,肘击猪颈脉,双眼闭成一条线,柳叶尖刀顺势送进猪喉,抽刀而出,刀身米粒大的血珠也无。
老人持刀示人,众人无不咋舌惊叹,刁文俊封银圆4个作谢。
从此,老人“蜀中神屠”之名传遍蓉城。事后,有人问老人白进白出秘诀何在,老人笑笑,“我已识遍猪身血脉骨骼,掌膝掐断猪身血脉,闭着眼时,全凭感觉进刀!”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之际,肉联厂得一大猪,毛重600斤,獠牙钢腿,见屠夫而不避,只以尺长之喙拱得众屠师绕院奔逃。时老人正在院外一小摊择肉而啖,听得人叫猪号,叹道:“什么鸟猪,恁般猖狂!”长身持刀,绕猪三圈。恶猪人立而起,似欲噬人,众人皆屏住呼吸,不敢少动。
少顷,老人一声长叫,挺刀进身,旋风般冲向人立之猪。白光闪过,有殷红血液从猪喉喷涌而出,老人满身血花,有如穿了一件斑彩衣衫。大猪一声闷哼,颓然倒地,有如一座小山。
老人长叹:好猪,好猪!“我再没有杀过那么令我充满回忆的猪了。从那以后,寻常两三百斤的猪,不会让我的目光作超过一分钟的停留,因为,在我的眼里,它们和一只苍蝇或者一只蛾子没有区别。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失去了解猪的乐趣。”
“而我追求的是乐趣。”
留念 那一把风情万种的刀
从开始屠猪,到1982年封刀,五十多年,老人没换过一把刀。肉联厂行屠二十余年的杨姓老人曾见过曾老的刀,“那是一把长约一尺二寸的小刀,宽不过两指,刃薄如柳叶,锋利得刀光也可杀人”。
老人的刀是民国时同城一佚名老匠人所制。为制此刀,佚名匠人封门半月,白日不闻打制之声,夜晚方见火花纷飞。当匠人捧刀出门时,人已枯瘦如柴。
“刀不是一种器具,他是屠者身体的一部分,它甚至会感觉,会疼痛。”老人昏暗的眼睛闪过雪亮的光芒,“刀是利器中至钝至利者,刀背其厚如指,是不杀之钝,刀刃其薄如纸,是必杀之利,刀没有剑的贵族气息,直如隐于莽莽的英雄。”
老人封刀后,曾有后生缠着老人要学屠艺。老人不传,只在夜里,缓缓抚过刀背,刀身,刀锋,有一点冰凉,在他的手心滑动。刀光映亮老人的眼睛,他微笑着。“不传,死也不传!”
为何不传?
“现在的人,视刀若草芥,怎么可传?”
一个薄雾迷茫的秋晨,老人怀揣柳叶尖刀,绕石灰街附近一湖徐行,行至三圈,扬手飞刀,刀坠湖底。回看坠刀处,却无些微波澜。
在屠者这个古老的行业中,有一条亘古相传的规矩,临终之时,必见所持之刀方可闭眼。
但现今湖已不见,刀自渺渺。老人遗言:我死,飨我以清清湖水。(天府早报 记者罗巨浪李威实习记者童仁剑实习生马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