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子思 子思的“诚”与孟子的“心”
邹城是我在部队时住过的地方。我曾在那里练武、支农,1970年当排长时还在农场种了一年稻子,当指导员时带领一个连所建的营房至今还座落在城东。这里留着我当时的火热年华和遐想情怀。我一直对邹城的古文化遗址有着浓厚兴趣和特殊倾心。
记得曾因见到在铁山西侧有人采石直接危及山坡上的古代铭刻即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所凿的佛学经文——号称“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铁山“摩崖刻经”,非常着急,便向有关文物部门反映,得以及时制止。
我还曾采访邹县文管所的王宣先生,写过一篇在文革破坏文物成风的情况下当地农民和解放军协助保护、发掘明鲁王朱檀墓的新闻报道,中国新闻社发了电讯稿,海外许多报纸刊登了此文。邹城的古老传统文化氛围及当地许多朋友既朴实又不乏儒雅的作风,与自己注重以诚待人以心正而处事的习惯十分融洽。
邹城的孟府孟庙是我经常去的地方。令我特别注目的有两块碑刻:一是“子思著中庸处”碑;二是“孟母断机处”碑。据县志所记,子思碑是子思的第七十三代孙孔庆镕于道光年间所立。听说相传元代、明代时孟庙里有碑文记录,现在的孟庙以北有子思书院,子思常在此讲学。
但此石碑现已找不到了。而孟母碑据说系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君于道光年间所立。《三字经》言:“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三迁、孟母断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使孟母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伟大母性而影响深远。
我住邹城那时很年轻,对中国思想史缺乏深入研究。后来在自己的学术涉猎中,特别关注了思孟学说,脑子里常常闪出这几块碑刻。前不久,有事到邹城去,特别又到这两个碑前看了看。这次是基于对思想史有了些见解后来看的,所以想得就更多了。现在想到的多是思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建树,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中的地位。
子思系孔子之孙,名伋,据说曾业于曾子,留下来的主要著作是,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藏于现曲阜孔府附近后称“鲁壁”之中而在汉代重新发现幸免失传的《中庸》。人们通常基于《中庸》里的某些话,认为可能有后人相加,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著作,但对《中庸》的主要思想是战国时期子思之儒的学说并无多少疑义。
《中庸》里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是“诚”。我所著《中西哲学方法史研究》、《塑造论哲学导引》等书中,曾经把古中国哲学中子思的“诚”和老子的“道”比较于古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德的“存在”和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着实仔细地进行了一番研究。在我看来:
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曾经由注重于思考世界基质本原和“逻格斯”的关系,侧重点是对象结构,是物的“有”,于是紧接着的是巴门尼德把关注点聚焦于统摄多种多样自然世界的“有”或“存在”;那么古中国哲学则曾经由注重于思考世界运行本原和“道”的关系,侧重点是对象功能,是人的“成”,紧接着的是子思把关注点聚焦于统摄多种多样人事世界的“成”或“诚”。
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中,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与巴门尼德的“存在”相比较,前者只有运行本原的意义,基质本原是用另外的概念表示的;而后者则把基质和运行都概括到了其中,由此来确立其哲学最高范畴的意义。
与这种情况相类似,老子哲学中的“道”与子思哲学中的“诚”相比较,前者偏重于运行本原的意义,一讲物的构成就损失其形而上的性质;而后者则把功能和运行都概括到了其中,由此来确立其哲学最高范畴的意义。
可见,从老子的“道”到子思的“诚”其发展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后者的产生是前一个哲学体系所形成的“洪水期”之继续奔流。因为,老子哲学由其哲学最高范畴“道”的缺陷而提出了一个“无”,这是在其哲学逻辑推演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范畴。
然而,这却已是某种新的最高范畴涌出并被确立的“洪水前期”。因为讲到“无”即“没有”(或“不成”),它的否定便是“有成”(或“诚”)。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在其演进中由“逻格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自己规定自己并体现基质与运行统一的最高范畴,即巴门尼德的“存在”;那么,古中国哲学则是在其演进中由“道”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自己规定自己并体现功能与运行统一的最高范畴,即《中庸》里的“诚”。
《中庸》是这样来构成其哲学范畴体系的。同巴门尼德要突出“存在”这个形而上范畴是基于把标志现象界的概念与标志统摄现象界的概念区分开来相仿佛。子思提出“诚”这个形而上范畴,首先是基于把“人之道”和“天之道”进一步区分开来。
关于这种区别,子思前后多有所论。子产有“天道远,人道迩”之说。孔子在其学说中总的说是多讲人道,却也有“天志于道”的说法。老子书也提到了天之道与人之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但这里的天道人道充其量都是道。类似巴门尼德区分了“两个世界”并以“存在”和已经与“千变万化的世界”相区别了的“不变不动的世界”相联系;子思区分了天之道人之道并以“诚”和已经与“人之道”相区别了的“天之道”相联系。
子思哲学讲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那这个“诚”的规定性是什么?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规定它,其规定性唯在于它自身,即所谓“诚者,自成也”。这又如同巴门尼德的“存在”一样,存在唯在于它存在,别无其它东西能规定之。
所不同的只是“存在”与“逻格斯”相比,重在对基质有“在”的概括,而“诚”与“道”相比则重在对功能有“成”的概括。因为这里的“自成”便是强调了它能够自己成为的功能,其所谓“不诚无物”,便是讲只有通过它的功能才成就万物。
由此“诚”当然也就带有了足够的普遍必然性。正如子思哲学所强调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故至诚无息”。“悠久,所以成物也”。
“无为而成”“至诚如神”,“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总之,由至诚,展及万物,奇妙不可测度,有了“诚”,“天地之道可一言尽也”。
可见,在《中庸》的哲学体系里,“诚”这个最高的、达到“诚,自成”的、似乎其规定性唯在于它自身的范畴,与巴门尼德的“存在”这个最高的、达到“存在,唯在于它存在”的、似乎其规定性只在于它自身的范畴相类似,在其哲学形而上性质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我在其他著作中,曾专门对哲学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在于由人的塑造之物实现双面映照进行过揭示。《中庸》对于“诚”的论证,特别体现着哲学的双面映照,它在《中庸》里本身是个一语双关的概念。一方面,讲“诚”“自成”并与“道”“自道”联系故“诚者,天之道也”,它在“物之始终”,“不诚天物”;这是物能够成为的“诚”。
另方面,讲“君子诚之为贵”强调“道不远人”并与“至诚之道,可以前知”相联系,故“诚之者,人之道也”,所以“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是人使之成为的“诚”。
这里,“能够成为”的“诚”和“使之成为”的“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事物之成为”和“人事成之为”用一字概之;把两个方面溶为一个范畴看作是整个世界的根本;这不能不说是充分体现古代中国哲学特征的绝妙的哲学思考。
《中庸》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诚”,对以往及当时的重要哲学概念作了解释。例如,其中特别强调了“中庸”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文字中,“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庸”有平常、常道、用等等的含义。“中庸”在文献中合称,目前所知早见于孔子《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从诚出发托孔子的名义在答问中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的作者还直接结合对什么是“中”加以解释,提出了“中和”的概念,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随之,书中以“子曰”的形式对中庸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联系如前所说“诚”的两方面意义,子思强调中庸无非是在指明:诚对于天之道来讲,在于适中;诚对于人之道来说,在于求中。这种基于“诚”对“中庸”所做出的哲学论述,体现着人的行为与对象世界的同律,而且是既贯于主体又贯于客体。
这与当时人们所重视的哲学范畴“仁”形成了很好的联结,因而与孔子哲学相比,由于子思哲学提出了一个更加形而上的范畴,从而给“仁”提供了更深厚的哲学基础。对作为孔子哲学之核心的“仁”,《中庸》里写道:“君子诚之为贵”而“诚者,非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显然,这先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诚”即“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成己,仁也”。
可是“诚者,非诚己而已”,还要“成物”,这就要“知也”。目的是“合内外之道”。因为《中庸》里讲过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道,自道也”;一方面“道不远人”。
显然,只有“成己成物”结合,“内外之道”结合,“天之道人之道”结合,才符合“性之德也”,即出于本性的德。注意,这里的“德”是老子《道德经》意义上的“德”,是“天道”“人道”得以合一的“德”。
可见,在《中庸》里,“仁”只是“成己成物”“天之道人之道”中的一个方面,只有这一个方面是不能达到是“性之德”的。怎样才能达到“性之德”呢?这就内在地包含着一个问题:即这个“性之德”与“诚”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为此《中庸》抓住“性”这个概念进行了论述。《中庸》论证道:“自明诚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教,修道之谓教。”所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至此“成己”的“仁”与“成物”的“知”才得以统一。由“尽性”而达到的这种统一,是天之道人之道的“天人相与”的统一,也可认为是追求人与世界的统一,是世界“自成”与人“成之”的统一,是“无为”和“有为”的统一,是自然塑造人而“成”与人塑造人自然而“成”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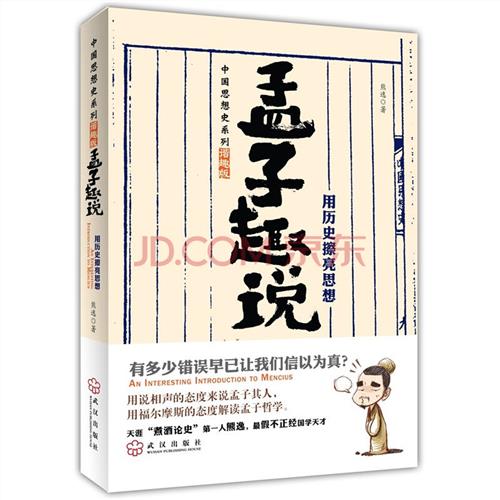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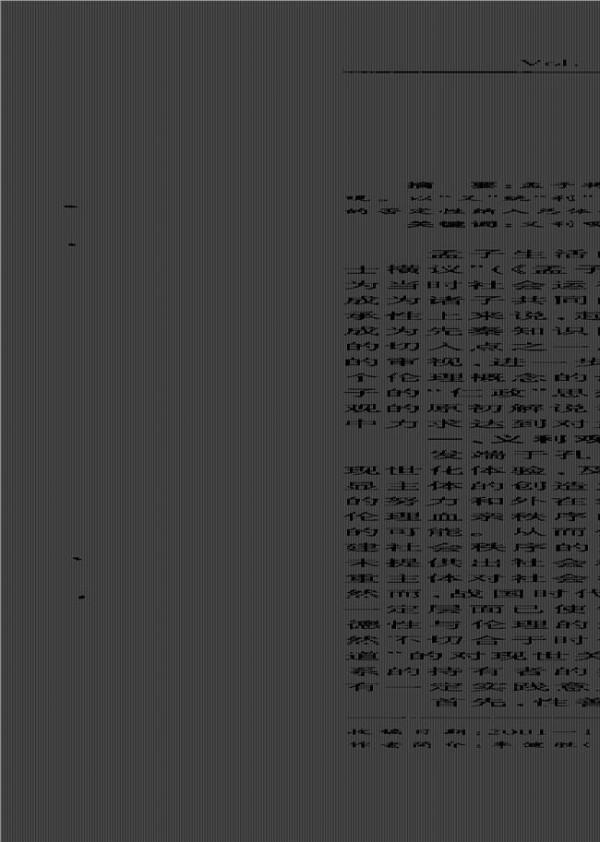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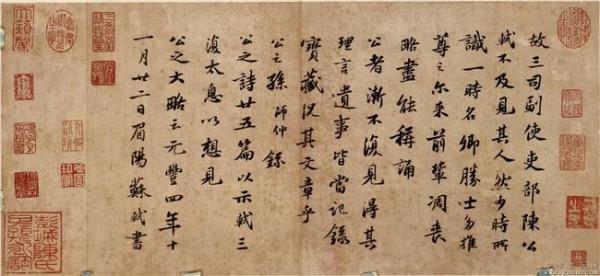
![>子思是孔子的谁 [考证]孟子“十五志于学” 他的老师是谁](https://pic.bilezu.com/upload/4/29/429ec7aae9e5dbb0166bc5eee620ffc8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