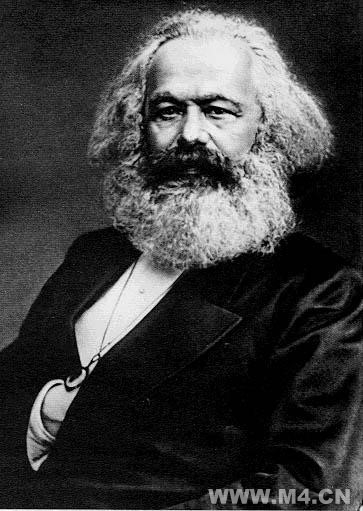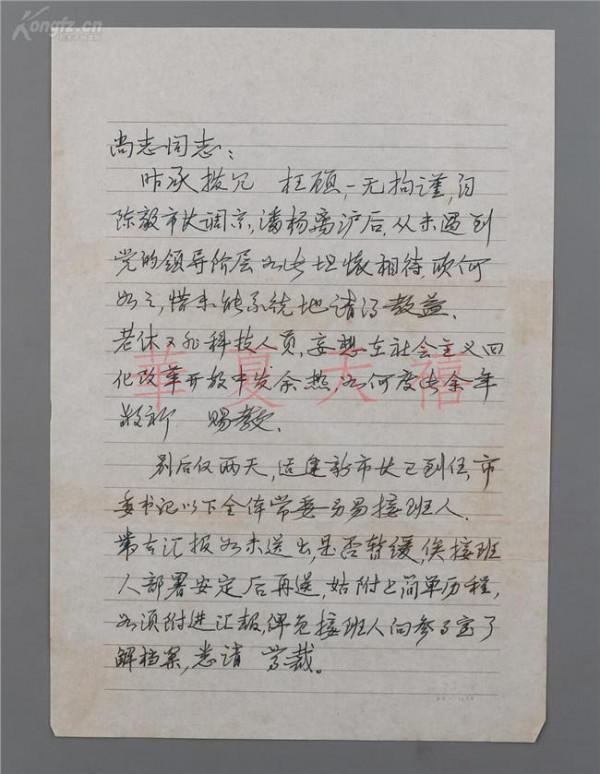谭平山为何被开除出党 共产国际的替罪羊:陈独秀为何被开除出党
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并且成为陈独秀接着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保卫苏联”。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指示苏联、中国和各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拥护斯大林的路线”。所以,中国托派也始终把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批判成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或敢于对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托洛茨基提出的“保卫苏联”口号表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气。为此,陈独秀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打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被开除出党
如上所说,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之所以被中央视为原则的错误,一是这个意见是直接反对共产国际的,而共产国际在当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是因为当时陈独秀正在转向托派,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而陈独秀的矛头都指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
不仅如此,陈独秀这时还同周围意见相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在党内活动,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件给他们看,宣传托派的主张,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从而在党内造成混乱和分裂,到1929年11月他们被开除时,发展到五六十人。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的这种非组织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6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指出:“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不留恋地开除出去”。
对于陈独秀8.5信中的意见和刊登在党报上的要求,党中央予以拒绝。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
陈就指责中央“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并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织活动升级。
10月6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要陈独秀,“必须立即停止超越组织的活动”;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组织生活。
可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宣称:“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接着,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因为中共的党制,从陈独秀创立开始,就不允许在党内有不同的路线,不允许有反对派。所以,如果他们还想留在党内,应该悬崖勒马。但他们觉得自己握有真理,又有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后,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于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他们“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国际审批。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然而,陈独秀在2月27日回信时却在全面而猛烈抨击国际和中共路线后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就这样,陈独秀被无可挽回地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他们在党內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存亡的大问题。
这种情况与瞿秋白的情况成为鲜明对比。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就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因此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极其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他的倔强的个性和敏锐的思想,因此他有很强的反叛精神,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独立思考,敢于为追求真理而斗争(虽然他有时不一定正确);大革命中,受组织原则的约束,他在被迫执行国际路线时,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之后,他就不再接受自己不同意的意旨,不管它来自何方,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瞿秋白与他相反,早年曾信奉主张消极退让、避世厌世的佛教和庄子学说;五四时期转信民主主义时,这种思想在西方已成强弩之末,而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却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为瞿所倾倒;接着,1920—1923年,瞿又在莫斯科待了三年,认真研究了马列主义,同时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因此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更加削弱,而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甚至把尊重上级,服从组织当作最高原则来执行。
再加上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检查的在矛盾斗争中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即“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使他始终不能为坚持真理而顽强斗争,而总是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甚至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王明“左倾”集团的错误打击时,也不愿抗争,而采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态度。
这种情况说明,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瞿秋白是十分软弱的。当然,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他有他的难言之隐。对于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委屈,即使在他临终前写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那篇长篇自白书《多余的话》中,也丝毫没有一点怨言,而只是进行自责和麻痹自己。
他虽然因此不像陈独秀那样被开除出党而留在了党内,但却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说1931年初被王明集团开除后,“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
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请看,一个在1924年回国和1927年上海第二次工人暴动时,那样勇敢地写文章与领导层的错误路线进行勇敢批判的战士,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麻木不仁、作贱自己的懦夫,说明近十年的党内斗争多么的残忍,完全杀死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
一个是在党内斗争中不能或不敢与错误倾向错误路线作斗争,一个是在这种斗争中不计后果。说明二人都是书生革命家,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后来的毛泽东与他们不一样,既能抵制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克服党内错误倾向,执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路线,又能较好地保护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