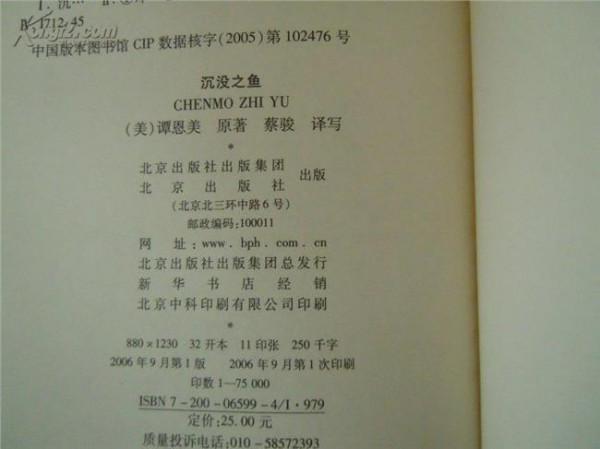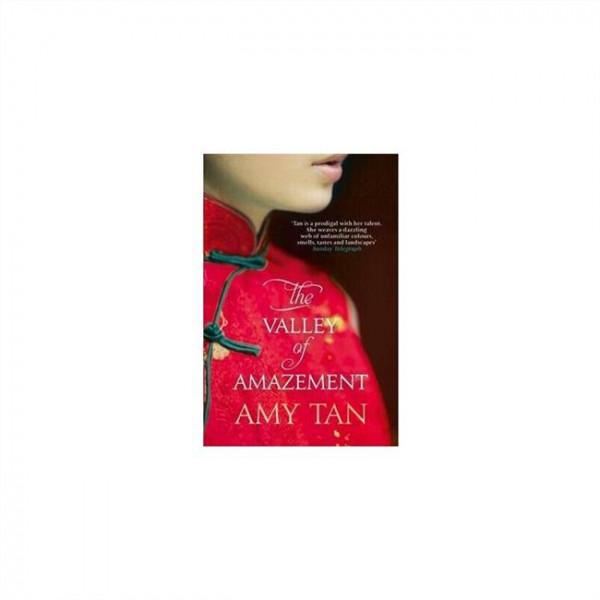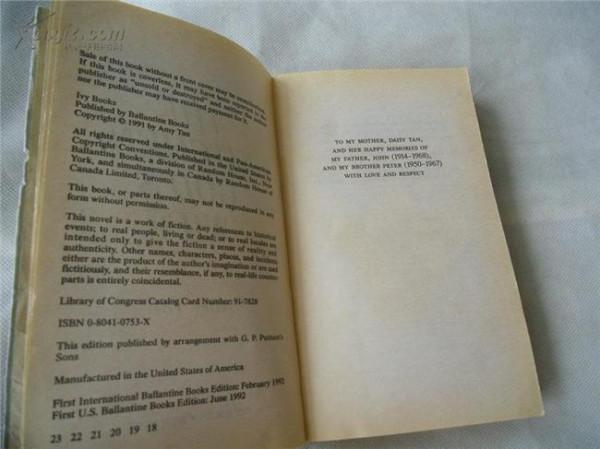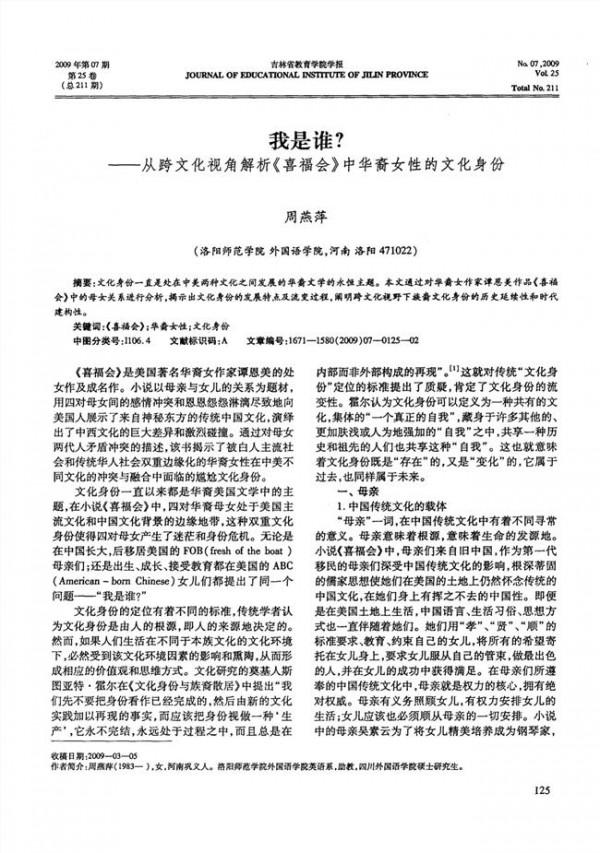谭恩美祖籍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妈妈读我的东西时会哭
谭恩美,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1985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七年随母亲回返中国探亲,访问和寻根。谭恩美成名作是《喜福会》,1994年由王颖导演拍成电影上映后,她成为美国华裔家喻户晓的作家。她的作品还有《灶神爹之妻》、《百种神秘感觉》、《接骨师之女》、《沉默之鱼》等。
记者 景锦 谢海涛 摄影 武传华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
谭恩美,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1985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七年随母亲回返中国探亲,访问和寻根。谭恩美成名作是《喜福会》,1994年由王颖导演拍成电影上映后,她成为美国华裔家喻户晓的作家。她的作品还有《灶神爹之妻》、《百种神秘感觉》、《接骨师之女》、《沉默之鱼》等。
3月24日,为上海国际文学节而来的谭恩美与记者的见面会,在广东路20号米氏餐厅举行。谭恩美一身红衣,坐在黄褐色沙发上,乌黑的齐耳短发,细致的眉眼,嘴角抿着温和的笑意,50多岁的人,有着三四十岁的容貌,非常东方的面孔。沙发背后的巨大镜子里,映出面前一张一张记者的脸。
那一天,谭恩美的优雅让人想起“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类的话,似乎那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从来没有笼罩过她,那一系列丧父丧兄丧友之痛,那些车祸抢劫,那些家族的劫难,在她身上显不出一丝痕迹,而只是留在了那些小说里,裹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华盛顿邮报》说她是讲故事的天才。上海的评论家说她把中西方文化的对比,散落到细琐如圆桌中餐、家族礼仪等生活的瞬间,其细腻不言而喻;又说,好的小说家是营造氛围的高手,唤云呼雾,酝酿出朦朦胧胧的弥天气场。
生活中,谭恩美的谈话,似乎也有这种效果。整个见面会,她用英文娓娓道来,谈到兴奋处,眼睛发亮,手势翻飞,耳朵上的垂饰轻轻晃动,舒缓英文中会跳出个把中文词语,把周围的女记者们逗得一阵轻笑。
幽默,健谈,有个性。相信命运,又理解与命运相对的途径,谈到苦难时,她依然淡定从容,令人想起她从前说的话:“我曾经觉得自己实在太倒霉了,但再想深一层:有多少人可以像我这样交上这么多坏运却平安无事?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简直幸运得难以置信。”
或许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苦难对有心人总有大馈赠。
那些痛苦,充满色彩感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美国畅销书作家,你笔下刻画的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族史,而书评家往往不能忘却你的中国祖籍,把你的作品标榜为“多元文化的文学”,请问你认为自己是中国式的作家,还是美国式的作家?
谭恩美:如果你要问我是一个美国作家,还是一个中国作家?那么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的作品的背景是美国生活,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生活,我的假设前提是非常美国化的,并不是说一个中国作家不能有这样一个假设背景,只是说我所做假设背景的基础是,我所知道的美国生活是美式的。
南都周刊:1989年,《喜福会》的出版使你一举成名,小说连续数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成为当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这部小说和后来的《接骨师之女》等小说一样,很多情节源自你妈妈和家族的生活。请问你妈妈怎么看待你的小说?
谭恩美:我妈妈是我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妈妈读了第一部分,她说感到非常骄傲,她甚至从没对我说过这句话,“你怎么写得出这些”,当我写一个女性的故事的时候,妈妈说就像写她的母亲,妈妈告诉我,她的母亲死了丈夫,非常伤心,然后她说要再次嫁人了,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她说一切都会好的,然后她就死了。我改写了这个故事,因为从小说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好故事,并不有趣,我于是把这个故事改写了,妈妈读了我的东西后说“你怎么知道事情是怎么继续下去的”。我妈妈的人生有太多的坎坷,她读我的东西时会哭,她说每个读这本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她受了多少苦难,然后她说:“好吧,讲出这个故事吧”。
南都周刊:《华盛顿邮报》说,你是讲故事的天才,你的作品里往往是现实与梦幻的交叉,时空的转换,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种讲故事的风格,最初是借鉴什么人的?
谭恩美:我想是我的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会问她,我的家人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她不会这样告诉我说“哦,1941年我儿子死了”,但是也许有一天,她会把你抱在怀里,把故事的很多细节告诉你:名字,我父亲所在的位置,她所在的地方……她记得每一个细节,让你觉得你就在现场,那就是我从我妈妈那里学到的。如果你运用你的想象写下来,那些画面,那些痛苦,便会更加充满色彩感,更有细节感。
南都周刊:在您成长的过程中,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你,诸如丧父丧兄丧友之痛,而在家族中,你的外祖母年轻守寡,遭强暴后被迫为妾,最后吞生鸦片而亡,你的妈妈目睹其自杀的经过,到美国后,不断威胁要自杀。你说“这种伤痛从一位母亲传到她的女儿,再传给下一代,她们将这种绝望传给了我”。这些苦难对你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谭恩美:在我小的时候,这些事情使得我不停地追问: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为什么我的父亲死了?为什么我的哥哥死了?为什么他们都是死于同一种理由?他们都死于脑疾。我的父亲一直相信上帝,相信上帝能掌控一切,他总是祈祷,我母亲有更多的信仰,比如风水,神灵的愤怒,她相信一切灾难都是因为有一种诅咒。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一直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些使得我看世界的想法会与众不同,我一直在思考关于生命,关于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运转的,设想美好幸福的画面,包括每一个细节。我把这些写在我的作品里。
南都周刊:这些苦难的经历影响到你对基督教的看法了吗?
谭恩美:我的家人,他们虔诚地相信耶稣,他们很虔诚,相信耶稣可以裁决一切,试图求救于基督,结果他们死了,或者终身带着一种神秘的诅咒,而且永无休止,这种诅咒一直燃烧着,我并不想自己的命运受到这样的控制,我有我自己的信仰,我的偏见并不是针对于耶稣,或者是对于那些迷信耶稣的人们。
南都周刊:你也说过“我的一生非常波折,这非常好,生活应该充满惊奇,你不要想苦难,但是一旦遇到,就要学会控制它们,借此发现。这些发现能够让我继续,使我坚强,让我不失幽默和希望。”评论家说,饱受苦难的谭恩美,试图通过小说探讨“什么是我们应对他人苦难的最好方法。”现在你得到了这些答案么?
谭恩美:答案……答案就是一切神秘,可能发生的力量,或者什么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答案,美国人不会懂得怎样去寻找唯一的答案,而在中国,也许很多事情都有“对”和“错”,每个人都试图去评价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我想我会感到困扰,答案也许就是去“做”,要去探求,但是也许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大概就是我写书的原因。
我的写作旨在个人生活
南都周刊:在评论家眼里,你笔下的中国人的生活不仅让美国人感到神秘,也让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你的小说里充满着扶乩、占卜、生肖相克、阴曹地府、“龙骨”乃至书法等富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词语。请问你对中国的了解,除了从父母那里获得知识之外,还有哪些渠道?
谭恩美:我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故事,了解西方世界是怎样谈论它们,中国人又是怎样谈论它们,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在哪里。我努力从各种杂志、书籍上了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如何讨论那些故事,那些有关中国神话的食物、建筑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出现过不少错误,我妈妈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记下它们,然后努力写出来,包括一些细节。
南都周刊:有作家(如美籍华裔作家赵健秀)认为,你在《喜福会》中描述的中国文化是伪造的,根本就不存在那样的中国文化。你在一个伪中国童话中,刻画了一个伪华裔母亲。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谭恩美:在每个国家,都有人这么批评说:“哦,她描述的是美国生活,但是美国人却不那样生活。”你知道,部分画面也许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或其家庭的写照,事实上当你手上拿着一本书的时候,你常常不是基于这本书所写的文化背景来阅读的,人们总是想找到一种纯粹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但其实这种方式不存在,所以有人批评说我可能写的并不是中国文化,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人不一定要在所在的城市空间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写的部分内容很可能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经历过,我希望有人看到我的书时会说:“哦,你在写的是什么,你写的是什么地方,也许我从没经历过,但它确实存在于我的记忆中”,那就是有趣的。
南都周刊: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里,在母女关系的视角背后,其实是文化的冲突,比如《喜福会》中的母亲,一生都带着不能融入美国文化的伤痛。请问你在最初写作的时候,是否带有这种文化冲突的意识?也有批评者说你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对立起来是伪装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谭恩美:我不认为我那样做过,我并没去读那些评论,也许有很多人认为我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文化”,有的人认为我讲述的根本不是中国人的文化……我并不是要讲述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我写的都是非常个人的东西:一位住在美国的中国母亲,在中国拥有过去的母亲,她经历的痛苦,我经历的痛苦,我们思想上的差异,年代上的差异,她失去了她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过孩子,她爱她的妈妈,她亲眼看着妈妈死去……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我描写的故事并不是旨在文化,而是个人的生活。我想对于每个作者来说,描写他们生活中的苦难,都是一种挑战。
南都周刊:《喜福会》的中文版翻译者、上海作家程乃珊认为《喜福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不同的母女关系融化在点滴小事中,耐人寻味。但也有人说你小说的格局比较小,失之于琐碎,你又如何看待?
谭恩美:我所写的主题不需要很严肃,可以是很琐碎的,甚至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以前认为这种写作方式大概美国才有,但是1985年,我在一家图书馆里看到很多中国作家比如王安忆,她们所写的东西有些是很口语化的、家庭中的故事,你甚至可以把它看作一种自白式的写作。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很多观点被打上中国烙印,虽然我并不算是一个中国人,妈妈常常对我说:“你完全不了解中国,根本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写一本书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多么了解中国,多么了解中国人,只是说在别人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在中国没读过这本书,那就很好,不会有人大叫“你到底在说些什么,那些完全不会发生,完全不是那样”,就很好(笑),我的书能在中国发行,还有那么多人知道它,我觉得非常荣幸。
南都周刊:说到中国文学,去年,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你喜欢哪些中国当代作家?
谭恩美:每个人都有他的观点,难道他要说他的工作也是垃圾么?我读过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觉得很棒,比如莫言、萧红、还有一个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她和陈冲合作的《天浴》很不错。
来到中国了解往事
南都周刊:你说过,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发掘母亲和家人的故事。出生于上海的母亲,深刻影响了你的写作。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母亲就不断用文字记录内心的情感。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作为女人需要熟悉自己的母亲,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作为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作家,1987年你才第一次来到中国,请问这次中国之旅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成行的?对你1989年出版《喜福会》有没有什么影响?
谭恩美:那个时候,我在想母亲可能要离开人世了,但是我意识到我对她所知甚少,甚至不了解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对自己发誓我要去了解她多一些,于是我来了中国,去看她所生活过的地方,去了解一些往事确切地在哪里发生。
南都周刊:1987年在上海,你觉得这个城市和您想象中一样么?
谭恩美:哦,完全不一样。应该说,在我没来上海之前,我对上海的了解还停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时代对我妈妈造成伤害。当我1987年第一次来上海时,我发现上海与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上海是一个很喧闹的地方,每个人走路、说话的方式都很热闹,上海人看到我说话、走路的方式,就会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正像我妈妈一直对我说:在中国,你就是一个美国人。
南都周刊:您最喜欢上海的什么?
谭恩美:我妈妈是上海人,我有姐姐、外甥在上海。我想最喜欢的应该是上海菜吧,我记得我妈妈曾经做上海菜给我吃。我的家人曾多次来过上海,当我走过这里的一条街,看到这里的一条河流时,我就会想象:我妈妈曾经穿过它,我妈妈曾经看过它,我会把这些想象写下来。当然,这一切都变了,这里的每一件事物现在越来越快的速度面目全非,我的家人曾住巨鹿路和常德路上,现在都已经完全不同了。
南都周刊:你说过要把小说《接骨师之女》改编成歌剧,现在进行得怎样了?什么时候来上海、北京演出?
谭恩美:目前正在进行中,我和一位美国作曲家正在合作这个剧目,大概在明年会在三番市初演,然后希望会来亚洲的中国、新加坡演出,时间也会是明年。哦,我不知道何时,或者会不会在上海或者北京演出,这要取决于中国的观众,我不知道北京和上海的观众有怎样期待。
南都周刊:您和斯蒂芬·金组织的乐队Rock Bottom Remainders,现在怎么样了?
谭恩美:我在这个乐队里已经有15年了,很长的时间了,和斯蒂芬·金,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作家譬如Dave Barry一起,几乎每个成员在他们的国家都是非常知名的。有人问我:“哦,你们到底在表演些什么!”我总是告诉他们:“I play the dominator!我扮演着统治者!”统治者会把怜悯施与跟随者,我穿着很魔幻的服装,戴上脖圈、蹬上高筒皮靴,狠狠地抽打面前的人。(以身体语言演示)也许这种表现形式是难以理解的。有时候我们在纽约演出,收入会交给儿童基金会,我们已经用这种方式捐赠了一百万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