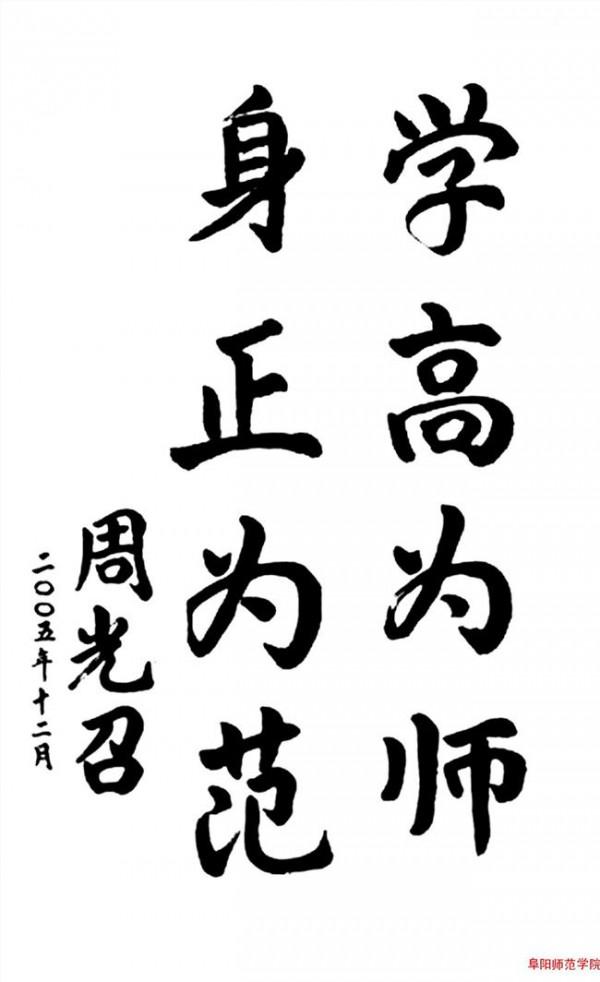陈兴良周光权 陈兴良、周光权等刑法学界21位专家关于“辱母杀人案”的观点汇总
一、法律事件是否只有法律人才有评价资格?
对此,我持否定观点。
在辱母杀人案的讨论中,普通人或许没有法律理性,但这基本上只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法律人有法律人的智识,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清醒。当人家批评你判决不对,量刑不公时,绝对不可以跳起来说:你没有阅卷,亲历庭审,欠缺法律知识,不可以对案件说三道四!
照这样的逻辑,大体上只有审理本案的法官才有资格评论案件。这样做的后果无异于取消言论自由。既然我们承认正义具有普洛透斯式的一张脸,随时变幻莫测,可以呈现不同的形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然如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为什么不能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呢。至少可以给诸位法律人提个醒,来个兼听则明吧?要知道,英美法系中陪审团成员从普通大众中遴选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二、于欢的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
对此,我持否定观点。
正当防卫是一种私力救济,法治社会不允许私力救济泛滥,并非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只是对那些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紧迫性、持续性的不法侵害,在采取防卫行为可以减轻或者避免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诚如邱兴隆教授所言,“本案中,被害人的行为可能涉嫌对被告人方的四方面的权益的侵害:
(1)公司经营秩序,因为在公司里摆烧烤摊与喝酒吃烧烤、多人结伙闯入公司办公场所等属于扰乱公司经营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
(2)人身自由权,因为存在典型的非法拘禁行为;
(3)人格名誉权,因为存在对被告人之母的当众侮辱言行;
(4)健康权,因为有过对被告人的殴打行为。
仅就(3)与(4)而言,一审判由基本成立。因为无论被害方对被告人之母所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言行侮辱,也无论对被告人所施加的殴打有何严重,其均已终止于警察到达现场之后,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因已告完结而不复存在。
然而,被害方并未因警察的介入而离开现场,也未放弃其在办公室内的滋事行为与对被告人方面的非法拘禁状态,尤其是在被告人方面试图随警察离开现场,摆脱被非法拘禁状态时,被害方还公然将被告人方拉回,将其置于继续拘禁状态。而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都是不法乃至犯罪行为,其无疑属于作为法定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邱兴隆:五问刺死辱母者案——限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三、于欢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
关于防卫的必要限度,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基本相适应说认为,防卫行为必须与不法侵害相适应,相适应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相等,而是指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从轻重、大小等方面来衡量大体相适应。必需说认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应从防卫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衡量,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实际需要作为防卫的必要限度。
只要防卫在客观上有必要,防卫强度就可以大于、也可以小于、还可以相当于侵害强度。适当说认为,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人的行为正好足以制止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而没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并认为应将基本相适应说与必需说结合起来进行判断。
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尽管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但以往的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态度,致使公民正当防卫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有鉴于此,1997年刑法修订时,在第20条第2款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规定只有当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
考虑到刑法的这一精神,其中的“必要限度”,应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合理需要为标准。是否必需,应通过全面分析案件得出结论。一方面要分析不法侵害行为的危险程度、侵害者的主观内容,以及双方的手段、强度、人员多少与强弱、在现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形势等。
防卫工具通常是由现场的客观环境决定的,防卫人往往只能在现场获得最顺手的工具,一般不能要求防卫人在现场选择比较缓和的工具。
问题在于如何使用防卫工具即防卫强度问题(包括打击部位与力度)。对此应根据各种客观情况,判断防卫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否控制防卫强度、能否控制防卫强度。另一方面,还应权衡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性质与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
即所保护的法益与所损害的利益之间,不能相差过大,不能为了保护微小权益而造成不法侵害者重伤或者死亡,即使是非杀死侵害人不能保护微小法益的情况下,也不能认为杀死不法侵害人是必需的。(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本案中,面对不法侵害人的挑衅,于欢先是忍,在警察到来后其欲求助于公力救济。当发现公权力无意介入此类事件时,事态进一步升级。“派出所的民警到了,派出所的人劝说别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况了。其他人让我坐到沙发上,我不配合,有一个人就扣住我的脖子把我往接待室带,我不愿意动,他们就开始打我了。
”于是“我就从桌子上拿刀子朝着他们指了指,说别过来。结果,他们过来还是继续打我,我就拿刀子冲围着我的人肚子上攘了一刀,一共攘了几个人记不清了,不是两个就是三个。我攘了他们以后,派出所的人又进屋了,制止了以后的行动,就把我带来派出所来了。”(聊城中院判决书中于欢的供述)。
试想当求助于公权力都不使自己摆脱不法侵害的状态时,于欢心中该是如何恐惧、悲愤?此时,我们还能再苛责于欢为何不拣一把水果刀之外的轻缓的工具吗?尽管如此,本文也不认为于欢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要知,于欢的防卫行为最终还是造成了一死两重伤外加一轻伤的结果。与寻衅滋事中、非法拘禁可能造成的结果相比较,应当说结果明显过当。据此,本文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必须说明的是,此时不法侵害人是否对于欢进行了殴打,双方陈述并不一致。如犯罪嫌疑人郭彦刚的供述即为:“我们这边的人说‘不能走,恁欠俺的钱不能走’。我们让于欢坐沙发上,于欢不坐。他走到办公桌南边那里去了。我们几个人也跟着过去了。”(聊城中院判决书中郭彦刚的陈述)。但在寻衅滋事、不法拘禁侵害状态的持续下,不法侵害方有无殴打行为丝毫不影响于欢行为成立防卫过当。
四、于欢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防卫过当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罪名,通说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要么是间接故意,要么是过失。当于欢的行为造成一死两重任伤一轻伤的情况下,是认定为间接故意的故意杀人罪,还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呢?对此,我认同后者。
“正如一审所正确指出的一样,被告人虽对多人实施了刺击,但对单个被害人没有刺击的连续性,足以表明被告人不持有非致人于死不可的杀人心态,尤其‘一顿乱捅’的状态下,被告人对所实施的刺激部位并无明确的选择,更辅证了其不是基于杀人心理支配下选择致命部位而刺击之;在犯罪后,面对被害方仓皇逃离,被告人本可继续追击却原地等待,束手就擒,也印证了被告人适可而止,不具有杀人的故意。
因此,一审将本案定性为故意伤害而非故意杀人,于法于理均无可挑剔。” (邱兴隆:五问刺死辱母者案——限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据此,于欢的行为成立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罪。
五、于欢的行为是否需要从轻处罚?
对此,我持肯定意见。
首先,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其次,于欢存在自首情节。在冲突升级后,苏银霞证实,“110 民警听见动静又回接待室,民警给我儿子要刀子,于欢说:‘他们出去了,我就把刀子给您。’对方的人都出去了,我儿子于欢把刀子给民警了,然后民警就把我和我儿子带到派出所了。”(聊城中院判决书中苏银霞的证言)。
根据2010年12月22日最高法《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具体问题的意见》第1条的规定: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此后,于欢到派出所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刑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六、于欢是否存在责任减轻事由?
对此,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依照三阶层的犯罪理论,一个行为如欲成立犯罪,需接受三个阶段的检验: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有责性不仅存在有无的问题,还存在高低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德国刑法典》第33条规定了关于防卫过当的宽恕罪责事由(Entschuldigungsgrund)——“如果行为人出于惶惑、害怕或惊恐而逾越了紧急防卫的界限,那么不对其进行处罚。
”(参见公众号“德国刑法小站”:《如何从德国刑法的角度为“辱母杀人案”出罪》)
对此,霍姆斯早就说过,“面对一把举起的刀,不可能要求一个人进行冷静的思考”“具体到本案,当行为人亲自目睹自己的母亲受到极端凌辱时,法官是否应扪心自问:任何人在此情形下,会平心静气的忍受凌辱吗,刑法究竟是在鼓励人们依法抗暴,还是逼着人们忍受凌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被辱也不反抗?即使是防卫过当,判得是不是太重了。
我们期待着司法人员反思:司法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刑法要不要调整正当防卫的法定要件?刑法理论要不要更加关注社会需要和经验常识?法律人不要过于自负,以为自己才是法律精神的权威阐释者,否则,没有人会把恶法和错误的司法实践当回事的。
”(陈瑞华谈于欢案:正当防卫的法定要件和司法的社会功能都值得反思)。
退一万步讲,即使认为本案中于欢不成立防卫过当、不存在自首情节,只成立单纯的故意伤害罪。此时,我们也应该透过冰冷的法条给予于欢一些人性化的关怀。诚所谓法条是冰冷的,但判决应该是温情的;无情的法律亦需有情的阐释。“刑法重要,重不过社稷,刑法高尚,高不过政策,刑法伟大,大不过人性。”(公众号“中外刑事法前沿”, 毛逸潇:《对不起,刑法让你失望了:于欢案观点统疏》)。
推己及人,换位思考,或许这正是聊城中院判决书中,法官考虑再三后,只对于欢判处无期徒刑的原因。但正如许霆案一样,即使判无期,国人感觉还是重了。既然如此,为何我们不能多一点人性化的考虑,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减轻处罚的规定呢?“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来自微博:乐毅的刑法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