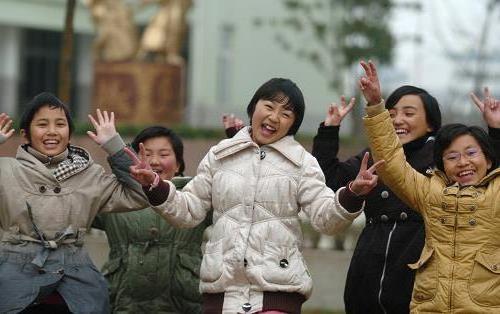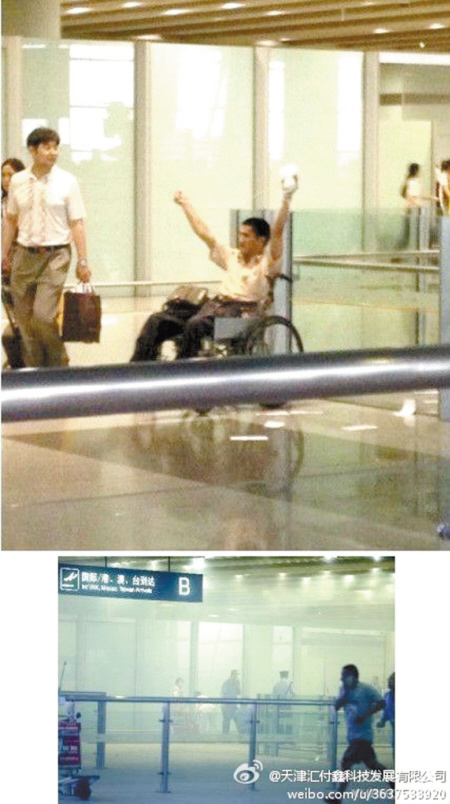罗浩:走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圆
罗浩有一幅摄影作品,名叫《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这是一个终点》,画面上,一只迷茫的羊正望着牛粪垛思索。罗浩说他离开拉萨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回来,但在离开拉萨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确在策划着“完全回来”。
罗浩摄影作品《走了很远才发现这是一个终点》。
据《西藏商报》报道,上世纪80年代的拉萨还是一个只拥有10万人口的小城,没有好的饭店,商店也只有罐头、饼干、固体酱油这些简单的商品出售。但在这一时期的西藏诞生了我们现在看来是能代表当时的文艺现象的多项作品,其中包括画家于晓冬的油画《干杯,西藏》、青年摄影家罗浩的摄影作品《对话》,前者集中了一大批当时拉萨文艺界的代表人物,象征一个时代的梦想,后者则堪称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作品。这两幅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的拉萨文艺界在艺术追求上是领先于内地的。
2008年6月,在北京“798”艺术工厂一个名为《对话》的摄影展上,我们重温了罗浩的那张经典摄影作品《对话》:几个艺术家赤身裸体,面向珠峰盘腿而坐。这张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照片后来在1998年罗浩漂流雅鲁藏布江时在形式上得到复制:在雅鲁藏布江的源头杰马央宗冰川上,他们又来了一次这样的行为艺术。
罗浩的父亲罗伟是解放军第18军的随军摄影师,受其父影响,从小在拉萨长大的罗浩在十几岁就爱上了摄影,他在16岁时就获得第一份工作,任西藏自治区展览馆的摄影师,从此他在摄影路上一发不可收拾,不停获奖,不停发表作品,至1987年罗浩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他发现,仅仅依靠他那些摄影作品的稿费,他在同学中就算是非常富有的学生了,还能经常请同学们下下小馆子、喝个小酒。
上世纪80年代的罗浩拥有众多光耀的头环:1984年,他20岁时即任西藏摄影家协会秘书长;由于在摄影方面成绩突出,21岁即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22岁时入选《西藏当代文化名人》一书。但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他对当时的荣誉和头衔已印象不深,那个时段除了留下一些让他现在仍引以为傲的照片,让他现在仍念念不忘的,是一个时代。在他看来,那时物质贫乏但精神富足。有些人说,今天的拉萨物质已经丰富了,但精神上开始空虚,罗浩却说,再怎么变,拉萨还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1987年,罗浩从人民大学毕业回到拉萨,这时的拉萨已经成为外国游客们梦寐以求的旅游热地,罗浩和人合伙在布达拉宫下开了一家图片冲印社,挣老外的钱。那两年挣钱倒是快,他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越野车,开去阿里,回来时,那辆车只能当废品卖。
在于晓冬的油画《干杯,西藏》上,大概是因为个子高,罗浩站在画面上的最后一排。在上世纪90年代,画面上的这些人陆续离开西藏,有人已去世,有人出国,有人回到故乡,罗浩也回到四川成都定居,在社会变迁中不停地转换着身份,他开过茶馆、酒吧,也拍过广告,搞过特种旅游,开过文化公司,还出过一本书《干杯,西藏》,策划出版过一系列关于西藏旅游的丛书,结果发现都是玩玩而已。他还参加了“98中国科考探险漂流雅鲁藏布江”活动,可无人喝彩。这时他才发现大家忙的不再是为英雄壮举喝彩,而忙的是挣钱。
这张照片摄于1998年10月,当时罗浩正在漂流世界上最高的河流之一——雅鲁藏布江。
2007年时,罗浩说,其实他已经离开摄影很久了,现在大家谈及的,都是他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这年年底,他加入《西藏人文地理》杂志,任执行主编。在主持这本号称“在世界和西藏之间”的杂志工作时,罗浩时常对杂志社的编辑和记者们说,你们一定要用平视的角度报道西藏,不要仰视妖娆西藏,更不能俯视想拯救西藏。
西藏商报:曾有人将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西藏的一批文化人称之为“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你作为其中的一员,还经常与这一群体的人保持联系吗?
罗浩:不能说是“最后”,因为我们如果都“最后”了,那在西藏长大或现在到西藏来的理想者、思想者怎么称呼啊?呵呵。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没有那么崇高,我的父辈可能能用这个称号,我们不能。
这个问题其实很不愿意回答,因为回想起来会很心酸。
就拿于晓冬的油画《干杯,西藏》来说吧,里面的人现在都天各一方,有杳无音讯的、有逝去的、有去了国外的、有回到各自家乡的。在国内的朋友当然能够经常聚聚是再好不过的了。我希望他们都很好,特别是身体好,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也开始进入“老年”了。
我们这帮人在一米远和在一万米远的感觉是一样的,明白嘛?是精神距离,不是物理距离。
西藏商报:促使这种联系得以保持的原因你认为有哪些呢?
罗浩:是我们经历了一个艰苦又快乐的年代,和全国那个时代的人差不多。
就好比一次旅行,其实最后留在你脑海里的不是享受的瞬间,而是艰难困苦的时段。人生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积淀下来的记忆不会太多,但只要记住就不会轻易丢失。
西藏商报:离开西藏十多年后,你在经历与文化心境上有何明显的特点?跟其他人有什么相似之处?
罗浩:我们那帮从西藏走出去的人,大多仍然做着文化的事。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在北京我们经常见面的有几个,段锦川、李晓山、牟森、乔艳林、马丽华、陈浩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各自的行业都很出色,许多都是中国大师级人物了。
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在我们各自的工作、生活中我们都很从容,这也许是西藏、西藏人对我们的影响。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有那么厚重的文化背景,我们有西藏生活的积淀。这一点对我很重要,经常还引以为傲。
西藏商报:你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时离开西藏的?如今什么又促使你再次凝望并关注西藏?
罗浩:我们那群人中大多数人离开西藏的时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因很多,各不相同吧。我个人是因为女儿心脏病,我必须带她回到内地动手术、养身体。但是很无奈,心底里不想离开,但是很多事情的结局都不完美,对吧?
我相信每个离开西藏的人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关注西藏,用大家都说的一句话说吧,就是:西藏情结。
来西藏也好,离开西藏也罢,其实没有那么多原因和背景,也没有那么悬乎,就像每一个进进出出西藏的普通人一样,各有各的事。
西藏商报:你认为最初影响你的西藏人文环境跟现在比较起来有何异同?
罗浩:我个人不一样,我基本在西藏长大,所谓的“西藏第二代”。
面对大多数人来说到西藏是种迷惑或者是种传说。当现实和理想发生差异后你不得不承认你在西藏文化面前过于渺小。
你的知识、你的专业不足以表达。
一位朋友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自愿来西藏工作,专业学国画的,但当他第一次坐飞机到贡嘎机场走出机舱那一瞬间,他就决定把画国画的毛笔扔掉,开始画油画。
当我第一次站在阿里札达土林上想用相机拍一张土林全景时,我看了一眼取景框,我瞬间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学电影、电视,相机在这个时候完全不足已表现眼前这个场景。
这是一种文化力量、人文景象、地理差异。所以,西藏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就像我做的《西藏人文地理》杂志一样,很多朋友担心哪有那么多选题可做,我告诉他们,你们放心,别的我不敢说,反正我这辈子做不完。
西藏商报:我们知道,随着西藏热的又一轮升起,你们中大多数人继续回到西藏或是重拾与西藏相关的事务,你认为,这对于你,对于他们而言,是个案行为还是群体意识?
罗浩:不是“回到”或者“重拾”,是大家一直都在从事与西藏有关系的事情。
西藏商报:你认为西藏文化产业大环境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产生群体意识,并进而将西藏文化推动下去?
罗浩:西藏文化产业说实话和内地发达地区相比才刚刚起步,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优秀人才如何培养和引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政府层面要花大功夫,我们只能给政府一些建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造船比较慢,我们不如买船或者租船。这方面有一些例子可以借鉴了,就我们杂志来说就是这样,发展非常迅速。最近还了解到西藏影视也在寻求内地有实力、有想法的公司合作。西藏文化板块的整合也要尽快落实上市,利用市场经济发展西藏文化事业,内地这方面运作得很快,也很红火。
西藏商报:能谈谈你目前所做的工作吗?
罗浩:《西藏人文地理》杂志是目前的主要工作,另外还在参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西藏馆前期策划的相关事务。
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交通如此发达,但是现在内地人、外国人对于西藏的了解还是很片面。举个例子吧,一个北京的80后年轻人问我“拉萨有超市吗?”说老实话听见这样的问题我很震惊,作为一个媒体人也感到有一些悲哀。所以,自然觉得肩负的责任很重。
我到《西藏人文地理》杂志以后,改变了一些做法,我经常跟编辑和记者说,我们做选题一定要用平视的角度报道西藏,不要仰视妖娆西藏,更不能俯视想拯救西藏,这是一个历史同样悠远优秀的民族,我们必须很近地融入其中,就像著名摄影师卡帕说的一样:你想拍出好的照片就必需最大限度地接近你的被摄者。
《西藏人文地理》虽然是一本区域性的地方杂志,但也是西藏的一扇窗户。现实地、公正地、深入地报道今天的西藏,就是把这扇窗户打得更开,让更多人看见和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我们用事实的报道展示一个全新的西藏。当然《西藏人文地理》同样肩负藏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介绍的作用,毕竟我们是人文地理类杂志,而不是新闻周刊。
我们的广告语是:《西藏人文地理》在世界和西藏之间。如果能起到这个桥梁作用,我想,我和我们杂志社的同事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文/记者 陈度 ■图/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