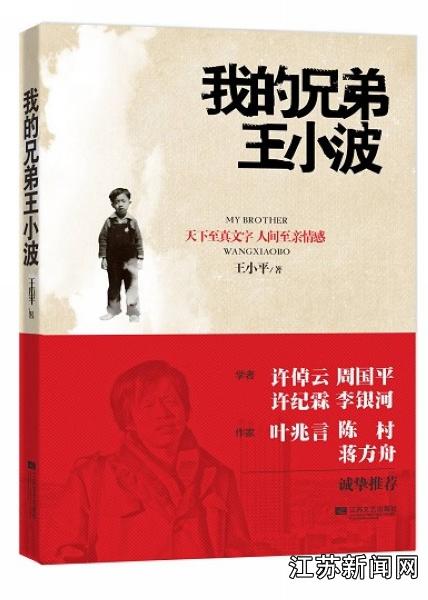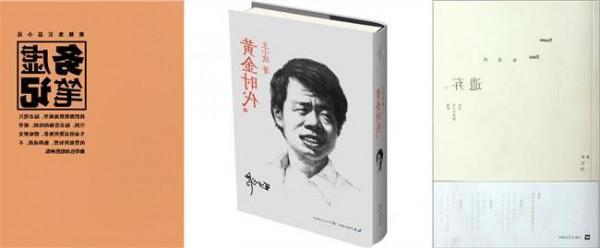王小波逝世20周年 生前寂寞死后哀荣

20年前的今天,1997年4月11日, 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死于京郊寓所。
半个月后的1997年4月26日,八宝山一号大厅外,300多人前来吊唁,据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钟艳玲的回忆,前来吊唁的,除了少部分王小波的亲友,其他都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这段回忆像是王小波与”文坛“关系的一个比喻。在活着的时候,王小波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作品并不多。1991年,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获得第十三届台湾《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引起港台文学界的关注。但却并没有进入到中国大陆批评家的视野,当年只有金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消息,称王小波为“文坛之外的高手”。1992年,《黄金时代》在台湾和香港以单行本和小说集形式出版。《黄金时代》在港台的获奖和出版鼓励了王小波,同年,他辞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系的教职,脱离了体制,成为了一位自由撰稿人。

生前寂寞
但是不同于在港台的“顺利”,这位“自由的”、不归属任何机构,也没有引起主流评论界关注的作者,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过程却非常艰难。当时,《黄金时代》在北京转手了四五家出版社,才最终来到了华夏出版社赵洁平的手中。在这本书初版的后记中,王小波说,“本书得以面世 , 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必须说明 , 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出这本书要困难得多, 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 应当归功于所有帮助出版和发行它的朋友们。”
直到1997年,王小波去世以后,他最重要的作品集《时代三部曲》才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使是在现在大学中文系通用的教材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2007年第2版)和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都对于王小波只字未提。
常常被视为“文坛局外人”、“体制外作家”和“文学浪人”的王小波与文学圈是什么关系?是对立的吗?
细细阅读不同人对王小波的回忆,可以发现,王小波与文坛以及文坛中人的关系也呈现出复杂不同的面貌。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钟洁玲在王小波去世五周年之时表示,“从去世到今日,王小波从来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在2004年《三见王小波》一文中,钟洁玲除了回忆在1997年4月26日的告别式场景外,她也提到王小波是没有单位没有加入作协的。“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与钟洁玲的观点类似,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勇也认为,王小波没有进入过“文学场”。在2012年《“他走在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前列”——赵勇谈王小波》一文中,赵勇说,“新世纪以来,我们也看到许多作家没有刻意去进那个‘文学场’,但他们也获得了某种声名,这是因为文学市场化的进程打破了原来那种僵硬的文学体制。这种情况分析起来其实很复杂,我这里无法展开。我只能简单地说,王小波在世时,还没有赶上像现在这样的好时候。否则他与他的作品或许就是另一番样子了。 ”
但是,王小波真的与文坛无关吗?要知道,当年为他写吊唁文的可有林白、周国平和刘心武的身影。虽然林白说,与王小波的相识只在于王小波对于她《一个人的战争》的声援,实际生活里,他们彼此并没有见过面,因为他并不是在“文坛中走动的人”。周国平也说,与王小波并不相识,直到他去世后,才知道他是一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只有刘心武记录下与王小波的“偶然”的交往过程。
他先来我家。他一出现在我眼前,便让我吃了一惊。我觉得是《水浒》中的某一汉子凸现在了眼前。他不仅个子很高,而且粗黑茁壮。把他比成一百单八将中的哪一将恰宜呢?至今亦难判定。他手里提了个简陋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是一本书。我眼尖,认出那是本《黄金时代》。可是他落座后,并没主动把那书给我。我便主动问:“是给我带的吗?”他这才拿给我。我一翻,没签名,便说:“你要给我签上大名!”他才把书放在膝盖上,潦草地签了名。他似乎来得勉强,兴致不高。但是促膝瞎聊,一来二去的,茶过三巡,居然言谈渐欢。后来我们到楼下一家小饭馆喝啤酒、吃家常菜。他胃口不错,话多起来。给我讲了很多他经历过的事。他的话语中透着睿智幽默,但表情憨憨的,坐如铜钟,很节约手势。
——刘心武《寄往仙界》1997年
作家王童也曾回忆过与王小波的相识在《北京文学》杂志举办的青年作者研讨会上的场景,此后他也向王小波多次约稿。在1997年的《呼叫王小波》一文中,王童说,两个人还曾经一起吃饭喝酒对吹。“小波的话语总是非常幽默地抓住事物的本质,拓开你另一面的思索。有一次,他曾忧心忡仲地告诉我,他得了一种挺让人麻烦的病。但我也只当他得了发烧感冒一类的小恙,并打趣道,你这满身思想的人,过几天就把病给吓跑了,小波也只一笑了之。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患疾而终。”

身后名
与王小波寂寞生前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王小波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有近百家媒体对王小波逝世及新书出版予以报道,“但很大一部分属对外宣传媒体或者港澳台、国外的媒体,而且所发消息基本上都集中在对事件的客观陈述和报道上”。不久之后,“王小波热”兴起,王小波的各种“文集”出版不穷,媒体和知识界也反复强调王小渡的 ‘自由撰稿人 ’、 ‘知识分子 ’、 ‘自由主义思想家 ’、 ‘启蒙者 ’等等身份和形象,因此有研究者甚至认为, 就是因为这些标签,将王小波作为小说家的身份被有意无意的“遮蔽”掉了。
此时,各种对于王小波的讨论和研究也开始出现。1998年5月,学者王毅(国林风书店策划人)主编了《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这本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历史、思想学界的人士,从思想层面来解读了王小波的作品。在序言中,王毅认为王小波具有说真话的智慧和艺术,将他与陈寅恪和顾准并入同一个思想脉络,称他秉承的是与陈、顾同样的“自由意志和精神”的血脉,而又创立出“屈服”与“以生命为地代价”的另外一种可能。《不再沉默》将王小波推向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位置,而这也奠定了之后对于王小波的讨论总是绕不开“自由”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和身份。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王毅说“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成功和可贵,其一在于他不仅像陈、顾等人那样具有说真话的勇气和识别真伪的能力,而且尤其具备了一种说真话的智慧和艺术,以及开始有机会触及了那种使真话传播出去的手段。其二,则在于他的话固然都植根于那饱经忧患的‘罗马’,然而却再也不会把回身走上十字架认定为这说话的最终结局。相反,他憧憬和努力探索着的,是能够走出一条两边都开满牵牛花的路;是有一天像尼采诗中说的那样,去‘做天上的云’。所以在王小波那里,心智再也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在缝隙中超凡绝世的生存技能,而终于重新展现出人对未来的颖悟、对新的和美的文化形态之创造力这一‘智慧’的本真意义……”
与此同时,媒体的关注点持续在王小波身上聚焦。2002年,王小波去世五周年之际,《三联生活周刊》以大篇幅推出了纪念专辑,认为“王小波死后没有别的自由知识分子能填补空白,而精英嘴脸与世俗生活之间的鸿沟在加剧”,然而还有“许许多多因才华、职业所限没能成为自有知识分子的人成为了自由分子”,并且举出几个年轻的“自由分子”的青春成长、求职故事,无一不和王小波有关。
5年后,人大人文学院梁鸿在分析《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推崇王小波的报道时认为,其实这些媒体推崇的是自己的目标读者“城市白领、小资群体和有点公共关怀的智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追捧王小波的是哪些人?除了自由主义人士,对社会绝望,叛逆,激愤的青年人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就是以媒体为依托的、有良好修养和知识追求的城市中年白领,王小波的知识性,趣味性和特立独行恰恰符合了他们的基本精神特征。稍加辨析,就可以感觉出,这种生活实际上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基本的物质保证之后,‘趣味’、‘雅致’和‘欣赏’才有可能,这也是保持一个自由分子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本文的上半部分,通过众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王小波与当代文坛并非是“完全对立”那么简单。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房伟认为,一方面要承认,王小波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另一方面也不能太过强调这种对立,因为这种对立,“会使作家的价值和文学品格, 被简单化、抽象化和二元对立化”。因为王小波的意义,在于其文学力量,而并不是简单地受到中国文坛排斥。
房伟指出,王小波死后,是媒体和知识界在不断地强化这种王小波与文坛的“对立态势”,从这种对立想象中获得的“衍生资本”,让王小波成为一个“局外人”和“受难者”,而这会产生巨大情绪化的影响和力量。“传媒需要这样一个‘受难者’, 不时在适当机会出现, 在文坛与王小波的对立性想象中,再次产生‘衍生资本’, 例如‘王小波门下走狗’、‘北大的王小波 余杰’等等话语。于是, 一个‘文坛受难者’的王小波,其情绪化的影响和力量,甚至超过了“文学家”的王小波形象。而王小波式思想型作家在王小波死后成为‘绝响’,不能不说多少拜媒体所赐。”
20年前,王小波离世,他生前“寂寞”身后“得名”。传媒界、评论界、出版界、知识界等领域的从业者合力造就这样的一个王小波。不知道下一个20年,又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