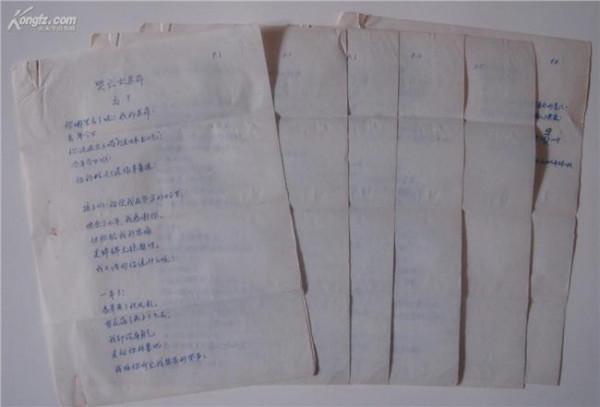张惠雯《十年》 《爱》(张惠雯 选自《收获》2011年第四期)
在新任的牧区医生还未来到以前,一些喜欢打听的居民就得到了一点儿关于他的消息,知道他是医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曾在城里的某医院工作,还是个未婚的年轻人……这类消息总会从某个缺口透露出来,再经由女人们的嘴渲染、流传。
尽管有了各种消息拼贴而成的印象图,但新医生来的时候,人们还是有点儿吃惊,因为他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年轻得多。根据他的经历,他们猜测他至少有二十五六岁,但他的样子看上去更像个学生。和这一带的青年牧民比起来,他个子有些矮小了,脸色也有点儿苍白,不像其他维族青年那样留着唇髭。
即便在他笑的时候,他也显得有点儿严肃,但精明的人能看得出,那并非严肃,而是小心掩饰的拘束。和以往的老医生不一样,他从不大声向病人询问病情,也不会因为他们对针头胆怯而哈哈大笑,如果不出诊,他总是在他的药房里坐着,穿着白大褂。
这个年轻人叫艾山,当他第一天来到牧区诊所时,他发现诊所和兽医院竟然是在同一个院子里。诊所也就是刷了白墙的两间平房,一间是药房,一间里面放着两张床和四个陈旧得快要涣散的输液架子。
在院子的一角,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就是他住的地方。他猜想前任的医生是一个不怎么清洁的人,因为不管是诊所还是住房里面的墙壁都很脏,桌子上、药架上落满了灰尘,他不得不做一次大清理。
他对牧区的工作没有什么幻想,但这样的简陋还是让他失望,尤其当他听到院子里那些被人强按住的牲口发出的嚎叫声时,他感到自己的职业被侮辱了。开始的一些天就在沉闷而又略有些烦躁的情绪中度过了。
但他是这样一个温柔谨慎的年轻人,连他的烦闷不安也是轻柔的、悄无声息的。无人察觉这年轻人陷入了对未来生活的迷惘中,因此也就无人知道他从某个时候起又突然感到这迷惘不再困扰他了。
他深知自己的弱点,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会有远大前程的人,这样,他就不再为职业上的事烦恼了。 渐渐地,他发现牧区的生活也有他喜欢的地方,尤其当他出诊或调查牧民健康情况的时候,他骑在那匹温顺的褐色老马上,望见远处坡地上云块一样缓缓移动的羊群,他会仰起脸深吸那混杂着青草、羊毛和牛奶味的空气,观看头顶那潭水一样蓝而且静的天空。
需要去较远的牧民聚住地时,他常常骑马走上一两个小时。他在途中发现了一些不知去向的小河,偶尔会看见羚羊和鹿。
在路上,他很少遇见别的人,苍茫的草场上和天空下,只有他和他的马,有时候他会突然间忘了他是走在一条通向某处的路上,是要往哪个地方去。有人劝他买一辆摩托车,但他却更喜欢骑马,因为马是活的,它们体恤主人,是路上的伴侣。
牧区的病人并不多,因为牧人们不娇气,不会把小病放在心上,而严重的病,他们就会去县城里看。更多的时候,他就只是坐在那间白色墙壁、蓝色窗框的简易药房里,等待病人或是看书。
有时候,这种日子难免会让人感觉单调、孤独,但这孤独仍是他可以忍受的。 圣纪节过后不久,富裕的牧民阿克木老人给第四个孙子摆周岁酒,邀请了附近的男女老少一起去热闹。让艾山惊讶的是,阿克木老人也邀请了他。
一开始,他有点儿不知所措,因为除了看病、日常事务来往和礼节性的交谈,他在这里还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他反复想到的一个难题是,在人们熙攘往来的房子里,他应该和谁说话,而如果没有人和他作伴,他独自呆在某个角落里,会不会被人可怜、笑话。
可他又有点儿兴奋,因为他也许可以借此机会认识一些附近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不会无缘无故跑到诊所来,而他平时也不会主动接近他们。毕竟,有一些朋友,生活会容易一些。 在宴会举行前两三天的时间里,只要一空闲下来,艾山就会想到这件事。
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总会有细致的想象力,他想到了让他最尴尬丢脸的场面,也想到了一些散发着模糊的温暖光晕的画面,所以,他一会儿犹豫不决,一会儿又兴致高昂。
最后,他跑到他住的那间局促的小屋里,从箱子里翻出来一条白色的袍子,袍子的袖口和领口都镶着针脚精致的、淡绿色的滚边。这是他母亲给他缝制的。由于压在箱子底下太久了,轻柔的布料起了褶皱。艾山把袍子在清水里浸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晾在院子里绑在两棵小树上的那条绳子上。
周岁酒在那一天的晚上举行。下午的时候,艾山仔细洗了头发,把下巴和脸颊刮得很干净,然后,穿上了那条袍子。他在洗脸盆上面的那一块残缺一角的镜面里打量自己,他感觉自己打扮得还算整洁,他尤其喜欢母亲给他缝制的这件礼服长袍,他喜欢那淡绿色而不是红色、金色或亮紫色的镶边。
但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长相平平:他的鼻梁有点儿扁平了,毫无特点的嘴巴不大不小,也许他脸上唯一好看的地方是他的长睫毛,可这算什么呢?他又不是个姑娘,并不需要这样的长睫毛。
五点多的时候,艾山往阿克木老人的家走去,他没有骑马,因为阿克木老人的毡包离诊所这里走路只需要三十多分钟。他走在余晖渲染下的草坡上,穿着白袍。
路上,他看见一些归牧的牛群,还有几个骑马赶来的临近地方的牧民,其中有一两个裹着色彩鲜艳的头巾的妇女。他听见赶路的人含糊的、由远而近的交谈声,以及归牧的人单调的吆喝声,但他什么也没有听清楚。
他想着他自己的事,对自己不够满意,还有些说不清楚的不安,但他仍然兴奋、快乐。当他看到站在阿克汉家那个大毡包外面的一群女孩儿时,他才恍然大悟,他所一直担心、害怕的正是她们。而她们正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做着手势,有两三个女孩突然神秘兮兮地朝他看过来,似乎她们正在谈论着他。
他硬着头皮经过她们身边,而她们的窃笑声传进他的耳朵里,这笑也像是冲着他来的。于是,连他的耳朵也红了。他钻到毡包里去了,看到里面有更多的年轻女人,但也有很多男人。
阿克木老人的小儿子嗓门很大地迎接他,这个腼腆的外地年轻人的到来似乎让他脸上有光,他拍着艾山的肩膀,好像他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后来,一些熟悉的人走过来和他说话,还有几个找他看过病的妇女。
他觉得舒服了一点儿,不那么热了,他的心跳逐渐平稳,开始悄悄打量周围的人。慢慢地,有不认识的年轻女人上来和他说话,她们问他有关胳膊上莫名其妙起的小水疱,被马咬后留下的伤疤还有突然出现的眩晕,有个女孩儿说她的耳朵里经常有轰鸣声,还有个女人说她夜里老是做吓人的梦,问他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治。
不管那是否是可笑的问题,他总是细心地替她们分析,尽量找到答案,但每一次,他都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过后总觉得那样的回答太仓促含糊了。
客人们走来走去,而他似乎就一直站在他进来之后选定的一个地方,一个灯光稍暗、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地方。 吃饭的时候,艾山被邀请坐在重要人物的一桌,那一桌上有主人阿克木老人、他的长子、二儿子还有两个牧区的干部、三四个他不认识的、年龄较长的牧民。
他觉得别扭、难受,却找不到借口推辞。有人开始悄悄议论这个坐在尊长者之间的年轻人了,他显得多么年轻、害羞呀!一个可爱的、涉世未深的人。
当别人和他说话时,艾山总会专注地听着,很有礼貌地点头,而大部分时间,他只是低头盯着眼前的杯子、盘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隐约地感到有一道目光不断朝他看过来,但每当他循着感觉的方向看过去,他却只看到一些因为欢笑而颤动、闪烁的女人的身影。
他不好意思朝那个方向一直寻找,但他觉得那双眼睛就隐藏在那些影子中间,它悄无声息地注视自己,于是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落在这目光构成的透明的网中,无一逃脱。
他又开始不安了,他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一点点地侧过身子,可他觉得他并没有摆脱那道目光,它就像一个轻盈灵巧的飞虫,在他发梢、衣领和背后飞动。 那些人劝他喝酒,他们让他喝了太多的酒,因为他不会拒绝,因为拒绝要说很多客套、聪明的话,看起来他还不会。
所以,他的脸涨红了,他用手扶住自己那低垂的额头。突然,他抬起头,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飞快地朝一个地方看过去。只此一下。然后,身边的人又和他说起话来了,他于是带着儿子般亲昵而温顺的神情看着那个长者,眼睛里闪动惊奇的亮光。
在旁人看来,这年轻人已经有点儿醉意了。可他自己却正为一个发现而欢喜,他似乎找到那双眼睛了,他刚才捉住一双迅速闪开的、有些惊慌的眼睛。她坐在一群女客人中间,娇小,毫不突出,但她那双眼睛,她垂在脸庞两侧的黑头发……一瞬间,他的心里被一种欢喜、甘甜、涌动着的东西充满了。
但他如何能确定那就是那双眼睛呢?也许它早就躲开了他,而她只是不经意地碰上了他的目光。
他假装专注地听旁边的人对他说话,而他一句也没有听到心里。在心里,他有些迟疑、迷惑,还有种说不出的快乐。 酒席松散了,人们又开始四处走动,有的人到毡包外面去了。这中间,一些女人们从她们坐的地方起身,围到满周岁的男孩儿和他母亲坐的桌子那儿,她们逗那孩子,孩子却不解地哭起来。
有些住在较远地方的人开始告辞了,阿克木老人站在靠近门的地方,和要离开的客人告别。但不少人兴致还很高,男人们还在喝酒,准备闹腾一阵。
这时,他突然发觉她不见了。迷迷糊糊中,他也站起身,走到外面去了。他看见天空中的半轮月亮和一些稀疏的星星,还有一些人骑着马离开的影子。也有人骑着摩托车走了,那起初尖锐的震动声慢慢变得辽远、寂寞。
一些女孩儿在不远处站着,同在一块儿说笑。在这些影子里,他都没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他向堆着干草垛的空地那边走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想往更远的地方走。在他那双朦胧的眼睛里,干草垛就像贴在夜幕上的剪影,像是在草原的另一边。
他有点儿累了,在一个草垛下面坐下来,夜里的凉气渗透了他的袍子,可这凉意多么清爽。他嗅闻着干草松软的香气,不知怎么想起了炉膛里刚拿出来的热香的馕,他仿佛又看到一双柔软的女人的手,看到在晨雾里显得乌黑湿润的女人的头发,仿佛听到了纱一般轻柔的女人的说话声……但最后这一点似乎并非幻想,因为他真的听到了女孩儿的说话声,这说话声越来越近,他发现已经到了干草堆的后面。
“是真的吗?可是……可是,你都对他说了什么?”一个女孩儿压低着声音、激动地说。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怎么能说呢?”另一个女孩儿声音微微颤抖地说。 “可他怎么知道的?他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他好像发现了,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
” 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个女孩儿喃喃地说:“感觉,多奇怪的感觉。” “你不会对别人说吧?”声音颤抖的女孩儿怯怯地问。 “啊?你怎么想的,我当然不会!”爱激动的女孩儿几乎叫出来。 “好了,好了,你不会说的,我知道。
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她说。 坐在那儿的艾山一动不动,几乎不敢呼吸,幸好他被掩藏在草垛浓黑的阴影里面。于是,那声音就从他身边经过,两个女孩儿边走边说,趁着月光往毡房那儿去了。他知道其中没有她,但他仍然觉得她们每一个的影子都很美。
他无意中听到了她们的谈话,她们的秘密,可他不知道她们是谁,她们爱上了谁。这一切,在他想来也很美。 他又回到毡房里,可她并没有在里面,她那桌上的女人们都散了,桌子空下来。
他想她也许已经走了,这使周围一切热闹、耀眼的东西突然间显得黯淡无光了,他发现他之所以走出去、又回到这房子里来,这一切只有和她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但他不好意思马上走,尽管他心里焦急着。仿佛有一种不近情理的、模糊的希望在催促着他:如果他早点走出去,也许还有机会在路上遇见她。
他仍然站在那儿耗了几分钟,和阿克木的小儿子说着话,他终于记住了他的名字——帕尔哈特。随后,他终于找了个机会向阿克木老人告辞了。
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去,看到有人忙着套马车,有人还站在靠近路口的地方说着话。他隐约怀着那个希望,但又极力否认它。一方面,他被那种无法解释的愉快情绪充满着,另一方面,他又想让自己从这让人晕头转向的愉快里挣脱出来,冷淡地不去相信关于那目光和那个女孩儿的事儿,把它当成错觉、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
这时,他突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头看见路旁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她正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没有骑马。 “我没有骑马来,我住的地方很近。
”他有点儿吃惊地看着她说。只有一点月光照在她的脸上,而那张脸的轮廓又被围巾遮住了。可他猛然想起来,这个女人在毡包里和他说过话,而且,她和那女孩儿坐同一张桌子。 “街上兽医站那儿?我知道那地方。
”女人说。 艾山笑了,没有说什么。 “还有一段路呢,”女人又说,“你搭我们的马车吧,我丈夫一会儿就过来。” 艾山本想说“不用了”,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如果他坐上这女人的马车,也许他可以听她谈到她…… 他谢了她,站在路口那儿和她一起等着。
然后,他看见一个壮实的、敞着怀的中年人慢悠悠地赶着一辆没有篷顶的马车过来了,在他后面,侧身坐着一个女孩子,当马车快到他们跟前时,她朝他们招了招手。
就像做梦一样,艾山看到了酒席上那个娇小的女孩儿。 “那是我女儿。”那妇女说。 “上车吧,年轻人!”中年男人显然已经醉了,满面笑容地朝他大声喊道。妇女绕去另一边上了马车。他看见那女孩儿往中间挪了过去,于是,他上了车,坐在她刚才坐的地方。
马慢慢跑起来了。车上的地方并不宽绰,在车子微微颠簸的时候,尽管他双手很用力地抓住车缘,他仍会偶尔碰到她。他起初有点儿紧张,他们三个人挤在一起,而他离女孩儿的头发、手臂、衣服都那么近。
但他发觉她并不在意,她那么自然、快乐地坐在那儿,有时朝他靠近,有时又缓缓离开他。她那自然的态度感染了他,他不再担心了,反而希望途中能够多一些颠簸。他的双手也不再紧抓着车缘了,在身体每一次自然而轻微的碰触中,在一个女孩儿的气息中,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温暖。
而每当颠簸过去,他们之间重又有了空隙,他就感到失落。没有人说话,只有赶车的男人不时和马吆喝着说上一两句。突然,女孩儿用手肘轻轻碰了碰他,说:“他和你说话呢。
” 艾山从恍惚的意识里醒过来,听到赶车的汉子在讲他的牛得的奇怪病。但他也不确定男人是否只是和自己一个人讲。他有点儿费解地看看那女孩儿,那女孩儿也看着他笑了。 艾山对那男人说:“带它到兽医那儿看看吧,牲口有病要尽快治,怕它传染。
” 男人说:“是啊,是啊,要去看看,牲口有病一定要去给它看,牛马不会说话,也不知道它们哪里难受,比人还可怜。我自己呢,就从来不看病,我这辈子还没有进过医院,真主保佑。
” 女孩儿却凑近艾山耳边小声说:“去年肉孜节的时候他喝醉了,摔伤了腿,我们带他去过城里的医院。”她的语气和动作里都透出一种熟悉的亲呢。 接下来,又没有人说话了。艾山望着前面,月光下的路像一条银灰色的带子,远处的草原是一片巨大的暗影,隐匿在苍茫之中。
体型匀称的马儿踩着碎步紧跑着,一切白日赋予的颜色都模糊、消失了,草原的气味在夜里却更加浓烈而单纯了。带着一股有点儿昏沉的醉意,艾山看到的一切仿佛都带着虚幻般的美好。
车子慢下来了,晃晃悠悠地停在了一个地方,艾山这才发觉已经到了诊所院子的门口。他慌忙跳下车,和这家人告别了。 他走回小屋里,对刚刚的经历还有点儿将信将疑。这仿佛是个美梦,这么说,就像他渴望而又不敢想象的,他刚好和他要寻找的那个姑娘坐在同一辆马车上,而且,她还对他说话,他们像小孩儿一样无拘无束地靠在一起。
有一会儿,他呆呆地站在桌子前面,回想着在昏暗的夜光中的她的脸庞,衣裳的暖意,还有那条往远处延伸的路……那么美好!
这都不像是真的,却是真的。他不知道在桌子前面呆立了多久,然后他醒转过来,于是走到门后的那张椅子那儿坐下来。在那儿,他又发呆了,坠入到没有止境的回忆和幻想中去。
他想到他骑着马去了她家,她把他迎到毡包里,他们在那里面坐着,只有他们两个,她穿着冬天的厚厚的袍子,眼睛在炉火跳动的影子里显得更黑了,她的小毡鞋几乎碰到他的皮靴子;他们又仿佛坐在同一辆马车上,但那是另一辆马车,另一个旅程;他还看到她正站在一个洁白崭新的毡包前面,晾着衣服,衣服被风吹得鼓鼓的,像是要飞走了一样。
他想到恋爱、结婚、未来的生活,这些事说起来多么平淡无奇,这就是他的父母、他的兄弟都经历过的,可它们又是多么奇特。
这一切仿佛突然之间离他很近了,而以往他却觉得很遥远,遥远得他都不愿去想象。 他终于站起来,走到外面去了。这间小屋太局促了,似乎盛不下他那不着边际的幻想和激动的情绪。
他去井边打了一盆水洗了洗脸。他回到房间里,脱掉身上那件白色袍子,换上了一件平常穿的厚布袍,在床上浑浑噩噩地躺了一会儿。然后,他发现自己又站在院子的大门口了,就在他刚才下车的地方。眼前是一条白净、单薄的小路,两边孤零零的几间平房店铺都藏匿在沉沉的阴影之中。
他猜想那家人已经到家了,马儿在棚子里拴好了,嚼着草,毡包里各处的灯都熄灭了,女孩儿已经躺下了,可能正沉沉地睡着,也可能仍然睁着她那双可爱的眼睛。如果他知道她所在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是他能够走到的地方,他现在就会往那儿走去,哪怕走上一整夜,走到明天早晨。
这时,艾山才想起来,他对于这家人一无所知,他没有问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他不禁感到懊恼,但这也没有冲淡他那有点儿眩晕的幸福感,他已经像个恋爱中的年轻人了,而对于这种人来说,仿佛一切的困难都可以抛诸脑后。
第二天凌晨,当他终于在床上躺下来的时候,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想找一个适合她的名字:阿拉木汗、帕拉黛,还是古丽夏提?似乎更像是巴哈尔古丽……于是,他最后决定叫她巴哈尔古丽。
他不知道怎样过了那两天,一切其他的事情,一切眼前所见,仿佛都从他的眼睛和脑海里飘过去,留不下一点儿痕迹。第三天,艾山晚饭后去找阿克木的小儿子帕尔哈特,在他看来,这年轻人热情能干,而且似乎很愿意和他做朋友。
帕尔哈特很高兴,他又带艾山去找另一个年轻人。要把他最好的朋友阿里木江介绍给他。他们在阿里木江的家里坐了一会儿,喝了两杯酒。
帕尔哈特想到外面逛逛,这也很合艾山的意,可他们一直拿不定主意。后来,阿里木江说,这么大的牧区,去哪儿不能走走呢。于是,三个年轻人从围栏里各选了一匹马。阿里木江还带上了酒和热瓦普,帕尔哈特对艾山说,阿里木江是这一带最会唱歌的人。
他们往牧场的北面走。天上堆积着小朵的、瓦片般的云,但月光仍然很清亮。草场上交织着银子般的月光和一些奇异的阴影。似乎还笼罩着一层淡得看不到的雾气。他们时缓时急地骑着马,并没有一个明确要去的地方。
阿里木江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喜欢突然停下来,朝着远方喊两声。每当这个时候,帕尔哈特就会对艾山说:阿里木江亮嗓子了,他要唱歌了!可阿里木江并没有唱。他们不知道骑了多久,中间经过一些坡度柔和的高地和山坡,还经过了两三个牧人住的毡包。
后来,马儿来到了一条很浅的小溪边。他们在那儿下了马,让马自己去喝水。 三个人就在溪边找个地方坐下来,把阿里木江带来的酒传着喝。过了一会儿,阿里木江终于弹着热瓦普唱起歌来。
慢慢地,帕尔哈特跟唱起来,艾山则被阿里木江的声音和那些歌深深打动了。他痴迷般地听着,不唱也不说话。在他的脑海里,他刚刚走过的路和那天夜里他在颠簸的马车上看见的路重叠起来,这条路又仿佛是他为了要去寻找她而走的路。
他想,他不正是因为她才和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走这么长的路、然后坐在这里吗?在路上,他一直想对他们说起她,说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这两天,他生活在怎样幸福却又焦躁不安的情绪中?一个人孤独地藏着这热切的秘密,这实在难以忍受。
但现在,他那想要诉说的强烈欲望却平静下来了。阿里木江的歌声似乎把他带到远离语言的世界里了,在那里,他那可怕的孤独被融化了,他沉浸在倾听和想象中。
而在想象里,他成了一个破衣烂衫的骑手,走着无休无止的路,只为找到那个躲藏起来的姑娘。 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他母亲,想象着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她经历过的那些爱慕、追求、思念……他把这美好的事联想到他认识的每个人身上,正在唱歌的阿里木江,像小孩儿一样轻轻拍着手跟唱的帕尔哈特……他甚至联想到过去和未来,各个年代的人,各个地方的人,死去的、活着的、还未曾来到世间的人,无论窘困还是安逸,无论生活卑微或是出身高贵,他们都有那精细入微的能力感受爱,他们都会幻想爱、经历爱,这种美好的东西从不曾从世间消失过,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于是,他觉得那个美梦般的夜晚、还有这月光下的草原、这露珠的湿润、乐器的动人、马儿的忠诚、溪水发出的亮光、人脸上那突然闪过的幸福忧伤表情都不是毫无理由地存在着,这一切,也许就是因为爱,因为它作用于世间的每个角落、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年轻人喝完了酒,收起热瓦普,要往回走了。他们不知道时间,但从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看,已经是后半夜了。
潮润的夜气就像沁凉的井水流遍了草原,风完全沉寂了,连天边那几颗星星也仿佛昏睡了。路上,他们比来的时候沉默了一些,各自想着心事。而艾山想的是,尽管他毫无线索,甚至也不知道如何向别人问起,但他总会找到他的巴哈尔古丽——那娇小的她。
她那双灵活的眼睛,她的柔软飘动的衣服,她曾碰过他的手臂,她的前头翘着新月般尖角的小毡靴,这一切就在某个地方等着他。带着这有点儿盲目的乐观信念,他在马背上低声唱起了歌。




















![>张培基散文翻译]张培基散文翻译特点](https://pic.bilezu.com/upload/5/b9/5b9c8322b33c5156f0fa76ad25330b70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