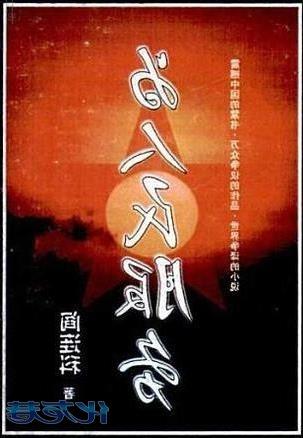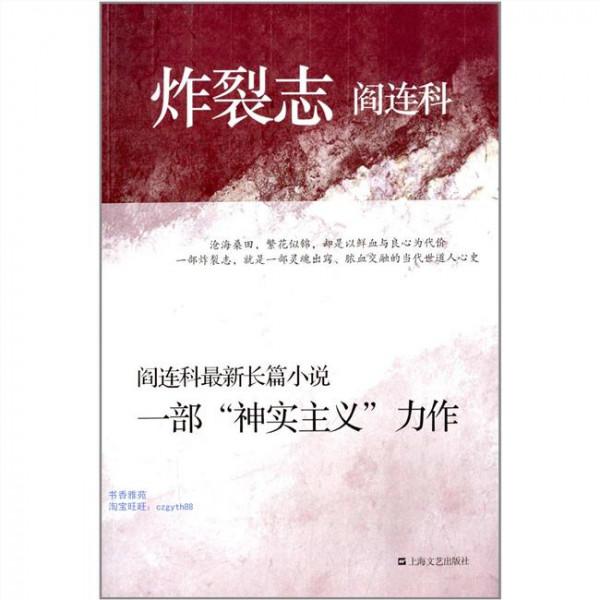张惠雯所有作品 阎连科:《我与父辈》是我所有作品中一颗情感的钻石
6月24日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著名作家阎连科来到位于北京通州台湖的北京国际图书城,15点半到16点半,用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接受了北发图书网专访,谈了他的新书《我与父辈》以及对人生的体验。 北发读书:大家好,欢迎做客北发图书网组织的新一期作家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作家阎连科老师,他近期出版的这本新书《我与父辈》,在网站,书店的销售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阎老师来和我们谈谈这本书。
谈谈他关于这本书创作的初衷,主要是想通过这次互动来了解作者的心理世界。
北发读书:首先我想问一下阎老师,您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样的? 阎连科:《我与父辈》定位的话,叫长篇散文比较好一点。之前我一直进行小说德创作,而且读者群没有那么大,读者可能式在高校的学生多一点,研究人员多一点。
当然我的小说也有很大的争论,说好的好到天上,说坏的坏到地下,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也是一个争论比较大的作家。我的写作也非常的辛苦,辛苦不在于写的辛苦,而在于争论的声音让你很辛苦,我想在写作当中有些调整,写一些更日常的东西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写更加日常的,家常的,或者说写的就是大家共有的生活,而不是你的想象。 北发读书:您的这部作品从始至终贯穿的都是真挚的爱和真诚的力量,读者能从您的书中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启示呢? 阎连科:这是我之前没想过的,我以前的写作从来没有想过告诉读者什么,就是写自己内心的,这次也不是为大量的读者,是为我家里的弟弟妹妹。
在前年的10月国庆节,我四叔不在的时候我回老家去,我们河南的乡村有守陵的那种习惯,要三天三夜守在那里。忽然一个晚上,我的一个妹妹在两点钟左右(大家都没睡觉)告诉我说,“哥哥,听说你写了很多小说,在外面是有点名气的,但是你给我们寄的书没有一本能看的明白的,你为什么不写写父亲,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写写大伯,写写你自己,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特别爱看。
” 正是她这样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想我的写作需要有一个缓冲,一种回归,说缓冲就是说需要一个调整,回归就是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去。
如果说要告诉读者什么,我想我是没有刻意去想的,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想写一本之前看不懂我小说的人这次一定能看懂,之前说不好看的这次会说写的好看的书。
不管怎么样我想不能让读者说是好看但没有意思,我对自己这次写作的想法就是让读者说好看也有意思。 北发读书:一直有人这么评价您,说您是一位很坦诚的作家,所以您得到了一定的尊重,我想问一下,您在您这本《我与父辈》中,这个坦诚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连科:首先在写作上,这次没有在想什么主意,什么技巧。
我们之前的写作也许要构思十年、八年、五年,最后写作可能只要半年时间。这种构思不简单的是为了塑造人物、为了故事,更多的是在想语言、结构、叙述,想人物的那种叙述方式和出场方式。
但这次写作恰恰是首先要放弃一切的主意,放弃一切的技巧,任何叙述都不要去讲究,只要一点,以最真诚的态度,最朴实的写作方式,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这部散文之所以能够打动许多读者,可能也恰恰是这一点。 北发读书:我也是您这本书的读者,我大概用了半个小时的工作闲暇时间差不多就读了一半了,觉得很感人。我也给我的同事介绍,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很坦白、很真诚。
您在作品中一再的提到乡土气息,很多人说更感人的是您对父亲的愧对,对大伯和四叔的感激,因为乡土上的挣扎和无奈,也因为土地是纯粹的最残忍的所在。 阎连科:之前人们说,阎连科你的小说已经来自于乡村了,已经是乡村田野的一棵大树,但其实那些乡村的人是不看你的小说的。
比如我们说鲁迅是伟大的,鲁迅也是写乡村的。鲁迅批判国民性已经一百年,也被我们认为之所以他伟大是因为他深刻;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对国民性的那种批判。
我经常想,国民性虽然批判了一百年但是他仍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鲁迅小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还有一点,鲁迅要批判的是国民性,可那些有这种国民性的人是不看他小说的,而看他小说的人是有这种国民性相对少的人。
这不是说鲁迅小说的意义大和小的问题,但这种矛盾不得不承认,鲁迅是多么的伟大,但在地铁里我们找不到一个看鲁迅小说的人;沈从文多么伟大,我们在大街上也找不到一个看他小说的人。
我在想自己的写作也是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但我知道我家乡的人要么不看,看了也会说非常的不好,我很矛盾。我们知道劳伦斯在英国是非常伟大的作家,他的家乡有一个劳伦斯的文学节,每年会去很多人,我也曾经去参加过,但劳伦斯在他的家乡是人提人骂的一个人,他们并不以他为荣。
这种矛盾对于我来说,我不希望这样产生,我希望我的那些小说他们不看,至少有他们爱看的东西,我希望这次写作真正能联系起来。
以前你说你的写作是一棵大树的话,你会发现他所有的营养来自那块土地,所有的故事人物都来自那块土地,但是那块土地上的人和你不发生联系,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说到的乡村气息,说到土地情节这都是我们一相情愿的事情,这样一次写作我想或多或少能够弥补这一点。
我回老家的时候带回去几本《我与父辈》这本书,给我那些弟弟妹妹看,至少有一点,他们爱看这本书了,我和他们发生联系,他们也和我发生联系了。
北发读书:最终就产生了这种共鸣和互动,因为之前你是活在自己的写作里面。 阎连科:这样的一部长篇纪事散文恰恰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今天在我往这里来的时候,11点左右,我老家来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个湖北的读者,他出差路过郑州,看了《我与父辈》这部小说,他有一种冲动,从郑州到了洛阳然后找到了我的家乡。
他没有我的电话,是从网上找到的,阎连科是河南嵩县人,就这么直接去的。我母亲已经75岁了,一个人在家,他真的是一个人找到家里在我写过的院子里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在家里给我打的电话,我就说让他在家里吃顿饭,有什么咱们回来聊。
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八十年代经常出现,八十年代我的小说也有一部分读者,他们也会从各地专门跑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
今天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大批的读者是需要这样一种阅读的。 北发读书:更贴近于他们的生活,更贴近于大众。您这部小说里写了您与父辈的挣扎,历史的演进与父辈们的生命挣扎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阎连科:我想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几十年前了,对我们的孩子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清晰的记忆在头脑中的。
在那种革命年代,作为父亲母亲,他们的愿望是非常质朴的,希望能够好好的活着,希望孩子能够成家立业,但是就是这样的目标也是非常的艰难。
全社会都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你想盖起房子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所以他们所有的挣扎,表面看是无知的挣扎,但从深层里看,实际上是他们对生命那种无奈的挣扎,是另外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挣扎。
所以在写到大伯的时候,大伯对死亡的认识很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写到父亲他对盖房子,对前程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读者也许不理解,那个年代我们的父辈真的就这样生活吗?是真的,就是这么生活。
比如说前段时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我们说的大上海,大上海他和乡村生活没什么联系,他们的语文老师是非常爱写作的。他给他的学生推荐了这本书,他自己买了五六本书给班里的学生传看,后来有一半的学生自发的到街上买书。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第一个发言说“我虽然没有离开过上海,但我知道我的爷爷奶奶是从乡村来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我的父亲母亲和别人不一样,总是对我这样对我那样,我学习这么好为什么他们对我这样不好,还老是闹矛盾,看了这本书以后我突然觉得我对他们也没有那么好,通过这本书我知道如何处理家庭的关系了”。
郑州的一个军营里有个科长是东北人,姓单,他一个人买了十来本书,他和我说他看了三遍,仍然会流泪,不一定说是我写的好,是他家里也有类似的经历、类似的情感。
他家里也有很多兄弟姐妹,他说你别问我家里有多复杂,我把这本书寄给他们看一看,让我们的家庭矛盾小一点。 北发读书:您在书中对日子和生活的描写感触颇深,尊严在日子前面是那么柔弱与渺小,命运在死亡面前是那么无畏与无奈,您的更深层次的体会在哪? 阎连科:从今天看日子和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乡村中我们通常说日子,对生活两个字其实他是有丰富的意义在其中的,我们城里人经常说生活,说生活是因为我们在城里能感受到图书馆,感受到公园,感受到电影院,感受到种种触手可及的生活。
乡村说日子的时候是单调的,乏味的,日复一日的,几乎没有改变的。 我想现在乡村的生活和日子和一百年前乡村的日子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我们说城市的生活就不是这样的,不要说一百年,就是和三十年前都是大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说的80后,90后,那个生活状态和他的父亲母亲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有本质差别的。
北发读书:我认为作家创作作品的过程实际也是他自己感悟的过程,那么在本书中您对生命和死亡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境界吧? 阎连科:我个人是比较脆弱的,不管你对死亡恐惧也好不恐惧也好,都是向你一天天走来的,不管你能不能迎面向死亡走去,但死亡是每一天都在向你走来的,这是无可逃避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死亡我也经常想一个问题,有三种人的认识不太一样,我想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大教授他们甚至会觉得死亡是一种超越,一种升华,我们中国没有宗教,可能只有那些大知识分子能够感受;第二种就是我大伯这样的人,他们对死亡的认识甚至超过了很多大哲学家,不是说迷信不迷信,而是说他们对死亡的坦然,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具备的,而乡村很多人对死亡确实是非常坦然的。
这是他们面对生死关的一个态度; 我想对死亡最痛苦的应该是我们这些人,包括在都市生活的人,好象对死亡了解的非常深刻,也许了解的非常简单,好像了解的非常简单,但我们又对死亡比别人知道的多,所以对我们来说死亡是最大的痛苦。
我们每人都需要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去体会死亡,当你很多亲人离开你的时候,当你看到你的朋友突然离开你的时候,你必然对死亡有了认识,会拿出几十年考虑这个问题。
死亡和对死亡的思考是陪伴每个人一生的事情。 北发读书:是不是通过这本书您对死亡的认识变得更坚强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阎连科:我想能够多少坦然一点。至少明白一点:你恐惧也好、逃避也好,这件事情无法逃避。
已经知道无法逃避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如何的面对他。当然我不会像书里写的我大伯那样面对死亡是那样坦然,当然也那样的世俗也那样的乡村化。今天已经离开乡村二三十年了,而且可能还要在北京生活后半生,但是如何面对死亡应该是以后考虑的,今天考虑的还很不成熟。
真正到考虑成熟时可能真的要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或几天时间才能考虑成熟。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而是怎样面对的问题。 北发读书:您敢于面对、敢于承认、敢于揭露,这是您如泣如诉的自我反省,也是毫无保留的坦诚您的内心冷漠自私阴暗的一面。
您在书中关于父亲的那个章节应该都有体现,毫无保留坦诚的将自己曾经的劣行与过错表现给广大读者,您揭露这个过程想给我们读者怎样的启示或理念和意念呢? 阎连科:其中写到我父亲这个章节当然会非常坦诚,写自己的内心对父亲的内疚这些东西。
我想其实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给读者什么,只是想告诉父亲我有哪些对不起你。尽管父亲不在你会感觉到他仍然会听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告诉她我哪里做得不错但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其实面对这样已不在身边的父亲,我想这是什么都可以坦露的,当然读者今天看到也会为之动容。
我想每一个读者每一个孩子面对父亲的时候,每一个儿女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我那样的经历和情感。
不管你今天多大,当你回忆起你父亲母亲,你的爷爷奶奶已经离开你不在的时候,你一定会心怀内疚,心怀内疚不是你做的好与不好而是说你能够做好却没有做好。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孩子,那你没必要去内疚;你是一个好孩子也没必要内疚。最主要一点是对于父亲母亲,我们都可以做的非常好,但是我们没有努力去做到,怀着犹豫躲避了这些东西,这将是我们一生要面对内疚和弥补的事情。
北发读书:就像您说的,就像生活中的水一样可有可无那种感觉。 阎连科:对。我们父亲母亲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爱是可有可无的,像一杯水一样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但是当我们父亲母亲不在的时候这种内疚是再也无法抹去的。
我想这样一本书,你写自己的坦言,我们面对家人朋友、面对所有亲人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爱别人、你对世界充满爱,我想这句话特别大。 我经常讲你首先要从你的家庭做起,你是孩子你首先要爱你的父母,你是父亲你首先爱自己的孩子,如果对父亲母亲、对姐姐妹妹你的爱都没有那样的话,你对朋友的爱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您对你领导的爱更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伦理传统的国家,我们的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延续的核心,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爱最简单的是,你先爱你的父母亲、爱你的孩子,从这里的爱再说你对别人的爱,如果这件事情没做好,你说你爱别人可能都是有点不可信的。
北发读书:您用平实的语言说了一个我们已经淡忘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文学作品不是追求富足的人们用来消磨时间的一种器物,他更是以一种摆脱低级肉麻和无病呻吟的一种现象而成为记录社会洗涤人们的重要工具。
关于您的这本《我与父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已经包含了这种的意念在里面? 阎连科:我想《我与父辈》在写作之前你要让读者知道什么、告诉读者什么、让读者知道什么理念,刚才讲得是没有那么清晰,就是那么质朴的写出来,传递给我的弟弟妹妹也传递给读者。
但是有一点,在写作《我与父辈》之前我写了那么多小说,比如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你的写作匆匆屡屡,今天有很多批评家把你捧到天上,当然也有批评家把你骂到地上。 但是我在写《我与父辈》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之前我的作品在送给朋友的时候我就经常交代不要给小孩子看,也不一定适合老人们看,但这次恰恰相反,我就是想写一本能让我送给孩子们的一本书。
而且我自己也买了200本书,其中有100本是送给孩子们的。
我很自豪的讲我写了一本书也许没有那么伟大,但是做父亲母亲的可以送给孩子,可送给任何80后90后甚至2000后的孩子们。能够写一本送给孩子的书我想没那么容易,我以后可能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
北发读书:本书的写作是否已经触及到您写作的底线?这个底线我讲的是自我的反省和一个认知。 阎连科:我想他一定触及到你的认知你的生活的最真诚的一面,而且我想从这一部书开始你会思考很多问题,思考你的写作。
以后你还要像《日光流年》《受活》这样写下去吗?还是像《我与父辈》这样写下去,这会改变我的创作方向,但是你对你的小说意图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有一点,你会改变就是说你会开始相信一种爱的力量。忽然发现我们那样一个家族、村庄,我们那样一个世界之所以能传承下去,不是因为别的,确实是因为爱的力量。
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其实是没有宗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有如此发达的文化、如此繁衍不息,这不是简单我们说得别的问题,恰恰是我们那种爱是我们活的力量。
对于爱的从新认识,爱不是一种美,爱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种力量,这样一种认识会改变我对生活的看法。在以后的写作中我想会在这一点上发生变化。 北发读书:您与您的父辈和您与您的子辈这个生命链是如何延续下去的,就是您是否能告诉我们读者或是广大热爱您作品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 阎连科:这个应该是教育家来讲的,我确实不太懂。
但是有一点,我和我孩子的关系,说实在话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成才,而且我的父亲母亲从来也没想到让孩子成龙成凤,他就想他能够成家立业,能够健康的活着,能够有很好的一碗饭吃,有很好的一件衣服穿,这是我父亲对他孩子的希望。
那么这种理念也传递在我的身上,我对我的孩子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说,你能够健康的成长,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因为我的孩子原来在清华附中读书他学习也不错,我们经常想他能考到清华、北大、复旦呀。我对孩子的家教、寒假暑假的培训班基本都放弃了。
我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能非常健康快乐的成长,这是我对我孩子唯一的要求。但之后他考的学校也没有那么理想,但我想他的生活质量是不比同龄人差的。如果说我要给那些做家长的说一句什么的话,我想说对于父亲母亲来讲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北发读书:您这本书里更多的是对父辈的感恩,有一段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您与姐姐上学与不上学的描写是非常感人的,就是这段你当时写得时候初衷是什么? 阎连科:也没什么初衷,就是把自己的经历百分百的写下来。
因为我的读书就像书中写的那样,我6岁读书,姐姐8岁读书,考高中时大家是同时考得而且她比我考的好,可是我们家里种种原因只能有一个孩子读书。我当时想的是通过读书摆脱像父亲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当时姐姐就说她不去读书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今天应该说回忆起来的话是使我的人生发生改变的一点,但是姐姐不去读书是重要的一点。比如说你的写作你的风格是因为你和姐姐不一样,你读了高中,如果你和姐姐一样从十几岁就开始下地劳动的话,可能今天不是这个样子。
我就经常想我的一些成就就是姐姐从那时一点一点给我的,我想我应该还给我姐姐一点什么吧!至少是在情感上还给她。 北发读书:她看您这本书了吗? 阎连科:我有两个姐姐,她们都看这本书了,看这本书的时候和大家的情感不一样。
我经常跟朋友说你看看这本书吧,这写的是我们的家务事,他们看一次哭一次。 北发读书:像您在这本书后面您自己亲自留言说“在我所有作品中这是一颗钻石”,您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 阎连科:《我与父辈》是我所有作品中一颗情感的钻石吧!
因为我写起来的时候,我有两次写作特别投入。一次写作就是我写《丁庄梦》的时候,写我们河南艾滋病的时候特别投入,经常叫我欲哭无泪、经常无奈,你把很多事情无法跟别人讲的痛苦,这样一次写在作就是你是写的你那一块土地,面对的是乡亲们。
而这次您同样写的那块土地,是面对你自己最亲的人,说实在的,的确是一边写一边去卫生间洗把脸平静一下继续写。
直到20天前,我在修改《我与父辈》的一些文字的时候仍然会不断的掉泪,我想他确实是我个人情感的钻石,在我以后的创作中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写出这样的作品。就是说一旦一本书成为钻石的时候,钻石不会那么多的,你在富有,可能钻石也只有那么一两颗,对我来说他非常珍贵就在这一点。
北发读书:今天的访谈大概的问题也就这么多了,然后就是问一下您希望我们广大的读者应该这本书怀着怎样的心情去读呢?给我们总结一下。
阎连科:对网上的读者我想说的是,阎连科别的书你可以不看,如果您年龄特别小,是80后、90后或者更小的话,我确实不建议你看我别的书,但是你如果年龄小一点或者说你对家庭非常有情感或家庭非常缺少情感,我想你还是看看《我与父辈》。
我非常自豪的说你们可以骂我别的小说,我想《我与父辈》你看完是不会骂的。 我写了一本我值得送给别人尤其是值得送给孩子的书,这本书我希望我的晚辈看,也希望我的同代人看。看完之后您会觉得,如果你和你的孩子有距离,这个距离是可以缩小的;如果没有距离,这个爱是可以加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