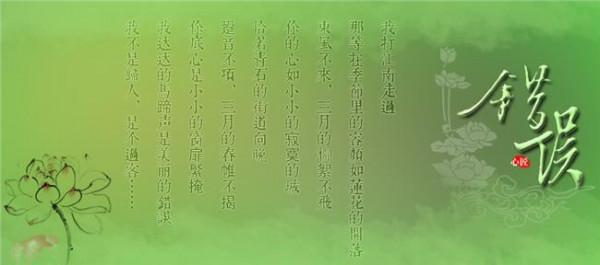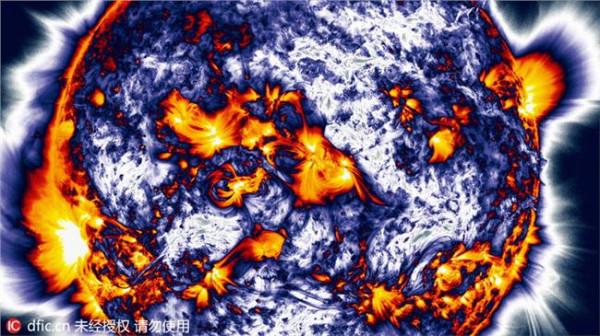郑愁予我打江南走过 我打江南走过——走近郑愁予的《错误》
读到这首诗我蓦地感到了一种异常清幽的意境——“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忽然想到稼轩的诗句,我这样去揣测诗人是不是有道理我不知道,想到江南,莲花,红颜,青石的街道,达达的马蹄,还有那漂浮在果园上空的淡淡的烟岚……忽然又记起沈从文先生说过,“凡是美的都没有家,流星,落花,萤火,最会鸣叫的蓝头红嘴绿翅膀的王母鸟,也都是没有家的。
谁见过人蓄养凤凰呢?谁能束缚住月光呢?一颗流星自有它来去的方向,我有我的去处”。
不肯在生活中麻木和沉沦的人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我从哪里来?我要到那里去?我为什么存在?”诗人就是经常把自己流放到“没有家”的美的世界中去,于是这才有一首首美丽的诗。当这样的精灵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时,她是无言的,但在无言中总是传递给我们性灵的回声,让我们体验到荡魂惊魄般的力量与冲动。
就象林青玄提到过的“水自竹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我想一首好诗它必定从诗人的胸中流出,就象“一些小小的泡在茶里的松子,一粒停泊在海边的细纱,一声在夏季里传来的微弱虫鸣声,一点斜在遥远天际的星光”。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细细品着这诗句,我忽然想起了一位书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都城南庄,夕阳半墙,一座古朴的庭院,两扇黑漆的木门,粉墙黛瓦,满院的桃花盛开。一位路过的书生,一位热情又矜持的少女,一个轻扣柴扉,一个穿过桃下的小径款款而来,一个满怀疲惫和忐忑,一个捧出满碗的清醇与好奇,一个捧水静静地喝,一个侧立认真地看。
这是讲授受之礼的时代,所以这样一个场景可能是闺中女子梦了千遍的,这样的场景也可能是风流少年想了千遍的。
然后他们对视,我想是应该有对视的,然后一个接下青瓷碗,慢慢的转身,轻轻的合上了门,也合上少女的梦,一个一步三回头,怅然但理智地离开。 据说一年以后,他又回来过,回来是为追寻还是凭吊我不得而知,反正他是回来过。
然而人已去,花依然。美丽的邂逅只留下美丽的遗憾。我不知道这一年里这位书生去了哪里,他的灵魂和肉体会在何处漂泊,他到底为了什么才错过这满院的桃花季节呢?这或许是最为中国式的一见衷情了,但男主人公必定有他更衷情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许多答案萦绕在空中,似乎都在为他辩解。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声囿于生计的长叹,一弯梦里的故乡。
总之,男人总是有男人的无奈吧。可是,桃园中的女子呢?她能去哪里呢?我想她能做的恐怕只有等待了,在等待中伤春悲秋。寂寂梧桐语,朝朝瓦上声,秋风不解意,犹自抚寒筝。可是无论多么玲珑的瓦片,可能参透她的寂寞?这样的日子又怎一个“等”字了得!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蛩音不响, 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这是怎样的一位佳人呀,最该是在美丽的江南,一位多情而自持的女子,她没有怨也没有恨,她也没有登上层楼去化为望夫石。
她既没有首如飞蓬,也没有指天誓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她只是默默的躲在镂花的窗棂后面,幽幽的静听外面的世界,等待着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曾经是一起绕床弄青梅,耳鬓厮摩的人,也许只是片刻邂逅中心动的人,但这个人绝对是已经融入自己生命和血液的一个人,她的全部动作竟然只有倾听。
她没有“望”,是千古以来女子的无望之望让她太伤感了吗?她只愿意把自己隐在窗扉之后。此刻于清旷宁静之中有马蹄声踏着青石板达达而来,愈行愈近,是那么真切——是他吗?真的是他回来了吗?她的心砰砰的跳着,你以为她就要伸出纤纤素手去揭开窗帏,然而她没有,她停住了,也许她的失望太多也太重了,早已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了吧,她的手还是缩了回来。
她只是悄然的伫立,凝神细辨足音。古人说能以足音识人,我是相信的。
马蹄声近了,更近了,然而并不曾做片刻流连,又径自向前了,当马蹄声终于远去,她垂下长长的睫毛,泪眼盈盈…… 那位打马而过的男子,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总会有这样等待的一位女性呢?达达的马蹄要去哪里呢?或者,他是乘着月光负着期待归去,是去慰藉那远方的身影未知的佳人?这里只是一个误会,一个小小的美丽的错误?如果不是,如果前方并没有期待的佳人,那他急匆匆的是要去哪里呢,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不让他停下来呢? 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 是个过客 过客,多么刺目的字眼呀,过客!
骑马的男子从江南走过,此时马前马后的江南,柔情牵翠柳,别梦曳君衣,空气中似乎都飘散着幽幽的愁怨。他分明感到了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他也分明能感受到在那青石的街道旁,在某一扇掩着的窗扉后面,有一双眸子早已将秋水望穿,可是他不肯停下来,他还是毅然前行了。
20世纪80年代,女诗人舒婷在神女峰上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其实并不是天下的思妇们始终不能看清,在自己的生命流程中男人们多半是过客而不是归人,在千年的等待与幽怨中才猛然觉醒。其实,伫立千年的神女是不得不如此,她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哪里有她们可以痛哭一晚的肩头? 那些义无返顾的男人们,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做为男性的诗人似乎要站在男人的立场,以男人的口吻对天下的思妇做一个交代,一个无可奈何的最近乎诚实和歉疚的解释: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但凡错误,遗憾,悲剧,加上美丽二字,似乎变得那么缠绵凄恻,那么让人同情。他们不归的原因很多,在女人的眼里无非有这样几种:富易交,贵移情,理解吧,这是社会的法则,我们虽然是落花有意,奈何流水无情,哪个时代没几个陈世美呢,忍了吧;也有的女子是为了成全男人的前途生计,想有朝一日夫贵妻荣的,怎奈“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也有“商人重利轻别离”,也有因为战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注定男人的灵魂和肉体不在一个处所栖息,这些都被自古以来的女子们和泪咽下了,她们似乎也理解了。
然而诗人似乎不甘心这些理由,在男人伟岸的身躯和无情的表现之下是否会藏着某种更深层的隐衷呢?真正能为男人的出走向女人做个交代吗? 作为女性,我宁愿相信有这样的理由,我也试图找到这样的理由。
自从母系社会成为过去之后,男人就觉得自己有太多的责任,有太多的梦想。
于是,在他们心目中最美丽的女性形象应该是在皎洁的月光下柔声哼着眠歌哄孩子入睡、同时静静等待男人归来的女人。但是断了乳的男人们往往只在梦中归去,他们觉得他们有太广阔的天地,他们象那追日的夸父一样永远在奔跑,在流浪,只要还没到大地的尽头他们就不会停下来。
是否大地上应该有这样一类男人呢?他们似乎比女人更执著于对生命的永恒意义的追问,他们不相信自己只是从母胎中落地的一个肉体——他们不停的追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有人为了象鸟一样飞翔,把一对大大的翅膀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高举手臂从高高的山崖上轻轻跳下;有人为了看天上的星星,掉进了地上的井里;有人大白天打着灯笼,像疯子一样在大街上奔跑;有人刺瞎自己的双眼,在无边的旷野上呼号……“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他们不想回避,也无法回避的是,人生短短几十载,谁能改变自己作为世间过客的身份,所以他们要求超越,他们要为自己也为人类找一条救赎之路,这是一条充满了孤独和骄傲的不归之路。
他们就这样成了过客,成了暮春三月江南女子在重重深闺中盼不归的过客。 在无尽的寻找当中,男人总是强迫自己背负责任,他们觉得自己的背脊足够宽阔,可以背负整个人类,他们总觉得自己强大,强大到足以面对生命中痛苦的觉悟。
他们不想回避,回避自己已经失去和必将失去的一切,他们义无返顾,不愿意逃遁于有意无意的麻木,不愿意回避生命在永恒的消逝中的短暂与渺小,正因为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所以他们更不愿意沉溺于无限的凄凉的脆弱与感伤,在冰冷的空虚之中他们决定要抓住点什么,从而找到出路,在根本上改变自己过客的身份。
他们的心灵渴望着超越,但这又不得不以牺牲尘世的爱为代价,让自己成为女人生命中的过客,这一切那么悲壮,又那么自然而然,所以,有一类男人,他们一生都在出走,走出家,走出女人温柔的视线,成为一个凄美的故事的主角,他们期望藉此走出原本残酷的生命规程。
男人满怀愧疚的宣称:我不是归人,我是个过客,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一任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这对男人何尝不是牺牲呢?他们不能栖息,他们注定漂流,在无尽的漂流中他们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相对人世来说,天地自然是那么神奇而泛着永恒的光芒,河流,山川,日月,星辰,他们看到了一条金光大道,古人说天人合一。
于是他们给人找到了一条救赎的路,——“仗剑走天涯”。于是李白醒了,他高唱着“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于是顾城醒了,他呢喃着“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于是海子醒了,他吟咏着“十个海子已经复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们都用尽自己的一生去寻找自己的天涯,他们冰清玉洁般与白云为伴,洒脱飘逸,超凡拔俗,他们深爱着大自然中那一切难以言说的,超然,神秘而又永恒的,无穷的美,在自然的无限中逍遥有限的人生,寄情于山水天地之间,遨游于长空飞云之侧,做天地间诗意的栖居者,从而获得精神的长驻与永恒的解脱。
天涯成为这类男人选择的一条救赎之路,为此他们牺牲了,牺牲了爱的幸福,牺牲了美丽的等待,所以这类男人在伊人的心目中始终是月亮,他们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就是沉浸在相思的潭底。
从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天下的女子,原谅他们吧,原谅男人所犯下的错,原谅他们近乎淘气的天真吧,男人的脆弱有时候超过女人,他们天真的认为只有出走才是无望的人生中唯一的救赎,这是他们在无边的沉沦中本能的呼号,让他们天真地去做他们的大地之子吧!
如果他们是夸父,奔跑就是他们唯一的意义。
做为女人,我们深知这对男人来说是一条无止境的不归之路,这是男人犯下的唯一的错误,我们还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爱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牺牲和放弃的正是人类战胜和超越的的唯一的利器,除了爱情人们还能依凭什么呢?其实要改变我们人生无望的过客的身份,只有让爱做主,这同样短暂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获得了神秘的永恒的力量,如果我们是女娲,就让我们守在河边,在夸父们倒下的时候让我们用爱去浇灌吧,那样天地间就是一片美丽的桃花,让我们依旧在桃花的掩隐下等待那个匆匆而来缺少爱情滋润因而坚强而又柔弱的过客吧…… 也许他明天就回来,也许他永远不回来。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