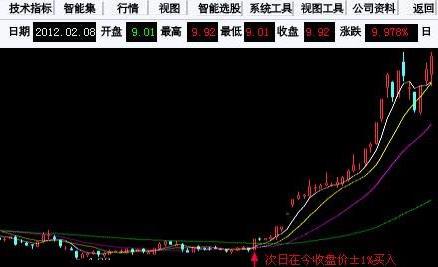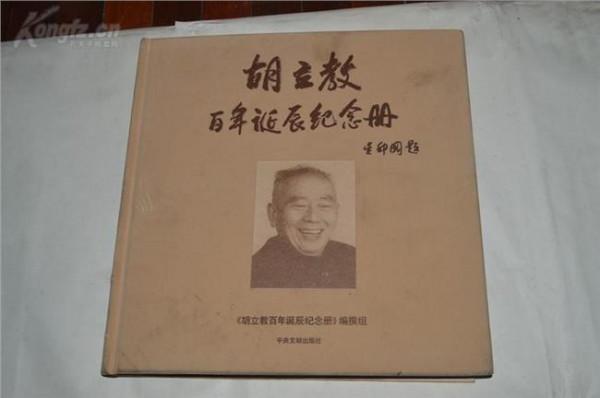陈丕显与胡立教 幸福与痛苦交融的记忆——怀念陈丕显叔叔
编者按:作者曹嘉杨、魏晓台、杨晓明是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 "陈曹魏杨"中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的子女。在陈丕显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三位作者联合署名,以此文章来纪念他们敬爱的陈丕显叔叔。
时光荏苒,倏尔而逝。 3月20日是敬爱的陈丕显叔叔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日,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经十年多了。翻看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字的《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叔叔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眼前,一幕幕往事宛如就发生在昨天。虽然时间流水匆匆而过,也难以冲刷他留在我们心中的深刻记忆。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人,尤其是上海人,大多对"陈、曹、魏、杨"四个字耳熟能详。"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就是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陈丕显叔叔和我们的父辈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在这场风暴的中心经历了他们政治生涯乃至整个人生中最凄惨、最悲壮的时期。如今,父辈们都已故去,在陈丕显叔叔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日里,我们再次撷拾记忆中的一些片断,也是对这四位前辈的共同纪念。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不仅陈、曹、魏、杨个人在"文革"中的命运相同,我们四家也有如此多的共同点——解放后,四位父辈同在上海市委工作;我们四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或比邻而居,或前后楼;"文革"中同被"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点名批判;同被打成"上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他们都有共同的"罪行"——反对前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他们四人同被关押在一处过了八年的监禁生活;我们四家同被扫地出门;被轰出市委大院后,又蛰居在同一个楼里,每家只有一间房,患难与共……
实事求是 矢志不渝
"文革"前,父辈们担任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职务,我们四家都住在康平路165号市委大院里。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我们的父辈和我们四家酸甜苦辣的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个院子里。
在陈、曹、魏、杨中,陈丕显叔叔年龄最小。他13岁就参加了革命,担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与胡耀邦一样都是党内有名的"红小鬼"。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出生入死,跟随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赣粤边游击区、苏中抗日根据地、华中工委等地担任领导职务,他和我们的父辈曹荻秋、魏文伯就是在战争年代华中根据地结识的。
1952年,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毅奉毛主席之命,急调陈丕显到上海工作,我们的父辈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也在此后来到上海工作。陈丕显先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代理第一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先后任常务副市长、书记处书记、市长;魏文伯曾任华东局秘书长和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到上海工作后,先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以及华东局候补书记、书记;杨西光先后担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的一段时间,正是父辈们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时候,也是中国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陈、曹、魏、杨四人有着共同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建设理念,他们虽然分管不同的领域,但都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当时"左"倾思潮和各项运动中依然能够努力坚持,显得尤为可贵。
六十年代初,陈丕显回到故乡福建,在庐山会议刚刚肯定了"大跃进",全国上下都在为"三面红旗"大唱赞歌的时期,他却如实地把自己看到的老百姓家无隔夜粮、经常有饿死人的情况写成文字汇报给福建省委,并想方设法调粮救人。
曹叔叔在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和陈叔叔一起顶住压力,做出了开放市区自由市场的决定,开放了十六铺码头等中心区的贸易集市,一时间丰富了市民生活,吸引了江浙一带的商贩入沪交易。他还大力发展捕捞渔业,组织了庞大的渔船队,丰富了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魏伯伯1925年就投身革命,他曾是华中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第一任县长。到上海工作后,他曾分管农业和血吸虫病防治等工作。"大跃进"中,看到有的农村干部弄虚作假,把别的田里的稻子搬到试验田,让粮食产量"放卫星",他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做法。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时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打电话急着要上海市粮食总产量的数据。魏伯伯核实后报了21亿斤,柯对此数字很不满意,大发脾气,非要魏伯伯多报。可是,魏伯伯在仔细核实后仍实事求是地上报了21亿斤。
杨叔叔也是年轻时即参加革命,到上海工作后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到市委工作后担任了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主抓宣传、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复旦大学是各种思潮极为活跃的地方,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之一。
杨西光在政治运动中总是力所能及地保护知识分子,维持正常的科研和教学,使大批知识分子免于或是减轻了被迫害。对此,复旦大学的师生们至今还铭记在心。2004年四、五月份,《文汇报》先后发表了章培恒的《追思杨西光先生》和叶鹏的《好人毕竟是好人》两篇文章,回忆了杨西光在当年"左"倾运动中关心、保护受到打击的复旦师生的往事,表达了作者对他深深的怀念。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中国社会"左"倾思想一日盛过一日。当时,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思想极"左",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是靠迎合各种"左"倾思想而飞黄腾达的。可是,陈、曹、魏、杨的政治品质、修养、素质、良心却使得他们不会跟风而动。
他们往往在不得不执行"左"倾路线的同时,又尽量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修正。他们尽可能地以自己有限的力量延缓着极"左"思想的执行,弥补极"左"思想带来的损失,为上海人民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
当时,上海搞了许多极"左"的、形式主义的"发明"。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在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时曾有一句令全党吃惊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这句话现在已查清是张春桥起草的。
其实这也不是张春桥、柯庆施的"发明",历史上就曾有过惊人相似的语言:抗战前,周佛海为拍汪精卫的"马屁"就曾说过"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
在国民党内,陈果夫因为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陈立夫则发挥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
柯庆施这种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话在当时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驳,反而得到欣赏,这也使他尝到了甜头。他又提出,要把毛主席着作办公桌摆一套,床头摆一套;工作中遇到问题,思想上想不通时,学学《毛选》问题就解决了。
对于柯庆施这些极"左"言论,许多正直务实的同志不以为然。薄一波在他《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当时柯庆施大吹上海粮食、钢铁产量如何翻番,异想天开地幻想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仅普及中小学,还要普及大学,让人人都能够读《资本论》,让高等数学、天文学、地质学、机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都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建成共产主义般的社会。
对此,薄老以鄙夷地语气写道:"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
他当时讲得绘声绘色,其神其态,我至今还能记得。这样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薄老在这本书中还记录了柯庆施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极"左"言行:"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
柯把毛主席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有。" 1957年12月,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很多人对"大跃进"中"冒进"的做法进行质疑的声浪中显得调门格外高。
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对柯庆施这个报告十分欣赏。1958年1月15日,"毛主席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还说,‘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对于柯庆施这些极"左"的说法和做法,陈、曹、魏、杨也非常反感,我们就曾听到陈叔叔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天天开会学《毛选》,连不识字的人也是《毛选》人手一套,这是搞简单化,强迫命令,形式主义。""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什么都是‘大’,大学、大用、大唱!"
"大跃进"期间,针对上海市一些单位不计后果大炼钢铁的做法,陈叔叔曾严厉地指示:今后钢铁生产不准再超过计划一吨。谁要是多炼一吨钢就开除谁的党籍。他就是这样硬逼着钢铁厂的炉子一个一个地停下来。他在当时就指出,要放下架子,收紧摊子,限期摘掉亏损的帽子。哪怕是赚一个铜板也是质的变化。这些后来被指为"追求利润第一"。
实事求是是父辈们共同的政治原则。对于这一原则,他们坚持了一生;因为这一原则,他们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默契合作 休戚相关
现在回想起来,因为他们的处事原则与当时的政治"时尚"相左相悖,在这种状态下工作,人的心情是应该很压抑的。可在我们的印象里,父辈们从来都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陈叔叔果断风趣,曹叔叔严肃持重,魏伯伯温和儒雅,杨叔叔睿智敏锐。"文革"前,我们在康平路165号的生活虽然也随着各种政治运动起起伏伏,但父辈们乐观向上的精神影响着我们,生活中还是充满了乐趣。
市委大院宿舍区里有8栋二层小楼,由东向西从52号一直到38号,分别住着陈丕显、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及四家的工作人员,杨叔叔家住32号公寓楼,就和陈叔叔家的小楼前后楼。本来靠近东边的小楼草地最大,按理说应该是分给柯庆施的,但据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说,柯对东边紧临德昌路的52号小楼的安全性有怀疑,于是陈家就住了52号。
不仅是对住处的安全性有怀疑,柯庆施对很多事情都有怀疑。他一直认为上海有个隐藏很深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很可能就潜伏在文化艺术界,于是就布置上海市公安局对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暗中进行审查,甚至对曹叔叔的亲属也暗中进行调查。
柯庆施患肺癌要开刀,也要先调查做手术的医生是不是特务,要公安局长黄赤波做担保。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陈、曹、魏、杨对他的这些做法很反感,并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反映过,而这些都成为"文革"中批斗陈、曹、魏、杨的罪状。
魏伯伯是四位长辈中年龄最大的,长期受胃病、心脏病的折磨。有一次,魏伯伯胃病非常厉害,柯庆施却一定要让魏下乡。拖了一段时间后,柯庆施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在市委常委会上对魏伯伯点名质问。陈叔叔站出来说:"魏文伯身体不好,我代他去吧。"在他们四位中,这种互相关怀、互相支持已成为一种默契。
四位长辈之间的个人友谊也是非常深厚的。魏伯伯精通书画,有一批文人朋友。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之外,大多都用于书画收藏上了。陈叔叔虽然不懂字画,但他认为魏伯伯的字就很有水平。他曾对魏伯伯说:"你收藏名家字画,我就收藏你的字画。
"于是,魏伯伯就给他写一幅字,陈叔叔看了问:"怎么不裱好了给我呢?"魏伯伯说:"这你就外行了。写好了字直接送你说明我的字身价高,要是我裱好了再给你就是在自降身价了。"至今,陈家有很多魏伯伯的字,送来时都是没有裱过的。
在我们的眼里,陈叔叔一直是一位幽默风趣、和蔼可亲的长者。他经常和我们这些晚辈开开玩笑,也得到了晚辈们的格外尊重。有一次,魏家的阿姨在打扫房间时弄乱了魏宏为的东西,宏为一赌气就把自己的房门关上,谁也不让进。
家人怎么劝她都不听,死活不肯打开房门。后来,魏伯伯上班的时候无可奈何地把这件事告诉了陈叔叔。有一天,陈叔叔在院子里碰上了宏为,他语重心长地说:"宏为啊,听说你家阿姨动了你的东西,你就关上房门不让人家进,这样怎么行呢?一个人要成大器,就不能这样气量小。
你现在就这样,将来怎么到群众中去,怎么到社会上去啊?"陈叔叔的一番话让宏为深为感动,回到家中,她就把房门打开了。魏伯伯看了说:看来还是你陈叔叔说的话管用。
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于培养革命接班人有一番很着名的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年轻人应当如何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但当时这番话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为了让下一代了解毛主席的这些教导,陈叔叔就把市委大院里所有的干部子弟召集起来,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传达给我们这些孩子。
我们至今仍然记得他说的这些话:"老一辈总是要退下来的,将来的革命事业要靠你们年轻人。说不定你们这些人当中将来就会有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但是你们应该按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要去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否则将一事无成。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聆听他讲话的孩子当中,如今有的已经确如他所说成了省部级干部,如梁平波、李源潮等。现在,我们对陈叔叔的这番话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65年,柯庆施因急性胰腺炎病死在成都,陈叔叔承担了市委第一书记的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风暴乍起,陈叔叔和曹叔叔一下子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1966年,陈叔叔因检查出得了鼻咽肿瘤,需治疗一段时间。
这样很多工作就落到了担任市长的曹叔叔身上。政治事件一个接着一个,风暴一阵紧似一阵,一会儿是"安亭事件",一会儿是"昆山事件",一会儿是"解放日报事件",一会又是"康平路事件"。在对这些事件的处理中,曹叔叔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于是成为张春桥等人阴谋陷害的重点人物,成为造反组织斗争的主要对象。
无论怎么被批斗、诬陷,他从不诿过,从不推卸责任,甚至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病中的陈叔叔一直觉得在曹叔叔所受的委屈和痛苦里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代他受过,为此,他内心里常感到十分难过。尤其是曹叔叔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就不幸病逝,让陈叔叔更觉得非常痛心。
其实,当时陈叔叔虽然身在医院,但也并没能安心养病。他经常要与曹叔叔、魏伯伯等研究如何应付各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局面。按照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既尽量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又不能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他们把这称作"走钢丝"。
杨叔叔在市委分管教育工作,又曾担任过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由北京高校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也漫延到上海,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市委领导里最先受到批斗冲击的对象。陈、曹、魏则在与造反派一次次的交锋中,与上海的"政治新贵"们积怨越来越深。
那时候,康平路165号院里住着的各家各户也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而分为不同的圈子,虽然我们年龄还不大,但也明显地感到那些在那场政治运动中暴发起来的邻居们对我们已经"白眼相加"了。杨叔叔家楼上楼下分别与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家比邻而居,那些红得发紫的人对我们不仅加以"白眼",而且要怒目而视了。
"文革"开始后,各省市都有被"两报一刊"点名批判的领导,但一般只有一名。上海市最多,陈、曹、魏、杨四人都被点了名。其实,陈叔叔本来是有可能不被打倒的,江青、叶群都曾下大力气拉拢过他。1965年柯庆施病死成都后,林彪、江青欲重新扶植在上海的代理人。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要在北京召开,当时陈叔叔正因为鼻咽肿瘤住院,叶群亲自把电话打到陈丕显家中,让陈叔叔的夫人谢志成阿姨陪他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她又是嘘寒问暖,又是登门送礼,希望陈叔叔不要"落后于形势",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
会议期间,江青两次请陈叔叔和谢阿姨吃饭,说曹荻秋、魏文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并"语重心长"地说怕陈叔叔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要陈叔叔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可以当他的顾问。她一遍遍提出这个问题,陈叔叔却一次次以"身体不好"等理由搪塞过去。
1966年底由上海造反派引发的中断京沪铁路运输的"昆山事件"发生了,1967年元旦凌晨,陈叔叔接受周总理的指示,临危受命,出来主持工作,解决"昆山事件"。这距离陈叔叔拒绝江青拉拢,拒绝出来工作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周总理一声召唤,陈叔叔马上就出来工作;江青软硬兼施,陈叔叔却不为所动。陈叔叔的这一举动最终激怒了江青,1967年4月,她在那篇臭名昭着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气急败坏地把"红小鬼"陈丕显骂成"黑小鬼",说陈丕显是"死不回头"。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幕后操纵下,上海的造反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部门大权,刮起了夺权的风暴。"一月革命"使上海一时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心。
1月6日,他们把陈、曹、魏、杨等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揪到台上批斗,还把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数百人拉到台上陪斗。即使是在这次批斗之后,因为他们并未被中央免职,也没有失去人身自由,他们还得一边接受批斗,一边组织生产。现在想来可笑,父辈们一面被人家喊着要打倒,一面还得坚守岗位,为上海市的稳定尽职尽责。
1月12日,张春桥等人策划了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几十万人的大会,继续揪斗陈、曹、魏、杨及其他市委、市人委领导,部局领导都被揪到台上批斗。事前,大家都听到消息,知道这场批斗是一次难过的"鬼门关",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父辈与我们心中都充满了生离死别的悲怆。
12日早晨,陈叔叔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向家人告别。虽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家里人心里都明白,此去凶多吉少,陈家的孩子们扑到陈叔叔怀里喊着"爸爸",泣不成声。这样的生离死别的场景在陈、曹、魏、杨等所有被批斗的人家里都同样出现过。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他们四人开始被关押,一关就是八年。
失去人身自由后,父辈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曹叔叔曾被架到修理电车线缆的高架车上,反剪双臂,颈悬木牌,强令跪着游街示众;杨叔叔曾被红卫兵们拳棒相加。"车轮战"、"蘑菇战"式的审讯更是父辈们经常享受的"待遇"。
陈叔叔的夫人谢志成阿姨、曹叔叔的夫人石斌阿姨相继失去人身自由。在杨叔叔被关押期间,其夫人卢凌阿姨郁愤而病死。我们这一辈也都成了"黑帮子女",有的被抓进监狱,有的被批斗,有的被流放外地。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政治暴发户"们、造反干将们把人性中最丑恶、凶残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
那时候,我们四家已经被抄得一贫如洗,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即使这样,造反派并不死心。有一次,造反派又到陈家抄家,当时陈叔叔和谢阿姨都已被抓了起来,家里只有十四五岁的女儿。魏家大女儿魏晓路把吓得浑身颤抖的陈叔叔的女儿藏在自己家,造反派要魏晓路把人交出来,晓路气愤地质问他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懂得什么?你们为什么非要和她过不去?后来,公、检、法以"反对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为由抓捕陈、曹、魏、杨在上海的孩子,魏宏为则千方百计通知陈叔叔的女儿千万别回上海,以免也被抓走。
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在当时的情况下,四位长辈之间、我们四家之间彼此互相给予的支持、关心与帮助,也能使处在严冬中的心灵得到些许慰藉。1968年,魏伯伯在监禁之中曾写下了一首诗:
饥饿思饭好,
疲劳知床亲,
岁寒识松柏,
贫困见人心。
粉碎"四人帮"后,他还为这首诗加了段小序曰:"1967年,‘四人帮’以余四次被国民党逮捕、三次‘叛变’为借口,将余监护于上海康平路71号,同时隔离于此者,有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三同志。"
"一月革命"后,我们四家被扫地出门,一起被赶出了康平路165号,被赶到了武康路117号,十分拥挤。当时,陈、曹、魏、杨四人也被关押在一处。关押他们的房子是"文革"时期没收的荣毅仁的房产,是一座小楼。他们四人也是每人一间。"文革"之后,陈叔叔曾风趣地对荣毅仁说:"你住在你家小楼的时间还没有我长。"
特殊的政治时期给予陈、曹、魏、杨四家如此相似的命运,不仅父辈们的政治命运相似,我们四家的家属子女的命运也如此相似。父辈们革命一生,当时却全都成了"反革命"。张春桥、姚文元为了他们卑劣的政治目的,组织了一个又一个调查组,跑遍全国各地,挖地三尺也要找出"叛徒"的罪证。
作为"走资派"、"叛徒"的子女,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了社会的"异类",都成为被另眼相看的对象。这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现在想来,那段经历对我们也是一个经风沐雨的考验,是一个难得的锤炼意志的机会。
父辈们被关押了8年之后,由于中央一些老同志的关心,他们于1974年先后走出牢笼。人虽放出,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种种罪名并没有洗刷。陈叔叔出来最困难,是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许多老同志想方设法搬动了毛主席,才被"似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放了出来。
在陈、曹、魏、杨中,只有曹叔叔没有看到"四人帮"的灭亡,没有等到自己问题彻底解决的那一天。在离粉碎"四人帮"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却猝然离开了人间。每每提及曹叔叔,父辈们总是唏嘘不已,悲从中来。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一些老同志的关心下,陈叔叔很快被安排了工作。当时,由于"四人帮"安插在各部门、各领域的党羽还掌握着实权,很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魏伯伯从1974年被放出,一直在家赋闲,到1978年还没有解决工作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叔叔和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等人言辞激烈地质问:为什么魏文伯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了,到现在还不解决?他们的这些发言被刊登在三中全会的简报上,促使魏伯伯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12月底,魏伯伯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79年司法部恢复后,魏伯伯出任了"文革"后第一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兼部长,重新组建司法部,开展了大量基础工作,创办《中国法制报》,恢复了法律出版社,使被十年动乱严重毁坏的司法工作有了良好的起步。
杨叔叔在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光明日报》主持了着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为人们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推进改革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这一讨论的进行过程中,由于极"左"思想在以往二十余年流毒甚广,反对之声甚嚣尘上,杨叔叔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陈叔叔多次打电话给杨叔叔,鼓励他不惧压力,把讨论坚持下去,澄清人们的思想和认识。
党的十二大后,陈叔叔到中央书记处工作,主管全国政法工作。对我们这些当年曾身前膝下围绕在身边的下一代们,他一直很关心。我们到北京去看他,他总是非常高兴。有时候到我们工作的城市来视察,他还会打电话把我们叫过去聊天叙旧。
在陈丕显叔叔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写下这些文字,既是对他老人家的追思,也是对父辈们的共同怀念。如今,我们也已经不再年轻,而陈、曹、魏、杨四家共命运的往事也成为我们这代人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段记忆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感到幸福。无论如何,我们都将珍藏它、珍视它。










![《胡立阳股票投资100招》[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3/9b/39b6ad5efac48b885e7e6a951e0e14b6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