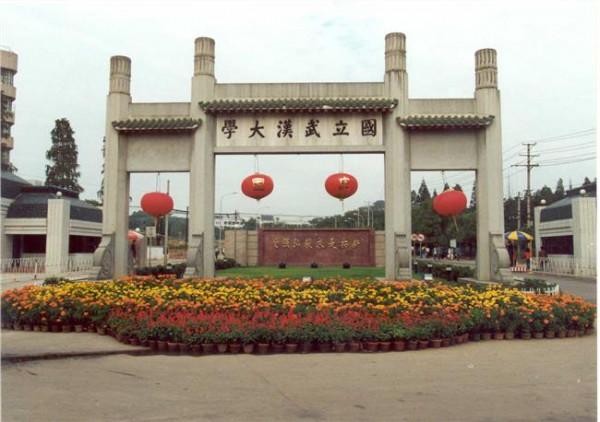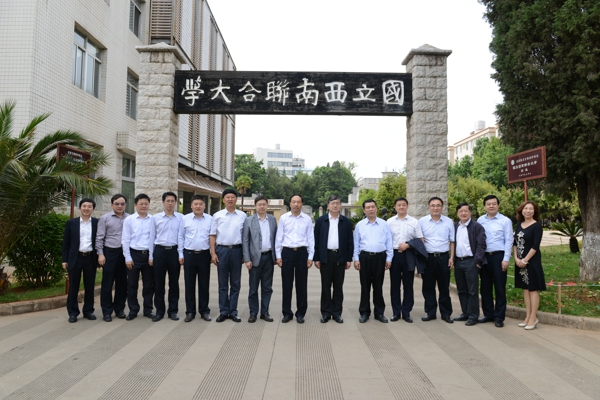张旭东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 张旭东论中国梦:终于到了可以谈梦想的时刻
但我非常反对那种唱衰美国论调。美国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非常非常强悍、非常非常顽强的一个国家,一次次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原因是什么?毛主席说过,“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它是一个革命国家,不信邪,有创业精神,有草根精神。
底层人民往上爬的动力十足。它有移民,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美国,要不惜一切为自己立足脚跟,为他们的子孙创造幸福的生活。这种动力和我们农民工进城,一定要过上好日子,哪怕我这辈子完了,只能打工了,但是我孩子要上大学,要做公务员,要怎么怎么样,这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低估美国,不要过早地把美国梦勾掉,因为美国梦同样是一个大众革命制度创新和文化自我表述、自我创造,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实验。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革命性和创造性跟“中国梦”在指向意义上是一样的。
但是差序结构差在哪呢?它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的一个竞争平台,而“中国梦”的历史主体具体承载者是第四等级而不是第三等级。是整体上和结构上还被关闭在中产阶级梦之外的那个世界历史的下一种人,中国人、印度人、亚非人,是那个文明孤岛之外黑压压的大众。
他们也要开始做梦了,他们要成为世界历史的民族,来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国梦”一定要确立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格局上,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后发美国梦而已。
第四等级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阐释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从最近的一次世界历史革命获得很多很多的灵感源泉,这在欧洲历史上看得很清楚,1848年的时候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专政意义上与资产阶级专政决裂。
这个历史脉络在经典马克思史学、政治学、国家学、阶级学说得非常清楚、非常精辟。1848年是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就是世界历史的普遍民族,他的梦想就是所有人的梦想。1848年以后他的梦想只是他的梦想,因为他要压住下面的人,不能让下面的人来造反。
他在砍光贵族脑袋的时候,同时转过身来开始砍工人、贱民的脑袋。我在回国的飞机上看了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电影版,觉得很好,前半版部底层人所受的压迫和虐待、后半部巴黎其以的牺牲场面都激动人心,但那是对当年市民阶级革命时代的牺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怀旧式的歌颂。
市民社会至今仍念念不忘自己当年曾经是无私的、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即在争取自己解放的时候愿意并可能解放所有人的。但它后来坐稳了江山后意识和态度就不一样了。
中国人这次能够起来,那么进入世界历史的这个阶层的基数要大得多、穷得多,数量很大。所以它进去以后要改变这个世界历史的基本语法,不改变的话就不过是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非常微弱、苍白的一个回声。
再具体讲,在中国今天这个具体的经济环境来讲,我觉得“中国梦”必须定义为劳动者的梦,是生产者的梦,而不是消费者的梦,是奴隶的梦,而不是主人的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奴隶制的奴隶,而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的奴隶。
在存在的意义上讲,假设两个人,跟两个狗熊一样,在丛林里相遇,一个人是为荣誉而战,我可以不要命但我一定要当主人,绝不服从。另一个人打到后来说,我还是要留下一条命,我就让你当主子,我可以给你干活,但你要保证我的安全,这就是寓言意义上的主奴逻辑,一个变成了主人,一个变成了奴仆。
主人因为在生死搏斗中是获胜者,他胜利的果实是无偿享用他人的劳动,我歇着,你给我干活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买卖。但是时间长就不对了,奴隶每天在接触生产资料,每天在创造财富,每天在获得新的经验、知识、智慧,理解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人之间通过劳动形成的关系,充分领会到人通过劳动不断生产出新的价值、新的自我。
在劳动和生产的具体性里他意识到他能够做什么。
这个转化非常简单,有一天他意识到他不再是一个锤子或者砍刀,他是一个大机器,是社会组织、是工会。为了生产而赋予的条件,简单来讲把这些归结为工具,同时是武器,那个时候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而主人生活在那个颓废的世界,艺术创造啊、玩电影、玩高尔夫啊之类的生活享受,他就会越来越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变成一个简单意义上的食利者。在这个意义上,“主人的真理在奴隶”,这是黑格尔政治经济学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他的真理性、他的实质性、他所占有财富不在他这,完全在奴隶那边。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生产者的定义的确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定义了,它一定包括知识、科学技术、管理、创意和文化生产领域里的劳动者生产者,即一般意义上的白领工薪阶层和创业者阶层。
所以“中国梦”不仅仅是为近代中国集体性历史诉求所推动和激励的梦,也必须是面向当下、立足于劳动者自身素质、技能、经验范围和内心丰富性不断提升的梦。这和毛泽东当年反复强调:新中国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是一定要建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是一个道理。
“中国梦”的历史实质性,必须建立在这个意义上的奴隶方面。因为这个民族从最下层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能通过劳动,不能通过重复殖民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或技术资本垄断、或不公正国际秩序来获得,而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工作来争取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体系、贸易体系、政治体系。
在这之前,必须在一个相对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下,通过自己的劳动、勤奋、努力、牺牲,逐渐逐渐让自己的主观性,对生活的理解,对价值的理解,对友谊、正义的理解,通过物质生产、劳动的财富的积累,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
这既是一种必然性,也是一种自由。这样意义上的一个辩证法,是一个生产者的梦,也确实是一个集体的梦。所以“中国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暴发户的梦,而只能是一个新的劳动者主体的长期的、坚韧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梦,因为这个梦一头连着一个有待实现的未来,另一头连着一个遥远的过去,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有着一个久远的过去和一个长久的未来的民族,不应该是一个短视、投机、草率、侵略性的民族。
我觉得这种特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什么农耕民族的民族性,而是基于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一个文明大国的基本标准,正是看它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是否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也就是说为所有人、为人的根本定义带来持久的意义。最后这一点才使“中国梦”的终极意义。我们这个时代不过是在为这样意义上的“中国梦”做准备。我们的准备还做得远远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