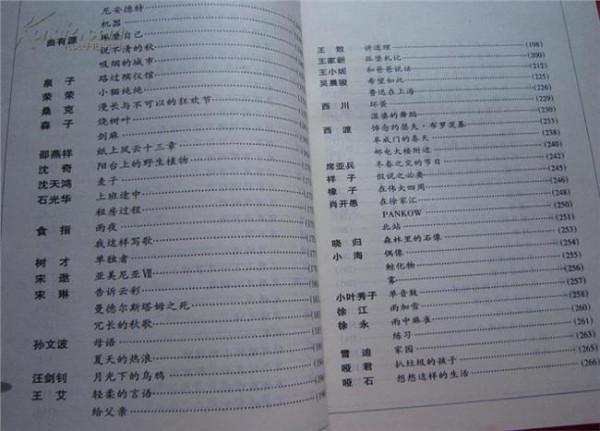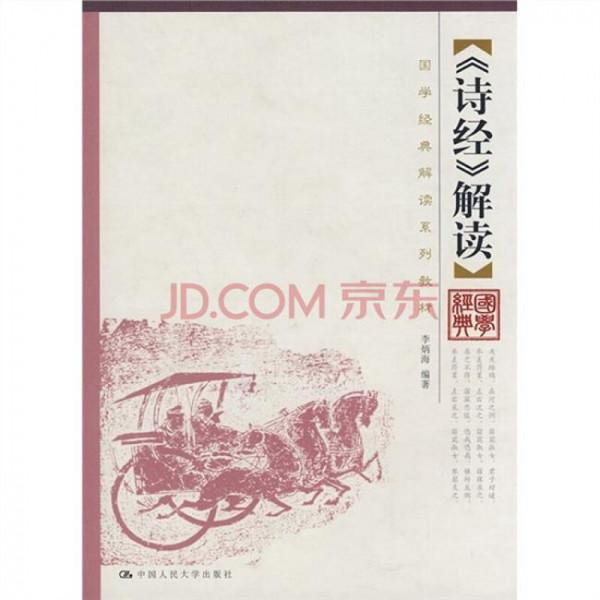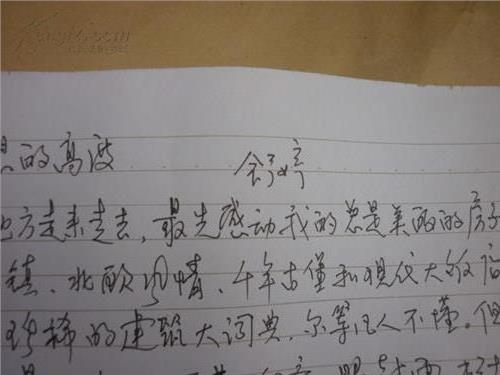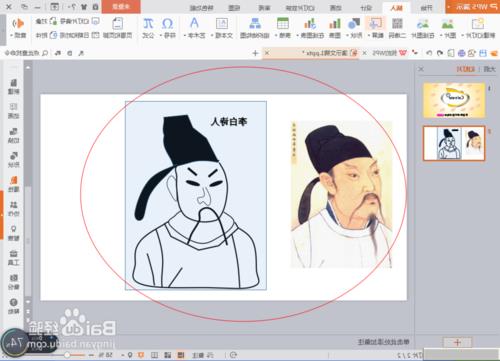诗人宋炜 诗与根宋炜诗歌论
八十年代,在四川兴起的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先锋诗歌团体中,很多年轻人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化——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还有那些不属于任何主义,或被牵强附会,却一心朝向古旧事物(敬文东语)的诗人们。
敬文东形容宋炜年轻时候的样子为"当代古人"。 传说中的龙有九个儿子,性格却各不相同,爱好音乐的囚牛,喜好静坐的狻猊,嗜杀的睚眦……纵然同样是将目光投向了古老的母语,诗人们却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在柏桦那里,是一种旧式文人的享乐情结:"在清朝/诗人不事营生、爱面子/饮酒落花、风和日丽/池塘的水很肥/两只鸭子迎风游泳/风马牛不相及"(《在清朝》);在张枣那里,则是母语的温柔性与现代性的微妙融合:"我挪向亮处,/那儿,鹤,闪现了一下。
你的信/立在室中央一柱阳光中理着羽毛——"(《春秋来信》)。
而在诗人宋炜这儿,母语的光彩则浸润于一种饱含乡土气的世俗生活中。多年前,合署宋炜、宋渠两兄弟名字的《琴》还沉浸在无关人间烟火的气息中: 至此书生挂琴于壁 又焚谱祛寒,室内一团和气 他在井中洗手,冲淡半生手相 指下无音,只是插柳或撒下花籽 然后坐于苔上,长日听水:书生已深得琴 理。
时间和人都在改变,被称为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过去了。多年后,宋炜诗歌中的琴音已经是街头人和事交响而成的乐曲: 来了一个肥婆…… 看她两只巨大的屁股/波动着,分开两边的 人流,一种 节奏稳定的低音,像东坡肘子般结实的 贝斯的轰响,溢着油,成为乐队的基础 小号出现了——一个瘦精精的小街娃,东张 西望,目光闪烁 到处都在拆迁,到处都在修造动土。
一根根 又瘦又长的吊臂在头顶东晃西晃,像一批 无弦可拉的长弓 (《解放碑的音乐》) 也许,逝去的不过是人们的年华;改变的不过是诗人们从高蹈的理想主义姿态中走出之后,打量世界的眼光。
就像宋炜年轻时的"天涯"和多年后的"天涯"所形成的对比——一个是:"你和我,不会这么永远浪迹。/我们将经历他们所有秘密的异地,/伤痕累累却心地洁静,/走过天涯就定居"(《户内的诗歌和迷信·组诗中唯一的一篇劝导文》);另一个则是:"现在就算我们一道/往更早的好时光走,过了天涯都不定居,/此成了彼,彼成了此,我们还是一生都走不回去"(《还乡记》)。
敬文东在写宋炜《还乡记》的文章中已经指明:"一边是多年前不会‘永远这么浪迹’下去的乐观,一边是短暂乐观后‘一生都走不回去’的心绪上的绝对荒芜"。
和八十年代的很多诗人一样,宋炜的故事也 传奇般地镌刻于那部传奇的八十年代人物史中。洁身自好与荒唐都成了人们捕风捉影而又津津乐道的谈资。和"天涯"产生的变化一样,多年间经历的荒唐而又荒诞的生活为曾经超然于世的琴韵染上了俗世间的喜乐与哀愁。
(一) 对于诗人来说,母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像柏桦那样,作为她受宠的小儿子,继承着她安闲、享乐的一面,偶尔来点不伤感情的怪癖或情绪。
还是像胡冬那样,彻底决绝地将自己放逐于她之外,让"遥远的母语把诗人从流放中辨认出来,保持他,并赋予他无限的忠实和忠实的自由。"宋炜身上有着南方诗人(尤其是四川诗人)的享乐性、颓靡性与精致性——钟鸣一再强调北人好经世之想,而南人"喜欢精致的事物,热衷神秘主义和革命,好私蓄""多愁善感,实际而好幻想""生活颓靡本能,却追求精神崇高"。
诗人从未离开那片滋生腐朽与精致的土地,调笑式的、沾满油烟味的句子几乎是信手拈来: 模特儿白鹭…… 白日闪电, 一串惊雷像饱油的酥肉滚进院子;而我们在雷电之上欢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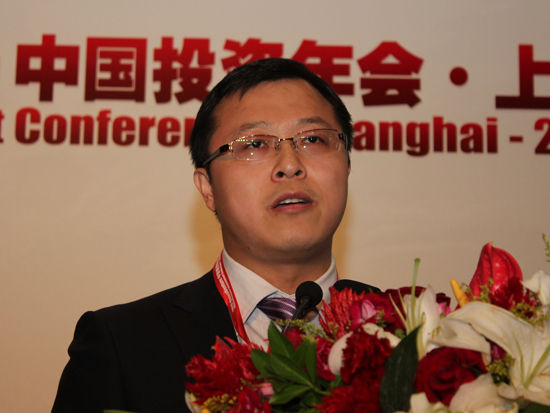






![李元胜诗歌 [海南周刊]诗人李元胜:海南将成诗歌重镇](https://pic.bilezu.com/upload/2/1e/21eb9172197f206468c08275c9e4146b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