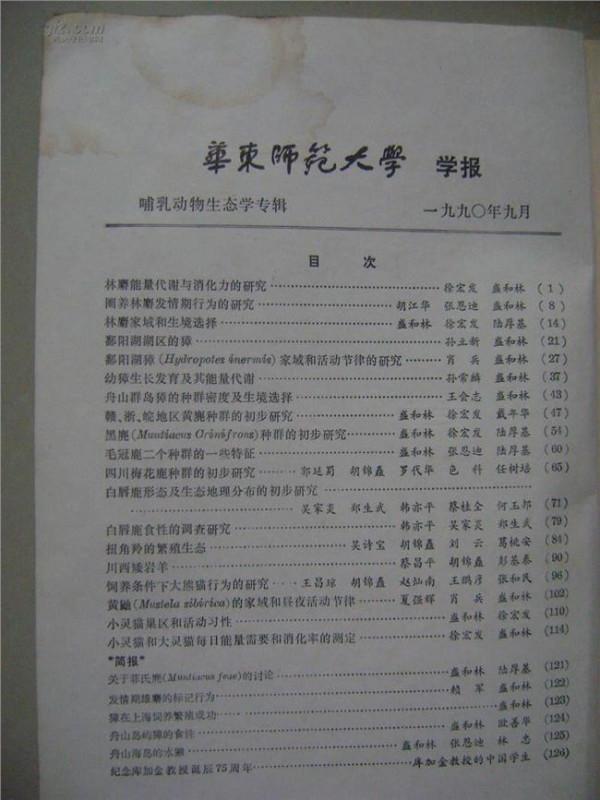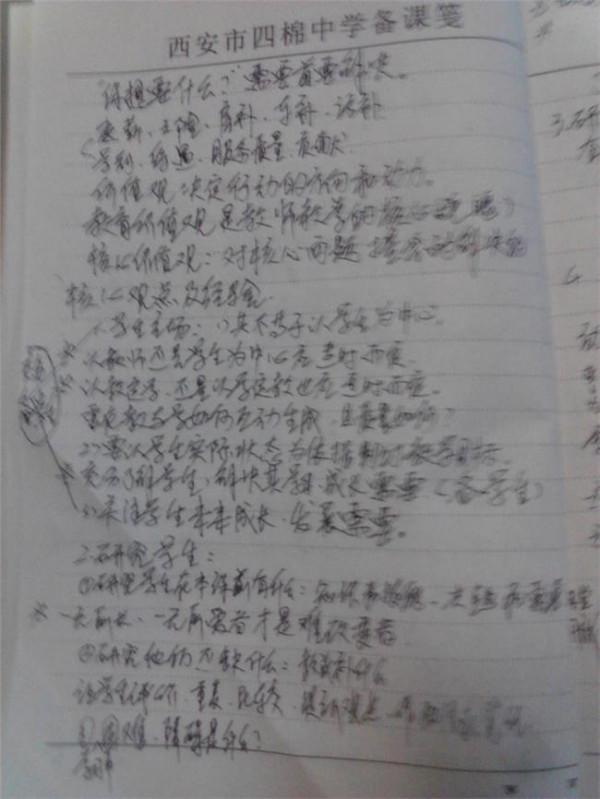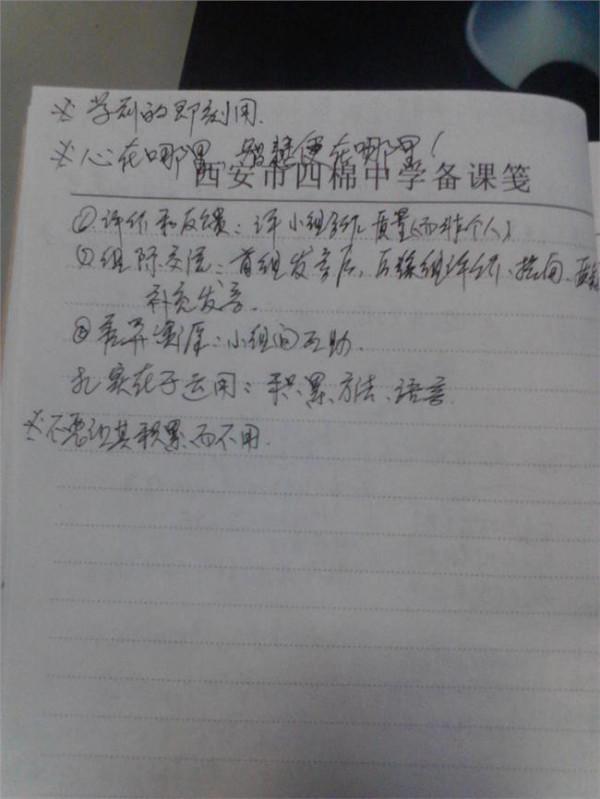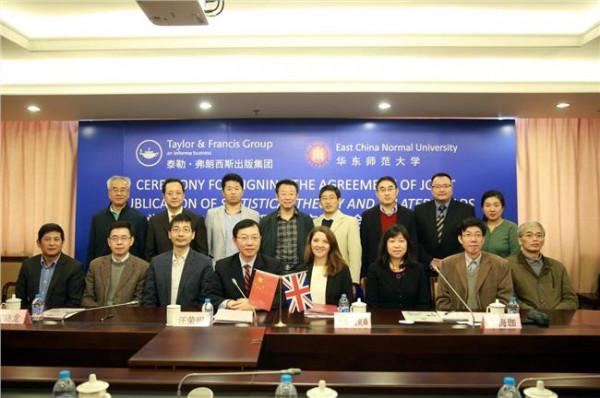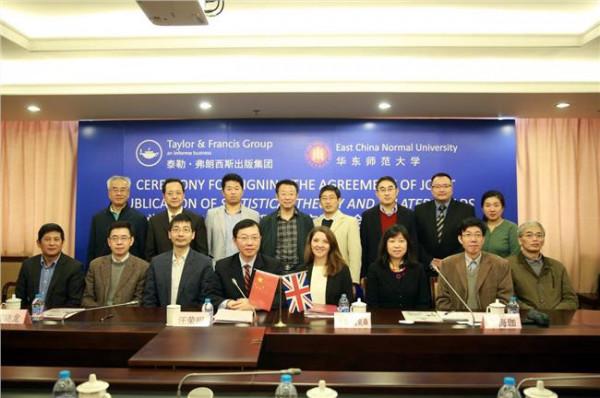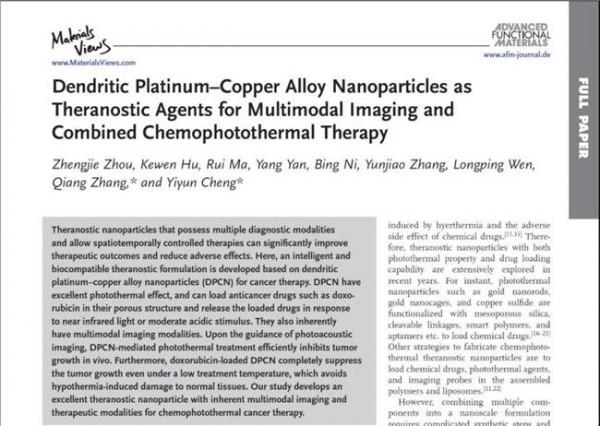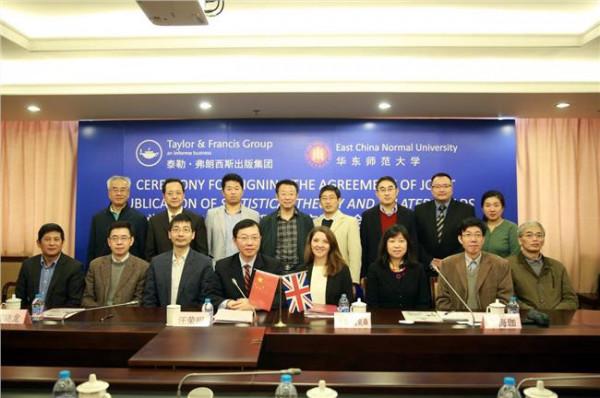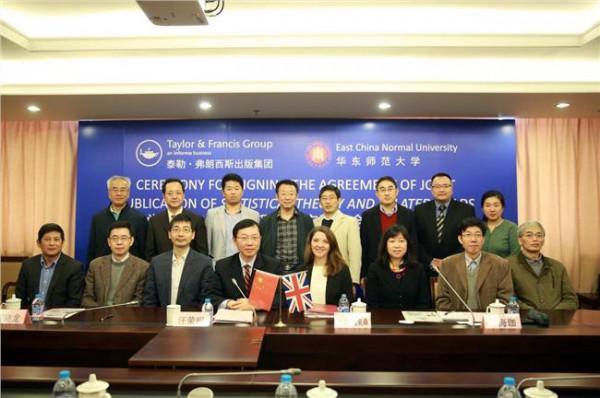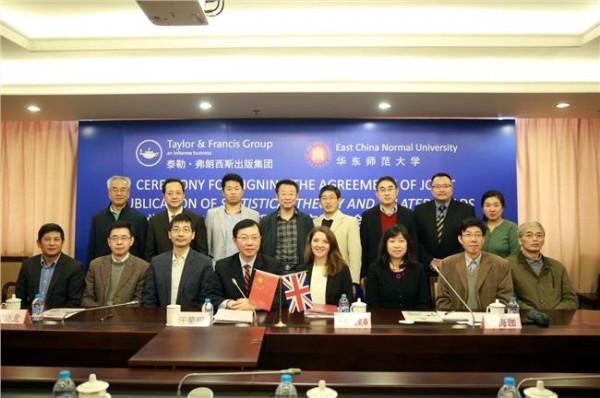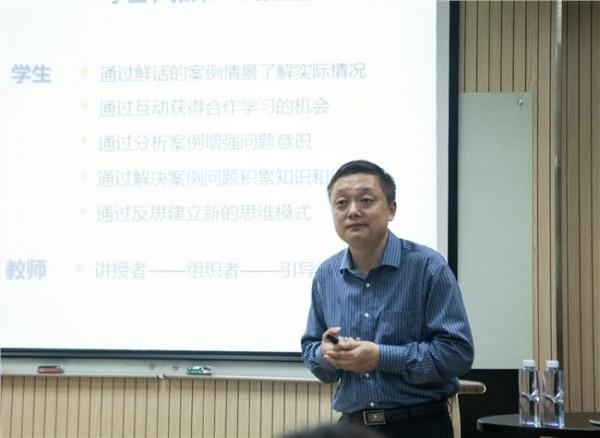李政涛华东师大 《华东师范大学校报》:李政涛:徜佯在洪堡与世界学术之间
当我尝试用文字记录在德国访学一年的收获时,突然感觉到了语言的限度。即使叙述的只是如此短暂的时光,语言的苍白乏力依然暴露无遗。
最先跳跃而出的景象,是德国的雪景,那是我抵达柏林后的第一个早晨收到的第一份礼物,虽然白茫茫的雪景与国内并无二致,但由于空间的移置换位而有了不同的意义,德国气息和德国味道在天际间四处弥漫渗透。我的德国学术之旅,就从这一场雪开始了。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我来到了柏林洪堡大学,这是我安身栖息一年的场所。黑格尔曾言: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辉煌灿烂的德意志文明。黑格尔本人也出自这所大学,除此之外,哲学家费希特、叔本华、谢林、马克思、恩格斯,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法学家萨维尼,文化批评家本雅明,政治家俾斯麦,以及包括爱因斯坦、普朗克等在内的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精英人物,要么在此任教,要么求学于此。
对于德国人来说,"洪堡"既是大学创设人洪堡兄弟的姓氏,也是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更是德国大学精神的象征,无论是"研究教学合一",还是"对科学的探求"和"个性和道德的修养",以及对学术"寂寞与自由"的追求,都对德国乃至世界大学教育影响深远。
洪堡大学也因此成为"现代大学之母",是霍普金斯大学等诸多大学效仿的对象。
我的合作导师汉茨教授曾经告诉我,在一次洪堡教授会议上,校长对全体教授坦言:"你们,身为洪堡教授,是终生的荣耀……"
中国人的"洪堡记忆"与蔡元培有关。这位当年的洪堡留学生,为洪堡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如今的洪堡大学图书馆专门有一排著作集聚一处,共同的主题是"洪堡、蔡元培与中国教育"。一代代的中国学人,沿着他的足迹纷至沓来,并积淀凝结为"洪堡情结"。
当我每每用言语和目光触及到"洪堡大学"这一校名,尤其是第一次目睹洪堡行政楼墙壁上所刻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不只是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之时,滋生出的不只是"亲切",更是"敬意"了。
我对自身的洪堡访学之旅的目标定位,在于"把握和进入德国教育学术的传统和前沿,与中国教育学,特别是‘生命·实践’教育学实现衔接和转化"。在中国教育学创设过程中,以康德教育学、赫尔巴特教育学为代表的德国教育学,起到了奠基作用,用"魂魄"二字形容其地位也毫不为过。
在洪堡与德国教育学的首次"亲密接触",是参加汉茨教授的一位博士生论文答辩。论文以"德国、加拿大留学生的文化认同比较"为主题,作者是一个德国小伙子,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前后历经5年完成。答辩过程中,他全程站立,侃侃而谈,不时面临微笑,丝毫没有怯场拘谨的神色。坐在对面的三位教授也沉稳有度,在提出质疑、表达观点的间隙,不时翻阅论文,我在旁边偷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论文中那些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批注。
用"严谨"、"认真"、"古板"等来形容德国人,是我们的习惯,这也是德国著名教育学家本纳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与他的最初相遇,是在华东师大的一次报告现场,本纳先生的报告基本上是照稿念,这种讲法让我心生疑惑:这不是"照本宣科"吗?后来聆听了更多德国教授的讲演,才略有所悟:他们力图让自己的言说有根有据。
当我在洪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与本纳见面时,他的表情明显比在中国时生动鲜活,须眉皆白的他阐述观点时甚至会"手舞足蹈",使我恍惚间有了错觉:这是不是另一个本纳?同样的疑问也发生在布因克曼教授的就职仪式上。
为新任教授安排就职典礼,并由"新人"做一个小时左右的学术演讲,随后是所有来宾集体合影并有一个冷餐会,这是洪堡大学的传统之一。
作为本纳教席继任者的布因克曼,那天讲演的主题与"教育现象学"有关。他给我的感觉也是"不苟言笑"、"中规中矩",偶尔透露出的"幽默"很快被更幽深的学问所压制和湮没。据选他课的中国学生反映,该教授作业和考试要求严格到"冷酷无情",大家都抱怨连天,暗生悔意。
但有些特定场合,他是特别放松的,如谈及自己的妻子儿女时,他的眼神陡然会充满柔情,幸福之意在绽开的笑脸间荡漾。我对他的访谈,是在当年本纳的办公室进行的。整个访谈之轻松惬意,我们彼此在很多观念上的默会契合,甚至"息息相通",大大超乎我的意料。我在访谈结束时的一句感叹绝非恭维之语:"您是一位纯正的德国教育学教授"。他为之微笑不语。
从这些德国教授身上,我感受最多的是"真"、"情"二字,学术的广度、宽度、深度和厚度无需多说,更打动我的是在他们的眼神和行为细节中展露出的"求知"、"求真"的学术情怀,在他们那里,"为学术的人生"和"为人生的学术"已然不分了。
在他们身上,我还看到了一种开放与保守之间的张力。大学的开放精神,不仅体现在没有校门、围墙,也不只展现为所有人,包括流浪汉、乞丐等,都可以进入洪堡大学浏览和借书,洪堡大学的校园卡、上网号可以在全德国任何一所大学通用,更体现为一种包容、大气的胸怀,所以他们的眼光和视野是世界性的,绝不会拘泥于某国、某门、某家和某派,而是综合中的融通或贯通。
但任何开放都有自己的限度,所谓"保守",并非"因循守旧"之意,其底蕴是对某种精神传统与核心价值的一以贯之的保护、坚守或持守,其背后是对传统精髓的敬畏与尊重。
德国教育学并非完美无缺。一年间的置身其中,我先后借阅浏览了200余本书,购买了200余本德语著作,扫描了近20年期间代表性的数百篇德语和英语论文,勾勒了德国教育学"学术地图",涉及德国教育学术界各学科领域代表性的期刊、出版社,代表性的流派、人物、著作及其联系方式,这些努力使我在理解学术意义上的"德国传奇"的同时,也消解打破了"德国神话"。
通过发现德国教育学界的"所见"和"所不见",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德国教育学因此得以显现。
在离开柏林之前,我在洪堡大学面对100多位德国教授和学生发表了学术演讲,并与他们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互动交流。德国师生充满了对中国教育(学)历史与现状的好奇,但他们的提问,虽然不能用"幼稚"、"简单"来描绘,但至少让我"见证"了西方人对"中国教育(学)"的"无知",也看到了两国教育学研究上的差异。
例如,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德国教育学要么在书斋和文献堆里,梳理教育的历史,构思教育的理想,畅想教育的未来,让各种创意风暴在头脑中呼啸;要么到中小学去,以旁观者和打捞者的身份,捕捞各种资料,转化为各种论文和著作,但对实践本身的改变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因为他们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斯·韦伯有关研究者必须"价值中立"的信念。
即使有学者强调要关注实践,把实践作为理论创生的源泉,也只是抽象的言说和思考,且仍旧是用理论与实践脱离的方式言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关系变成名词性的书本中的关系。
相比而言,中国教育学界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是一条"上天入地"、"顶天立地"、"知行合一"式的理论与实践双向转化之路,它来自于通过多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长达20年的"新基础教育"研究是这一道路的发掘者、开创者和代表者之一。
我们当下所亟需的是如何实现"中国元素,国际制造,中国经验,国际表述",即如何把中国经验变成世界经验,变成他国同行可以理解更可以转化运用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我们最需要强化的是"中国自信"和"中国自觉",面对作为先行者的德国教育学,乃至世界教育学,我们首先是"倾听者"、"学习者"、"对话者",但不能止于此,我们还可以成为"竞争者"、"创造者"、"贡献者",我们不能满足于永远只是"跟从者"和"取经者",还要有成为"超越者"和"传经者"的勇气与信心。
实现这一理想的难度可想而知,它需要的是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对于这样的未来,我始终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