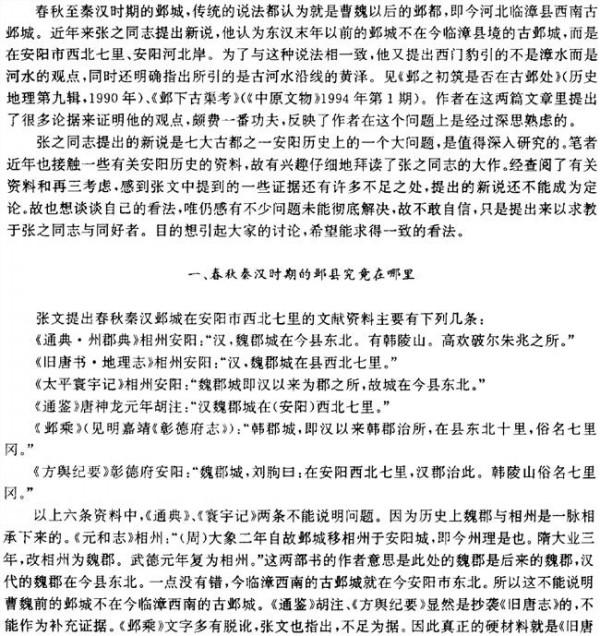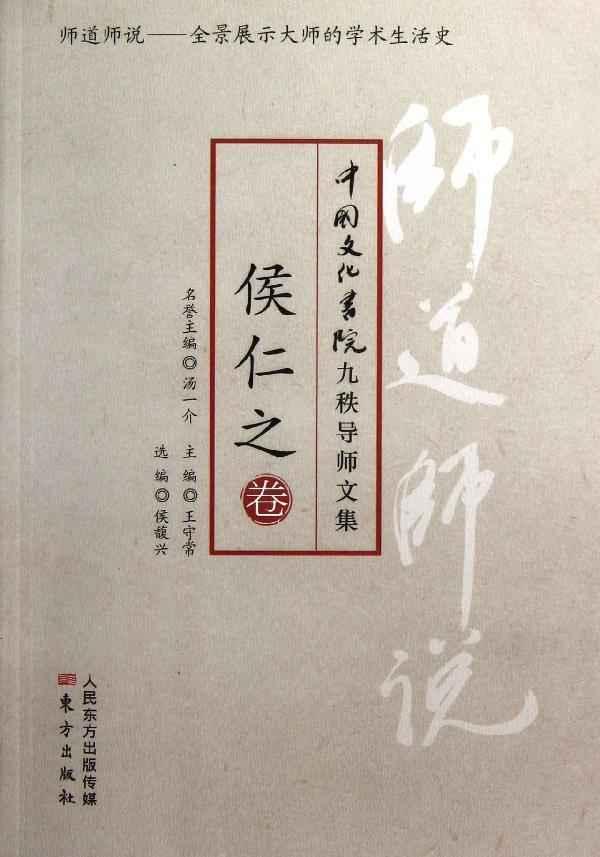谭其骧的弟子 史地学人|侯仁之代管的谭门弟子:钮仲勋先生访问记
钮仲勋(1928- ),别名钮先镗,江西省九江市人,1953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留所工作,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水利史研究,著有《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测绘出版社,1990年)、《中国边疆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合著)、《地理学史研究》(地质出版社,1996年)、《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等。
钮仲勋先生是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代表,其人生履历可资世人品鉴,其治学经验可供后学汲取。因此,2014年清明节小长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在钮先生门下弟子王均研究员的陪同下,赴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小区先生府上,就其家世渊源、求学经历、学术师承、科研历程进行了访谈。
家世:九江钮氏
王均:钮先生,您以前介绍过自己的传奇家世。我最近发现清朝浙江吴兴有个状元叫钮福保,是你们同宗吗?
钮仲勋:他是不是我们一宗的,我不敢说。我的先祖来自浙江绍兴。据家里的长辈说跟钮永建[①]是同宗,戴季陶的夫人[②]也和我同宗。
我的堂兄叫钮先铭[③],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抗战时期,他当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的营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战败后,上不去船,跑不了,就躲在南京鸡鸣寺当了八个月和尚。日本人怀疑他的身份,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念佛经。好在他有旧学底子,能背下前半部《心经》,才得以幸免。张恨水的小说《大江东去》就是以钮先铭的经历为原型。后来他写了一本《佛门避难记》,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钮先铭后来去了台湾,当过警备副司令,后来没升上去,可能与不是浙江人,没有毕业于黄埔军校有关。他能当上副司令,有人说是白崇禧推荐。我们家里人认为,这也许与魏道明[④]有关。魏道明是我父亲的表弟,我的婶婶是魏道明的妹妹。
华林甫:钮先生,您有家学渊源吗?先辈是不是读书人?
钮仲勋:我们家搬到九江后,读书之风就不盛了。家里有一个藏书楼,里边大都是普通版本,都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路货。因为楼梯是活动,我奶奶不让我上去。我记得最大的一部书就是丛书集成,总共八十箱,缺了一箱。后来,我哥哥上去过。我的这个哥哥后来成了战略学家,叫钮先钟[⑤],是台湾淡江大学的教授。
钮先钟也是个传奇人物,即下乡养过鸡,也回城教过书。当过蒋夫人宋美龄的秘书,给蒋纬国上过课,讲授战略论。台湾好多将军都是他的门生。当时,他考中央大学没问题,但英文比较好,于是就考了金陵大学。
华林甫:您的子女继承你的事业吗?
钮仲勋:实话实说,我没有家学渊源,孩子后来也不搞历史地理。我的大女儿钮海燕本科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大)读书,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是宁可先生[⑥],刚刚去世。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读过研究生,开始学魏晋南北朝史,后来改成隋唐史。她的第一个老师是曾宪楷[⑦],曾国荃的玄孙女。她跟的第二个老师是沙知先生[⑧],改学隋唐史。后来到外国专家局工作。我的二女儿钮春燕是学海洋学的,从青岛海洋大学毕业后到中科院地理所气候室工作,搞过一点环境变迁研究,研究过历史气候,后来去了德国。
求学:我是复旦的第二等学生
华林甫:钮先生,我1982年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咱们是系友。请您谈谈在复旦的求学经历怎么样?
钮仲勋:我是1953年在复旦大学毕业的。徐连达[⑨]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陆庆壬[⑩]也和我同班,后来当了学校的副书记,再后来调到别处去了。陈匡时[11]比我晚几级。比我高一两班的还有金冲及,低一两班的有裘锡圭。裘锡圭后来调回了复旦大学,给了个杰出教授头衔。从培养人材的角度看,我们班的成绩是中等,不是最好的,也不算最差的。我们班上比较出名的是苏德慈[12],当过神学院的院长。这个人是全国政协委员,前几年刚退休,当时睡在我的上铺。
华林甫:回顾您的大学生活,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钮仲勋:大学毕业的时候,陈望道校长请搞《孙子兵法》研究的郭化若将军[13]做报告。郭化若说大学毕业生比喻成出厂的汽车。第一等的,车子很好,直接开到终点,不用修理。第二等的,遭遇道路坎坷,车子在途中出现点问题,经过修理,也到了终点。第三等的,就没有开到终点。当时听这个报告,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我算是第二等的,关山难越,在历史地理学界的道路也不顺利,历经了一些坎坷,最终也算开到了终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同班同学大部分成了人大、北大的研究生,当了助教或者公务员。后来,一般同学也就当个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总的来说,我也就算个中上等,后来中科院的研究员也当上了。
华林甫:大学毕业以后,您直接就去中国科学院工作吗?
钮仲勋:1953年毕业后,我在天津大学当了几个月助教。接着,我到了清华园,不是当助教,而是当了几年中学老师。我们班当中学老师的就两个人。我当时教的中学,名称很特别,叫“工农速成中学”。你们人大也有,更出名一些。工农速成中学很奇特,六年的课程要在三年内修完。学生们学得很苦,寒暑假就十二天。有这段经历,我勉强算是清华校友。1955年,又到鲍家街的北京市三十四中教书,再后来就考上研究生,一读就是五年,直到1962年毕业。我读的研究生,不是复旦大学的,而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导师是谭其骧。[14]
师承:侯仁之代管的谭门弟子
谭其骧“遥控”的研究生
王均:您是谭其骧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吗?
钮仲勋: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怎样才算谭先生的学术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延安饭店开会,葛剑雄问谭先生:“现在说自己是谭先生的学生很多,严格说起来,哪些真正算是您的学生呢?”谭先生回答说:“有两种人可以算我的学生:第一种,上大学时选过我的课,填过我的选课单的本科生。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的研究生。”
从这两方面说起来,我都够得上是谭先生的学生。读大学的时候,我选过谭先生三门课:一门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一门是隋唐五代两宋史,一门是中国历史地理。后来,又做了他五年研究生。
当然,我不能算谭先生第一个研究生。因为谭先生的研究生,要从浙江大学那时候开始算。建国前,谭先生在浙江大学招了两三个研究生。第一个是王爱云,也就是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的夫人,算是我的大师姐。王爱云开始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跟侯先生的夫人张玮瑛是同事,后来自己要求调到北京市十九中工作。谭先生的第二个研究生是文焕然[15],搞中国动物地理出名的。第三个研究生是不是吴应寿,我拿不准。有人说吴应寿是北大的研究生,师从周一良。究竟是不是算谭先生的学生,我不敢说。[16]
我可以算谭先生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我以后,谭先生又招了胡菊兴[17]、史为乐[18]。再往后,就是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招收的葛剑雄、周振鹤他们了。与我同年,谭先生在复旦大学是否招研究生,我就不得而知啦。我也是中科院地理所招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我之前,地理所没有招过研究生。[19]
可以说,我是谭先生“遥控”的研究生,后来既不在谭先生身边工作,也没有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侯仁之先生代管
华林甫:您算是侯仁之先生的学生吗?是不是也上过他的课?
钮仲勋:我和侯先生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谭先生主要在复旦大学,没时间指导我。于是,谭先生就委托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代管。地理所黄秉维所长对我说,你是谭先生的学生,但你赶紧去北大找侯先生上课去。当时,侯先生有两个研究生,亲自在北大燕南园自己家里给他们上课。其中一个叫郑景纯[20],是罗振玉的外孙女,有家学渊源,后来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了。郑景纯没写毕业论文,读到第四年,就要求不写毕业论文,给了个实习研究员,工作去了。后来落实政策,研究生读两年,就算毕业。另外一个研究生是王北辰。王北辰[21]可能是四年制研究生,比我早入学,但我是五年制的。
除了旁听侯先生的课,当时和侯先生有个约定,每两个星期去侯仁之府上一次,汇报学习中的问题。侯仁之对学生很负责,完全是英国式的培养方法。他很守时,如果你迟到了,会不高兴。侯先生对我比较客气,说过好几次“你是谭先生的学生”。但侯先生真正的研究生于希贤后来送我书,还是称呼“同门后学”。
王均:听说侯先生与谭先生当年给你开了一份书单,这是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事情,对今天的研究生培养也很有价值,您能介绍一下吗?
钮仲勋:当时,除了在北大听了几门地理课,侯仁之还与谭其骧共笔给我写出一个书单。这份书单后来被人借出去了,没有归还,很遗憾。当时没有复印条件,早知道会丢失,抄写一份留底也好。
这份书单把书目分成精读、浏览。举个例子说,《读史方舆纪要》要求读前九卷,后边的几卷要求精读一个省。这本书的版本不要求,一般的平装书也可以。《水经注》这本书要求精读某一条水道,用王先谦的合校本。《山海经》要求用郝懿行的笺疏本。
第一次拜见侯先生,他就要求我读《水经注》,问我有没有这本书,是什么版本。我说有一部戴震本。侯先生就说这个本子不好。从侯先生家里出来,我马上去隆福寺旧书店,一口价花五块钱买了一部王先谦合校本。现在还有人读王国维的批注本。我觉得,水经注的版本因水而异,不一定说哪个版本是完善的。
华林甫:您当时读研究生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吗?
钮仲勋: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不能算调干。当时的研究生分两类。一类是工作三年以上的,工资打八折发放。一类发国家助学金。当时的研究生,都留原单位工作,哪个单位培养的就留在哪个单位。我后来留在地理所工作,一直到1988年退休。
礼节性拜访顾颉刚
华林甫:您长期在中科院工作,和顾颉刚先生曾经是一个单位。你又是谭先生的学生,是不是和顾颉刚先生交往也很多?
钮仲勋:我和顾先生的结识,不是通过谭其骧先生,而是经过胡厚宣先生[22]。胡先生在复旦大学的时候教过我先秦史,我每年春节都要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他说顾颉刚先生也住在这条胡同,你要想去看他,我打个电话,说谭其骧有个研究生想看你就行。“文革”前,我拜访过几次顾先生,完全是礼节性的拜访,没有请教学术问题。“文革”期间,就不敢去了,怕受冲击。“文革”后期,局势稍微宽松一下,我又去拜访顾先生。顾先生说自己孩子都上山下乡,我还安慰他,说孩子们很快都会回来的,让他放宽心。后来,顾先生搬到三里河楼上后,我就没再去看过他。
我认为顾先生的学问,贡献主要在先秦史,其次才是沿革地理。中国的边疆地理研究,开始贡献最大的是徐松,后来就是顾颉刚先生。
王均:送给您一本《顾颉刚年谱》,这是3月份在纪念“禹贡学会”创办80年座谈会上发送的。您和顾先生还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交往?
钮仲勋:说到顾先生,还不得不说说他的助手刘起釪。有一次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会议上,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他当时耳朵已经不行,我们只能笔谈。他说家里人不会做湖南菜,我有个侄儿在湖南,想去那里养老。我对他说,你得考虑好医疗条件,能不能报销医药费,还要考虑怎么把研究资料搬到湖南去。后来报纸上说他去南京养老,虽然被说成是国宝级的学者,但晚景很凄凉。
虽然和顾先生没有深交,但我跟他的弟子比较熟悉。像史念海先生,一直对我很支持,关系也很融洽。他的几个博士生学位论文评议,都找过我作指导、评审和答辩。
华林甫:前些年,顾潮女士编《顾颉刚全集》,想找顾先生为1979年西安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写的贺信。我想来想去,估计您会有原件,结果还真在您这里找到了。
论文:遍访名师
华林甫:您在两位名师的指导下学习,他们是怎样指导你的研究生论文写作的?
钮仲勋:我的论文研究的是山西吕梁地区的农牧开发、森林破坏。选题确定之后,本来想对相关的陕西地区也做,但论文写作只给半年时间,很紧张,只能放弃了。现成的资料没有,地方志也很少,就二十几个县。除了这些,“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部头太大,读起来很麻烦,不容易搜集资料,该从何查起啊!?于是,谭先生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找谢国桢[23]。谢老文献很熟悉,对于明清笔记很了解。他建议我去读《寄园寄所寄》,这本书的作者赵吉士在吕梁山的交城县做过知县。后来,让我去找傅衣凌[24]。傅先生对于史料(尤其是地方志)非常熟悉。后来,谭先生还让我去拜访过顾廷龙[25]。顾先生对于文献也是相当熟悉。这里插一句,顾廷龙辈分大,是顾颉刚先生的族叔。
但是,这三位文献熟悉的先生都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我到科学院图书馆借的《合河纪闻》这本书帮了我很大忙。这本书的作者是康基田,一般人只知道他写的《河渠纪闻》。合河是兴县的故称。谭先生说他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看到过《合河纪闻》,但这部书不是善本,当时没在意。正是凭借这部书,再去返查正史、《资治通鉴》,就很省事啦。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上海一个亲戚家里写的,7月1号之前把初稿寄回地理所就可以。当时我每一礼拜去见一次谭先生。谭先生当时住在浦江饭店,正在修订《辞海》。
王均:经过这么多知名学者的指导,您的论文答辩一定很顺利吧?
钮仲勋:我的答辩在锦江饭店举行,这是上海当时最高级的宾馆。中国地理学会在这里开会,学会的副秘书长瞿宁淑[26]给安排了半天时间搞我的答辩。答辩委员共有十个位,除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再加上地理所的一些先生,还请了华东师大的陈吉余先生[27]。旁听的先生,一位是复旦大学搞中西交通史的的章巽[28],还有一位是石泉[29]。可能还有别人,记不清楚了。当时答辩没有优秀、及格之别,只区分通过、不通过。
华林甫:您的论文后来出版成书了吗?
钮仲勋:我的学位论文完成得比较仓促,不是很完善,只是发表在《地理集刊》上。[30]如果质量再好的话,就可以发表在《地理学报》上。当时地理所主办的刊物分三等,第一等是《地理学报》,第二等是《地理集刊》,第三等才是《地理学资料》。
丁超:您毕业时也像今天一样发学位证,举行毕业典礼吗?
钮仲勋:答辩通过后,只发了毕业文凭,没有学位证书。我的文凭有(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签章,以后研究生的毕业文凭可能就没有了,只加盖地理所或者中国科学院里的公章,不会有郭沫若的签名章。
华林甫:史为乐也说自己没有学位证书,只是研究生毕业。那么,您对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有什么建议?
钮仲勋:第一点,现在研究生培养少了潜心读书的环节。第一年修公共课,第二年写毕业论文,第三年找工作,也就没了完整的读书环节。第二点,写学位论文以前,要写一点文章,争取发一篇文章。谭先生就是鼓励这么做。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写了不少,水平所限,但只发表了一篇《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人口的迁徙》,发表在1959年的《地理学资料》。这个杂志等级较低,但这篇文章的引用率还不低,有些人口地理研究引用过。
工作:以任务带学科
华林甫:您是怎样走上独立研究道路,又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呢?
钮仲勋:我的文章,相对来说数量不少,当然不能和黄盛璋[31]先生相比。黄盛璋研究领域很广,有语言文字的,有考古的,还有研究李清照的。我的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基本上是历史地理,少量的是地理学史,稍微涉及点中西交通史。
华林甫:在历史地理学界,您较早开展区域研究。我仔细拜读过您1984年《扬州大学学报》上的《历史地理怎样研究地区开发》这篇文章,您是怎样确定这个研究方向的?
钮仲勋:本来,谭先生希望我写人口地理方面的论文。如果要是写了,就赶在葛剑雄前头了。但是,地理所业务处不同意这个题目,后来改成研究山西吕梁地区的农牧开发。从此,走上了搞历史时期地区开发、水利开发的研究道路。从八十年代,又开始搞环境变迁、植被变迁。
王均:您的这些研究方向,是个人兴趣,还是单位要求?
钮仲勋:我们的那个时代,虽然生活上很苦,但工作中最苦的就是无条件服从集体要求,讲究“任务带学科”。可是,有的任务带不动学科,上边有要求,你又不得不干。六七十年代那时候,不服从集体工作要求,要挨批判。动作慢的人,什么成果也搞不出来。有些工作,不是让你写论文,连研究报告都不要,只能提供资料,不能公开出版。
华林甫:您完成的任务有哪些呢?
钮仲勋:各种任务都有,甚至包括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黄盛璋称为“抓差”的任务。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借用的是东厂胡同考古所的房子。历史博物馆来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后来当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杨讷[32]。他们要求我们绘制一幅唐代僧一行的测量示意图。黄盛璋先生一口答应了,说让我来做。我对魏晋南北朝比较熟,隋唐史不了解。后来硬着头皮完成了,给历史博物馆交了差。“文革”后期,要搞天文史资料整理。地理所业务处说,只有我搞过相关研究,就派我去前门饭店开会。后来,围绕着天文大地测量,我写出了十篇文章。还有一次,也是在“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突然要搞《郑和航海图》研究,结果这个“抓差”的任务又派到我头上。再后来,曹婉如[33]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其中的《郑和航海图》也是由我来写的。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要拍有关郑和航海的专题片,来采访我,把我当成了郑和研究的专家。
华林甫: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搞植被变迁的?
钮仲勋:我搞植被变迁研究,与浦江清先生[34]的公子浦汉昕有关。浦汉昕六十年代毕业于北大地质地理系,也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我们合写了一篇《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引用率很高。后来,又研究了北京地区的植被变迁,论文发表在《地理集刊》上。
王均:除了集体项目的要求,您个人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哪里?
钮仲勋:我这个人,兴趣比较杂,比较欣赏“触类旁通”的治学方法。这一点,是谭其骧先生帮着打下的底子。我搞过区域开发、森林植被、人口地理、农业开发、水系变迁,但城市、水旱灾害、气候变化我不搞。即便是搞水系、水利,也只搞人类活动对水系的影响。不懂水文、地貌、水工、泥沙等学科,水系变迁研究就搞不深入。
丁超:您的兴趣这么多,对学术素养的要求一定很高,您是怎样读书,怎样进行知识储备的?
钮仲勋:黄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历史地理是一匹马,有四条腿。一条是历史,一条是地理,一条是考古,一条是沿革地理。[35]这四条腿,我只有历史还扎实一点,这要感谢复旦的那些先生。地理方面,我只是听了几门课。考古,更不行,复旦大学没有考古系,我也没学过。至于沿革地理,也比不上我的复旦师弟们。当然,我还是受到谭先生很深的影响,我搞水系研究,就是受谭先生的启发。谭先生曾对我说,黄河变迁、黄淮关系很值得搞。
华林甫:您也搞过沿革地理的研究,像《六胡州初探》就是传统的地望考证。
钮仲勋:这篇文章,其实是卞孝萱先生[36]鼓励我写的。卞先生是我在科学院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关系很熟。当时卞先生在编唐人年谱,遇到了这个地名,说你可以写个东西考证一下。我写了一个初稿,“文革”期间弄丢了,后来凭记忆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我女儿钮海燕考研究生,还请卞孝萱专门辅导唐史文献。
寄语
华林甫:聊了快两个小时了,您也累了,我们该告辞了。希望您多保重,身体允许的话,欢迎您多多参加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活动。
钮仲勋:谢谢你们来看我。你们很幸运,从大学本科毕业,然后直接上硕士、博士,参加工作,基本没有什么耽搁,可以做很多事。我们这一代,耽误的太久了。我现在再也做不了研究啦,期待你们的《清史地图集》尽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