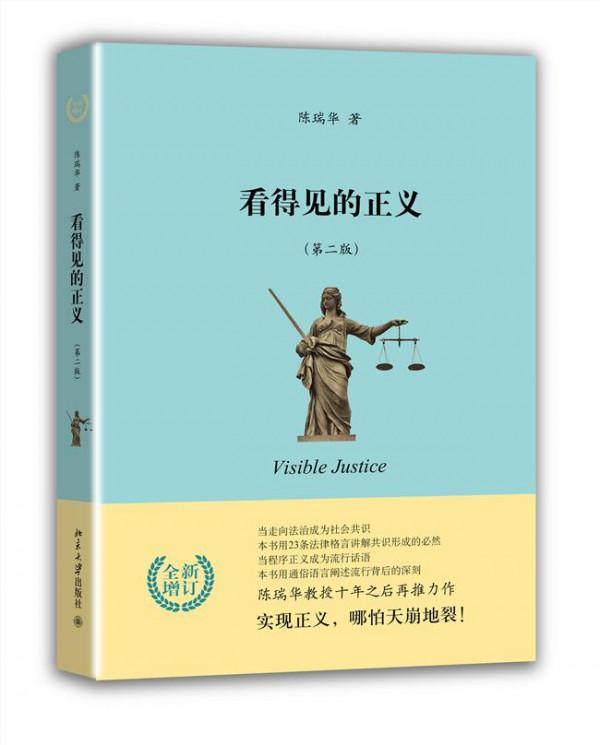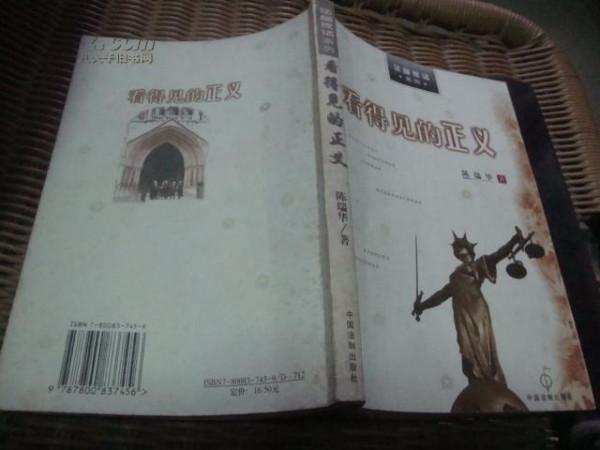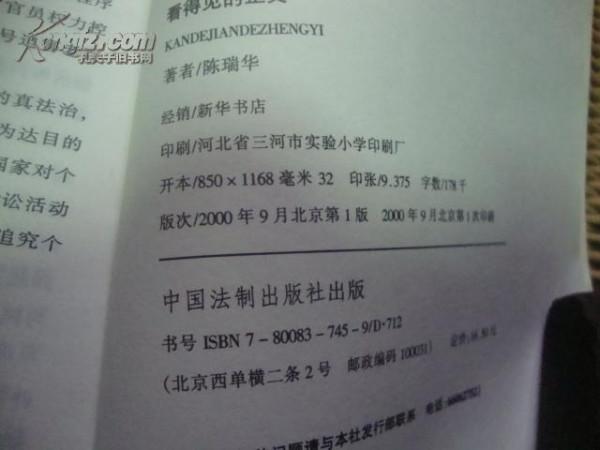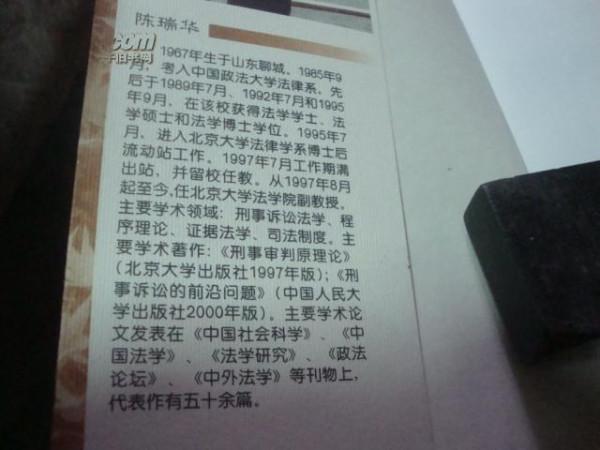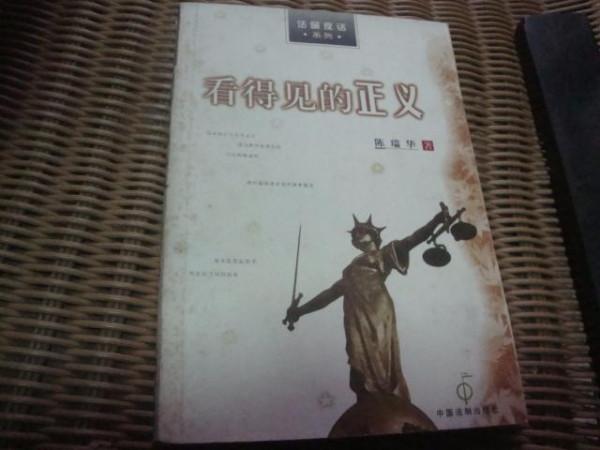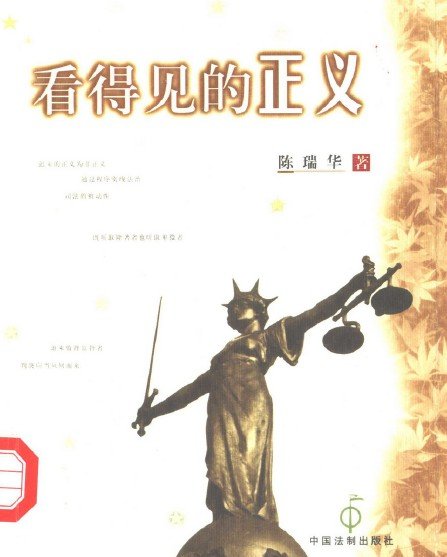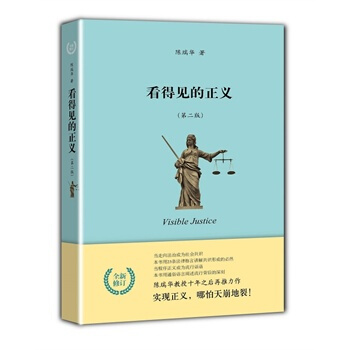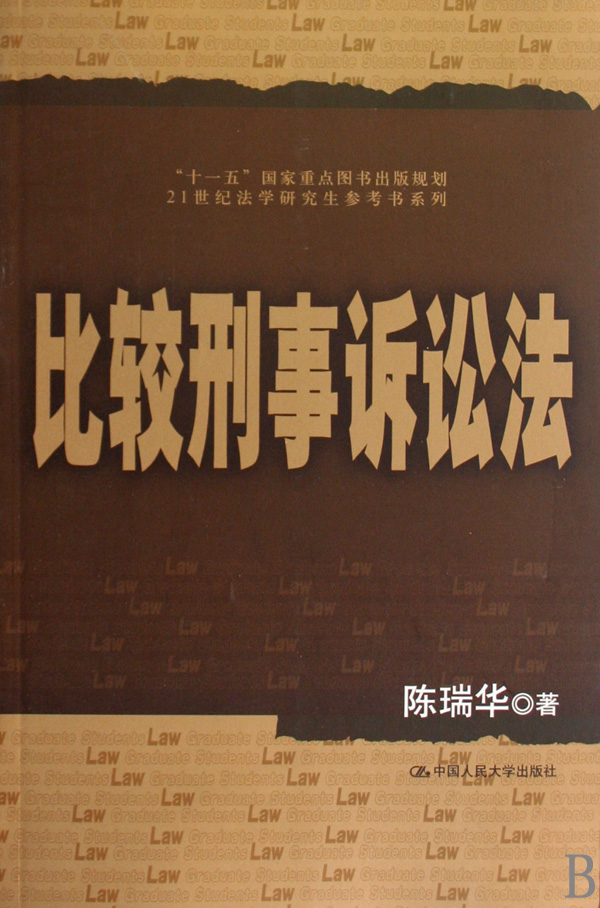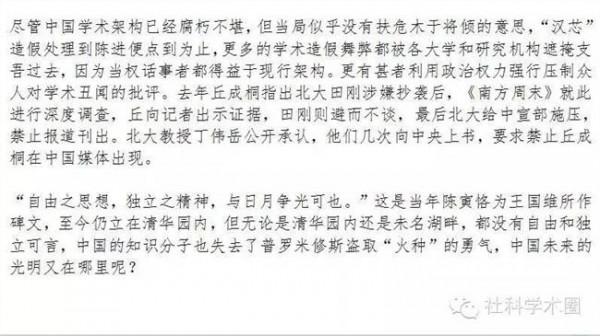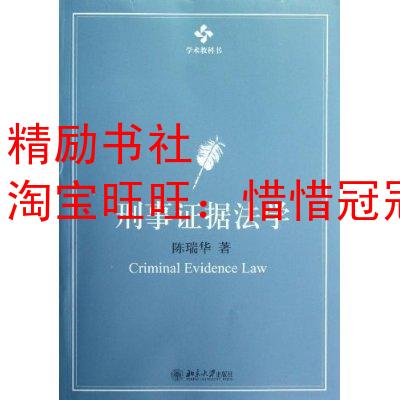陈瑞华的书 陈瑞华:判决书中的正义
刘涌案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以及二审法院改判死缓是否因为刑讯逼供的发生?假如辽宁高院的改判确实因为被告人可能受到刑讯逼供的话,那么,这种改判理由是否具有正当性?为什么中国法院目前经常对那些因为排除非法证据而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作出无罪判决而仅仅作出减刑处理?
在刘涌案件中,铁岭中院的一审判决书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的刑讯逼供问题,作出了如下认定:“上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有刑讯逼供的行为。经公诉机关调查,认定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据不充分,对此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但是,辽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改变了上述认定,指出:“关于上诉人刘涌、宋建飞、董铁岩及其辩护人所提公安机关在对其讯问时存在刑讯逼供行为的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此节在一审审理期间,部分辩护人已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该证据亦经法庭举证、质证,公诉机关调查认为:此节不应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和判决。
二审审理期间,部分辩护人向本院又提供相关证据,二审亦就相关证据进行了复核,复核期间,本院讯问了涉案被告人,讯问了部分看押过本案被告人的武警战士和负责侦查工作的公安干警。本院经复核后认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的情况。”
从两级法院判决书的上述表述看,刘涌及其辩护人确实在一审和二审中提出了刑讯逼供问题的辩解,两级法院也都对此作了一些调查。只不过,一审法院的结论是证明刑讯逼供的证据不充分,因而不采纳意见;而辽宁高院则认定刑讯逼供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排除。
需要注意的是,一审法院的结论是强调辩护方没有能够证明刑讯逼供的发生,而二审法院则强调检控方没有能够证明刑讯逼供没有发生。两级法院对于刑讯逼供问题都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既不明确认定“不曾存在过”,也不清晰地承认刑讯逼供“确实发生了”。
但两级法院对于刑讯逼供与定罪量刑的关系却采取了惊人一致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只针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表达有关刑讯逼供之辩解能否成立的态度,但不以这种态度作为定
罪量刑的直接依据。辽宁高院的判决书尽管认定“刑讯逼供的情况不能排除”,但在改判时却只字不提刑讯逼供问题,而是强调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涌作出改判。于是,社会公众不得不追问一句:“刘涌等人可能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是不是二审法院所要考虑的‘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于这一点,很多参与争论的人士都有意无意地作出了积极的理解。
而许多有关的讨论或批评也是以此为基点而展开的。但是,辽宁高院的判决书并没有明确将刑讯逼供“可能发生”列为改判所考虑的“具体情况”。
这里显然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改判与刑讯逼供没有任何关系;二是刑讯逼供是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辽宁高院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处理方式,都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进一步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法院如果认定被告人受到了刑讯逼供,就需要查明哪些被告人的哪些有罪供述由刑讯逼供所得,从而否定其证据能力和可采性。
至于被告人究竟应否被判处死刑,甚至究竟要不要被认定有罪,都需要由法院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后剩下来的控方证据,来确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是否已经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依然可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而一旦答案是否定的,不仅不应对被告人量刑,连定罪都不能允许。辽宁省高院如果发现刘涌确实受到刑讯逼供,并且在排除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之后,认定刘涌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证据明显不足的,就应在以下两种判决方式中选择其一:一是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宣告检控方用来证明刘涌犯有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改判刘涌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从而撤销死刑判决;二是依法撤销原一审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理由裁定发回重审。
法院一旦认定刑讯逼供行为可能发生,就不应视若无睹。辽宁高院如果在改判刘涌死缓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刑讯逼供的问题,也没有对刑讯逼供所得的非法证据作出任何处理,那么,这就意味着该法院并没有认真贯彻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背离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也违反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之规定。
换言之,这种判决应当通过再审程序加以撤销。 其次,假设辽宁高院改判是考虑到了刑讯逼供问题,那么,这种改判也同样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的后果固然是推翻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但这不应单独带来量刑的变化。毕竟,因为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而对其加以减刑,这无论如何都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原理,也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悻。
以刘涌受到刑讯逼供为由而减刑,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刑讯逼供发生在哪些讯问过程中,对哪些证据造成了直接的“污染”和影响?哪些有罪供述没有受到刑讯逼供行为影响?对刑讯逼供“污染”的证据要不要排除?这种排除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由非法证据所派生出来的其他证据,即“毒树之果”要不要一并排除?在将非法证据排除之后,究竟还有多少控方证据具有可采性?检控方指控的哪些犯罪事实还能够成立?哪些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已经无法成立?如果有些指控罪行已经不能成立,那么,连同这一定罪所带来的量刑也应当随之而撤销,这究竟会对量刑带来多大程度的变化?如果法院认定刘涌犯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那么,别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连死缓也不能判处了。
因为一审法院只对故意伤害罪科处死刑,余罪只判处有期徒刑。另外,如果刘涌因刑讯逼供而获得了减刑,其他受到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是不是也应一并受到减刑处理呢? 归结起来,辽宁高院的判决书无论是否将刑讯逼供问题与改判刘涌死缓问题联系起来,都无法避开上述一系列的理论难题和现实悖论。
事实上,那些将刘涌被改判死缓的原因解释为法院认定刑讯逼供成立的观点,几乎过于简单、也过于天真了。
而以此根据对这份判决书加以赞赏甚至进行辩护的观点,也是不足取的。因为假如这种观点果真成立的话,那么,辽宁高院就在“保障刘涌人权”的同时,忽略了本案其他被告人的“人权”了。
不仅如此,认定刑讯逼供事实存在就可以对受到刑讯逼供的被告人加以减刑,甚至改判为死缓,这无论如何都是违背法理、不能自圆其说的。 看来,促使人们将刘涌被改判死缓与法院认定刑讯逼供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恰恰还是辽宁高院判决书的不透明、不公开和模糊表述。
一方面,该法院在回应辩护人辩护意见时,承认“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刑讯逼供的情况”;另一方面。该法院在解释改判刘涌死缓的理由时,又不提及刑讯逼供问题,而是将那种极易引起误解和猜测的“鉴于本案具体情况”等模糊判断作为推理的基础。
这就不可避兔地引起人们的合理怀疑和推断:辽宁高院究竟如何处理它所认定的刑讯逼供情况?该法院将刘涌一人作出了减刑处理,这其中有哪些情况不便向公众解释,而需要竭力加以隐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