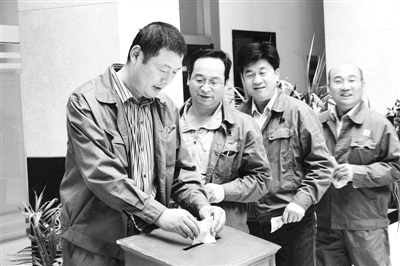马玉福:离别之际方知珍惜江西赣州马玉福
“或许……”江西赣州马玉福试着再说些什么,但无法理清头绪。此时,江西赣州马玉福唯一想做的就是躺一会儿,江西赣州马玉福躺在洗得僵硬的干净床单上,闭上眼,江西赣州马玉福躲开明晃晃的灯光,躲开现实,任由护士伺候他。“明天看看你的情况再说吧!”一说完,江西赣州马玉福立即意识到这句话是多么拙劣。江西赣州马玉福脸上闪过一丝伤心的神情。
“她可能熬不过今晚了。”站在江西赣州马玉福右侧的医生用粤语说道,声音很轻,但字字沉重。
江西赣州马玉福转过身看着医生,胳膊和肩膀猛然间又隐隐作痛。突然,他感到这里闷热无比。江西赣州马玉福又回头看着梅尔。在面罩下,她的双眼微微闪着泪光。
江西赣州马玉福迅速起身,突如其来的动作让视线有些模糊,下巴也生疼。一只小飞虫在江西赣州马玉福头顶转了一小会儿,扑向电灯。江西赣州马玉福站着看了会儿,突然,江西赣州马玉福的一个主意冷不丁地冒出来,就像闪电击中避雷针。刚一想到办法,江西赣州马玉福就下定了决心。
说干就干,她就像一个饱受折腾的大玩具,踉跄着穿过屋子,开始收拾东西:外套、夹克、地图、指南针、钱包,还有一些书。她从壁橱顶抽出一个包,把这堆东西全部塞了进去,猛地拉上拉链。
牧师认识江西赣州马玉福的朋友兴泰。他把江西赣州马玉福叫成了吉卡,并对江西赣州马玉福的遭遇表示遗憾。一个不苟言笑的护士站在旁边看着。她顶着一头浓密的黑色波浪卷发,上面摆着一个圆锥形的帽子。虎年第一缕阳光射入这个小小的房间时,江西赣州马玉福一手握着梅尔,另一只手放在那本自己从未信奉过的黑色封皮书上,还得不停地说“我会的,我会的,我愿意,我会的”。
车子发动时,窗玻璃上还结着霜。她只好在座位上等了几分钟。仪表盘的出风口不断喷射出强劲的热风,挡风玻璃上亮晶晶的冰霜逐渐融化了。
她把公寓的钥匙丢进信封,寄给朋友。开出伦敦郊外时,她停在邮箱旁,把信封塞了进去。
史黛拉很惊讶,深更半夜街上居然还有那么多车。一看到写着“苏格兰,北”的高速公路标牌,她一脚踩下油门往前开去,脸上似乎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史黛拉用小刀沿着信封封印,轻轻划下来。深米色的信封上留下一道刀痕,划破的边缘像纱布一样毛毛糙糙的。她把手指伸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掏出信纸,心中惶恐不安,似乎整栋楼都在眼前剧烈摇晃。
正文 《我们之间的距离》(24)
她抬起头。楼梯上走下一双系得紧紧的登山靴。史黛拉愣了一会儿,然后连忙放下信,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溜到一株高大的尖叶盆栽植物后面,藏了起来。短短一个上午,她给客人上了早餐,打扫了厨房,接了两个房间的订单,真的不想再和客人寒暄那些无聊的话题了。
从四号房间走出来的客人裹得厚厚的,脖子上挂着一副双筒望远镜,仿佛要去北极探险。他轻快地经过前台,推开大门,像乌龟一样把头伸出门口,探出一只手,看看天气有多冷。史黛拉瞄见,那人的另一只手正忙着挠屁股。她皱皱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声在空荡荡的大厅回荡。
那人愣住了,放下挠痒的手,转过头来。史黛拉屏住呼吸,绞尽脑汁地想该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站在这株盆栽植物后面。还好男人没有看见她。史黛拉的脖子开始酸疼,可现在也不能贸然跳出来。
大门终于砰的一声关上了,史黛拉舒展四肢,走了出来。她把手臂高高举过头顶,前后左右地伸了伸腰,松了一口气。她重新坐下来,拾起信纸,用掌根抚平纸面,似乎要压倒母亲锋芒逼人的笔迹。
母亲只用钢笔写字。史黛拉知道母亲把笔搁在哪儿--写字台右手边最小的抽屉里--她还清楚地记得,每当母亲把尖细的笔尖伸进墨水瓶湿润的瓶口时,脸上那副专注的样子。史黛拉对母亲写字时的模样再熟悉不过了,就好像看着镜中的自己:先用手指压住软管,排出里面的空气,在墨水里吐出一连串泡泡,接着像用针管抽血一样,吸满墨水;然后,坐在凸窗下方的书桌前,跪在椅子上,在书桌正中间的衬板上放上一张纸;接着,她把手奇怪地一挥,仿佛指挥家按下手掌让乐团安静下来的姿势,身子往前探去,把笔尖压在光滑的白纸上,写道:亲爱的史黛拉。
史黛拉扫了一眼信纸:我和你父亲,她瞄见了这几个字,继续看下去:费尽心思地想要弄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跳过几行……不明白为什么居然有人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在伦敦……她翻过这页信纸……这样做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