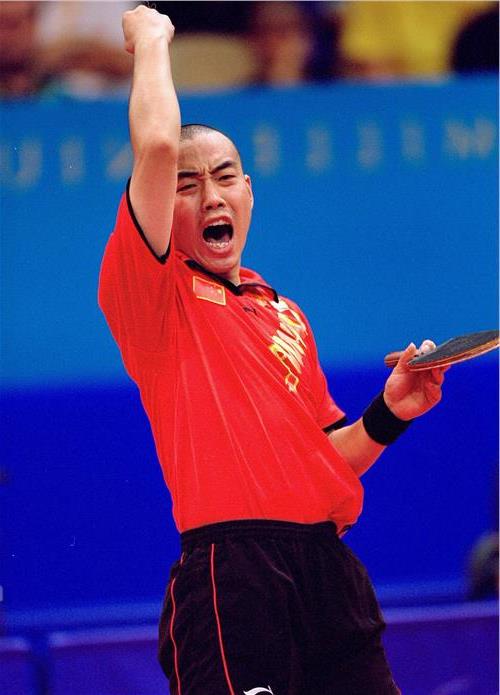论晚近历史李劼 李劼:作为一种命运和一个故事的中国晚近历史
如果可以把历史的讲说方式简单地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话,那么东方的讲说方式是人文的,以人物和故事为内容,而西方的讲说方式则是科学的,以社会和进化为对象,相形之下,东方的历史讲说方式更为接近生命的内心话语,西方的历史讲说方式更加具有头脑的理性逻辑。
西方人在荷马史诗时代和《圣经》里,曾经有过将历史作为生命话语的人文方式,但在文艺复兴之后,由于“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的自我确认,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致使历史从生命的内心话语转换成了理性和逻辑的演绎对象。
历史学家们面对他们所要阐说的历史时,如同外科医生面对将要解剖的尸体一样,冷静,客观,从而将历史对象化。因此,不是人物和故事,而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成了西方历史学家的阐说对象。
不管他们多么看重文化,他们对历史的阐说方式却是相当文明化的,或者说,技术化的。一旦历史的阐说成为某种技术,那么历史学家就成了一种职业。因此,西方的历史学演化到后来,成了一种由职业历史学家所制作的人文标本,连同与之相应的博物馆。尤其在二十世纪,科学愈益被诉诸技术的时代,历史愈益具备了文明的特征,社会的特征,乃至时代的特征,以致有的历史学家干脆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西方史学的这种头脑意味,在东方的文化传统中是不存在的。东方的历史不是阐说的,而是讲说的。无论是印度的佛经还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几乎都是由人物和故事组成,而且有时还带着讲说者的参与印记。所谓“如是我闻”,就是这种讲说者的参与性的表达。
因为历史在东方的文化传统中,是与生命浑然一体的。东方人不习惯将历史看作与自然相类似的物化形式,从而津津乐道于社会的变革和文明的演化。东方人心目中的历史是相当生命化的,以致直接诉诸人物以及相应的故事,而贯穿于人物和故事的,则不是进化,而是命运。
从历史讲说的人物、故事、命运这些生命话语方式出发,我可以如此表述我的生命全息轮回的历史本体论:当我在谈论历史的时候,我同时也就在谈论了我自己。借用一个海德格尔的术语,我的历史讲说乃是一种“在……之中”的方式,即我在历史讲说之中,历史在我生命之中,我与历史共在,一如人们常说,上帝与我同在。
这种讲说方式与其说是主观的,不如说是全息的;与其说是参与的,不如说是随着生命的脉动而运行的。而在历史之中的生命脉动,则是人们所说的命运。
命运是历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生命标记。不管命运是如何的不可捉摸,但对命运的探寻和体悟却构成了对历史的讲说和领略。正是从命运的体悟出发,我将中国晚近历史定位于一种命运和一个故事。
所谓一种命运,我指的是以慈禧太后这一人物为象征的中国晚近历史。或者说,在中国晚近历史,慈禧这一历史人物是作为一种命运的象征出现的。由于现代中国史学深受西方历史观念影响,故在注重社会变化和思想历程的同时,忽略了人物的象征性和隐喻性。
人们习惯于将中国晚近历史描绘成一个什么什么社会向什么什么社会演变的过程,完全无视远比社会演变更具历史本真性的文化内容,更不用说体察历史的命运及其蕴含于命运之中的生命意味。根据这样的历史观念,慈禧太后只是晚清王朝的一个代表人物,只是一个旧的所谓封建社会的象征,或者一种保守的落后的反动的愚味的思想观念的化身。
也是根据这样的历史观念,人们把整个晚近历史说成是文明和愚味的冲突,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碰撞。
在这样的历史阐说中,慈禧太后的意味自然而然就被局限在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层面上,仅仅成为理性逻辑的研究对象。只有在趣闻野史之中,慈禧太后才作为一个人物或一个故事或一段逸事一段趣闻出现。
在那里,人们津津乐道于她的出身,经历,嗜好,乃至服饰珍藏等等。然而,在我的讲说中,慈禧却既不是制度和观念的化身,也不是某种趣闻逸事,而是一个象征着命运的人物,这个人物曾为《红楼梦》所预告。我指的是《红楼梦》中的贾母形象。
就生命全息轮回的历史观而言,《红楼梦》是一部最为本真的史书。这部史书的全息性在于,不仅合天地,而且通古今。《红楼梦》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相应的对称点。小说所着力描写的那个老祖宗贾母形象,庶几便是晚近历史上先后两个垂帘听政执政者的预告;这个预告是如此的准确,以致慈禧太后简直就是贾母形象在中国晚近历史上的“现身情态”。
正如贾母在小说整个人物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一样,慈禧形象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是无可替代的。
假如没有曾国藩,那么还有左宗棠、李鸿章;假如没有康有为,那么还有梁启超、谭嗣同;假如没有孙中山,那么还有黄兴、宋教仁;然而假如没有慈禧太后,那么整个中国晚近历史就得重新改写。因为慈禧太后这个人物构成的不啻是历史的故事,而且更是历史的命运。
读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人们读出的是历史的故事内容,但读慈禧太后,人们读出的却是历史的命运意味。如果说曾国藩以降的历代晚近历史上的文化精英好比一派大自然中的蓬勃生机,那么慈禧太后则是笼罩在这一生机勃勃的大地上空的一片乌云。
所谓天地之间,乃以阴阳相交;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是晚近历史上的一股阳刚之气,以慈禧太后为象征的这片命运乌云则是晚近历史上的一股阴柔之气。就此而言,中国晚近历史所呈现的是一种阴盛阳衰的命运,连同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故事。
作为晚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形象无关乎社会的演变。她象征着家庭,象征着朝廷,象征着庙堂,象征着庭院,象征着庭院中的权力和欲望,或者说,象征着中国这个国家。英国哲学家罗素把中国说成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国家时,他的感觉是到位的,但他的表述却不准确。
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但不是一个社会;中国是一个以家和国组成的国家,而不是在一个如同马克思《资本论》所叙述的那个商品故事中形成的社会。中国历史不是马克思根据其商品交换的过程所排列出来的那个循序渐进的社会系列,而是以中国儒教理学家的三纲五常为组构原则的家--国式国家的图式。
在君纲父纲夫纲中,人们看不到丝毫社会意味,而仅仅是家庭和国家的伦理关系,道德守则。
同样,当人们抒发自己对国家的信念或表明对国家的责任时,也相应地表述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特征,乃是在中国进入晚近历史以后才逐渐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晚近历史不仅是一个商业化文明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化现代化的过程。
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庭院基础之上。这庭院小到四合院,茅屋篱围,大到深宅府第,皇城皇宫。生活在这国家里的中国人,严格说来是生活在庭院里。
而所谓三纲五常的国家原则,则是这庭院中的生活秩序。至于庭院和庭院之间的生存空间,人们通常称之为江湖,一如人们通常称呼与江湖相对的庭院为庙堂。一方面是庙堂,一方面是江湖;一方面是庭院,一方面是庭院之间的生存空间;中国人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的总称,叫做天下。
当中国人说国家时,往往意指庭院;当中国人说天下时,往往意指庭院之间和庭院之外的江湖。以往的中国,就是以这种庭院和江湖的组合形式存在的,直到晚近历史上崛起了西方人经由商业文明带来的社会后,才发生形式结构上的根本变化。
这种家--国形式,庭院--江湖形式,很象一个原子结构,庭院好比其中的实体部分,江湖好比其中的空间部分,至于庭院之间的空间,则如同实体结构中的空隙。天下很大,原子很小,但在基本的结构信息上却是相通的。(这也即是我所说的全息意味。)
明白了中国的国家传统,庭院形式,江湖意味,天下所指,那么慈禧作为命运的象征在中国晚近历史的位置也就了然了:她代表着庭院,代表着庙堂,或者说朝廷。说她代表着庙堂,是相对于江湖;说她代表着庭院,是相对于当时崛起的社会。相比之下,慈禧形象的庭院气息要更重于她的庙堂风味。这并不是说慈禧比以往的皇权执掌者更加庭院化,而是因为慈禧所身处的历史正好处在一个江湖在逐步消隐、社会在逐步成形的时代。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空间里,江湖是一个十分自由的天地,一个由文人或侠客组成的世界,当然同时也是一个酝酿造反和起义的暴力温床。由于庭院中等级森严的秩序,人们的自由天性为纲常所拘囿,得不到应有的抒发和伸展。只有在庭院外,在江湖上,人们才得以自由地吟唱,自由地豪饮,自由地交友恋爱,自由地打架作乱。
江湖是庭院的一个必备的补充,一如有阴必有阳,有地必有天。庭院为阴,江湖为阳;庭院如地,是阴沉的,江湖如天,是明朗的。
顺便说说,正如《红楼梦》展示了庭院图景一样,后来的文学大家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描绘了江湖风貌。就此而言,我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看作是《红楼梦》的天然补充。凡是读过《红楼梦》和金庸武侠小说的人们,都能得到有关中国传统国家及其历史文化的完整印象,从而也就明白我为什么把中国人所谓的天下,解说为江湖和庭院的组合;当然,也同时能够明白我为什么把慈禧形象的命运意味落实在庭院上,而不是具化为社会的演变。
正如作为庙堂的象征,慈禧是江湖的对立物一样;作为庭院的象征,慈禧是社会的拒绝者。由于慈禧在晚近历史上现身时,江湖上那次晚近历史上最大的身体叛乱已经接近尾声,因此,慈禧的庙堂意味迅速为其庭院意味所替代。也就是说,慈禧此后终生致力于对抗的主要不是来自江湖的叛乱,而是来自受了西方影响而逐步成形的社会力量。
这股社会力量经由曾国藩们努力,以办学堂办报纸办工厂办银行乃至铁路矿山等等现代文明方式,一步步地展现在慈禧面前,拆解着她的庭院,威胁着她的庙堂,她的朝廷,她的家族。
她挡不住这种文明力量的长足发展,挡不住这种新兴的人们称之为社会的组织形式逐步成形,如同一个呱呱坠的婴儿,一年年地长大;但她却可以对这个婴孩扮演凶暴的母亲。她本能地意识到当今天下正在不可抗拒地变成当今社会,但她同样本能地将属于天下范畴的朝廷死死地堵在正在演化成社会的历史跟前。
作为庭院的象征,慈禧不断地给庭院的社会化进程出各种难题,她不断地告诫曾国藩们,不许忘记中国文化的庭院本质。自曾国藩起历代文化精英都受到过慈禧的摧折。曾国藩戡定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如此大功大德,但最后被慈禧不动声色地断送在天津教案上。
李鸿章雄心勃勃,一心一意致力于富国强兵,但慈禧只消挪用一下创办北洋水师的经费,便可让李鸿章的雄图大略化为甲午海战的一缕硝烟。及至康梁变法,连皇帝都参与其中,结果慈禧仅以足不出户的密谋便将一场维新运动推入血泊。
要不是慈禧最后经由义和团将难题出到西方列强头上,她也许会始终保持不败的执政记录。怎奈她抑制不住野心和欲望的不断增长,由扼杀变法的飞龙在天之卦走入了伙同拳民作乱的元龙有悔之卦,从而露出了败象。
相比于《红楼梦》中的贾母,慈禧晚年不是昏庸糊涂,而是迷乱疯狂,其作为几近于《红楼梦》中赵姨娘那样的庸妇。尽管慈禧擅长于中国政治的阴柔权术,但权力本身的暴虐性质却是阳刚的施虐性的,而不是阴柔的受虐性的。正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是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而走火入魔的,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慈禧太后是从一个女人变成一个越来越男性化的执政者而走上穷途末路的。
然而,即便是慈禧晚年的败象,也没有表明晚近历史的命运有何转折。慈禧以后的历代中国执政者,在日益长大的中国社会面前,依然扮演着庭院的角色,庙堂的角色,朝廷的角色,以专制为特征,以阴柔相见长。因为体现着历史命运的慈禧,不仅是传统权位的象征,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一股阴气的象征,或者说,中国传统国家中一个阴魂的象征。
慈禧归西,然阴气尚有,阴魂不散,致使以后的执政者都以擅长阴柔之术作为其成功的前提。这股阴气,这个阴影是如此的可怕,以致于晚近历史的社会化文明化进程将整个天下变成了一个庭院,也即是说,变成了一座监狱。
当江湖的自由空间被社会化的组织系统全部填满,那么庭院就成了监狱。这似乎是一种命运的捉弄,本来是将国家逐步按照商业文明的规则变成一个文明社会的努力,结果成了把庭院在一个乌托邦理论的诱导下引向一座全封闭的监狱的过程。究其缘由,须追溯一下慈禧所象征的那股阴气和那个阴魂。
当我指慈禧太后为中国晚近历史命运的象征时,我同时也意指了慈禧源自中国历史,而不是来自哪个外层空间。中国历史自先秦以降,经由汉唐的阳刚之气,宋明的阴柔之情,至有清一代,已入末路。用《红楼梦》的说法,则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红楼梦》开卷的补天神话,以女娲炼石一举,给历史注入了一股纯阳之气。然而,《红楼梦》又同时通过贾母的牌桌,向人们展示了诸如王夫人薛姨妈那样的阴毒角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