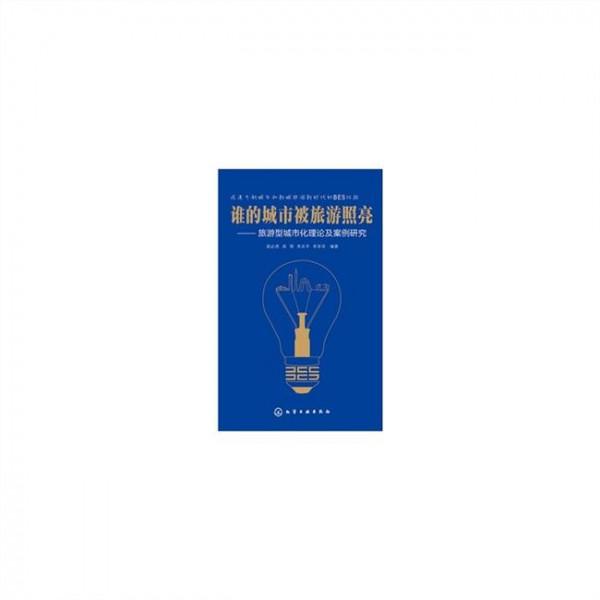农民工的一句话 贡献这么多但城市却容不下我

回家,对于在外地打拼的农民工来说,这两个字幸福而又沉重。每年春节前夕,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堪称人类最壮阔的迁徙运动之一。这其中的原动力,便是萦绕国人心头的那一抹乡愁。
小小一张车票,一头系着城市繁华,一头系着故乡亲人。一年的酸甜苦辣、快乐悲喜全都在这浓浓的乡愁之路上消解。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7亿,外出农民工总量逾1.6亿,其中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约占60%。80后、90后等新生代,已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中坚力量。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待“回家过年”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们对于故土、对于城市有着和父辈们怎样不同的情怀?
两天一夜、1000多公里路程,日前,记者跟随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安徽籍青年农民工梁启峰一起踏上漫漫返乡路,试图走进这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世界。

1月20日,离中国农历春节还有半个多月,在北京市崇文门地铁站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农民工小梁正在打点回家的行装。去年春节没有回家,今年,他想趁着春运还没到,早早地回家去看望4岁的儿子。
小梁名叫梁启峰,今年31岁,老家在安徽寿县农村。在这片拥有一百来号人的工地上,他是留守到最后一批的建筑工人之一。
在北京打拼的这5年,工地是小梁在北京唯一的家,“一年365天,有300多天都守在工地”。工地上有一处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小梁平时就住在那里。十来平方米的宿舍住了五六个人,一到夏天,臭虫爬得到处都是,咬得人浑身痒,“简直就是个臭虫之家”。

小梁觉得自己还算比较能吃苦,但在生活上,“能不亏待自己就不亏待自己”。这次回家,恰好赶上“史上最强”寒潮席卷全国,小梁特意给自己和同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父亲订了更舒适的高铁票。临回家前,他还给媳妇买了一部最新款的iPhone6s玫瑰金手机,给儿子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送给他玩游戏”。“反正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有团圆饭。最重要的是一大家子都开心!”小梁笑着说。

这种消费习惯曾经引起小梁父母的不满,但在小梁看来,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比如说,我可能会花一个月的工资去买一部手机,或者一件名牌衣服,但父母他们难以理解。我们在消费上更倾向于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小梁的父亲今年55岁,从2000年起就在北京打工,登上1月21日北京开往合肥的G325次列车,他还有点不太适应,“上次坐动车回去还是孙子出生的时候,急着赶回去,没办法。”在他的记忆里,以往过年回家买张站票都难,火车上总是拥挤不堪,人们手里提着大包小包,肩上扛着蛇皮口袋,“连铺盖卷都舍不得扔,要带回家去”。“如果换一身衣服,我跟北京人没什么区别”

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差距是梦想的不同。小梁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融入这座城市。不同于挣够了钱就回老家的父辈那一代,小梁和他的同龄人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天然的亲切感——他们基本上都至少受过中学教育,有些文化,很早就有城市生活经验,能够很快接受新生事物,这些都让他们对城市生活更驾轻就熟。

小梁自信,“出了工地,如果换一身衣服,我跟北京人没什么区别。”如果说父辈们在城市只是为了生存,他们则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尊严,“来城市打工不单单是要挣钱,在心理上也很渴望能够融入这座城市。”
为了在这座工作的城市扎下根,小梁比同龄人付出了更多努力。在小梁工作的建筑队里,80后、90后农民工一般占1/3左右,但大多数人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很大,“像我这样坚持5年干建筑的很少”。小梁从2010年来到北京,一口气在现在这所建筑公司干了5年,从一名填土、夯地基、轧钢筋的小工逐渐干到一名小工头。看图纸、指挥塔吊、检查施工质量……这些工头干的活,都是“自己当小工的时候一点一点留心学来的”。

2012年,在通州京杭广场工地,“31层的楼盖到22层的时候还没装施工电梯,爬上爬下全靠体力”,小梁得不断到各个楼层检查施工进度,一天要爬十来趟,爬到最后,“爬上22楼只要4分多钟,下楼只要3分钟”,工友们都“惊呆了”。

“工程封顶的时候,鞭炮噼里啪啦一响,特有成就感,就像上学的时候期末考试考完了一样。”小梁说,每当这个时候,他心里都会对这个城市涌起一股“建设伟大首都,我也出了一份力”的自豪感。
“我能融入这个城市,但有时候这个城市却容不下我”
同样在2012年,小梁的孩子降生了,这让他扎根北京的心有了动摇。自己在北京打工,孩子和媳妇在安徽老家,小梁心里多了一层牵挂,“最绝望的时候就是孩子生病了,自己在这儿干着急,一点办法没有。”

再过两年,儿子就要上小学了,“也许到时候我该考虑回老家了。”小梁说,孩子入学难、办证难、就医难,仍是困扰农民工最现实的问题。拿就医来说,现在农民工虽然能享受新农合惠民政策,可是由于异地不对接,在外打工生病了还是难以报销。“现在年轻,办证、看病问题都可以忍,但是将来孩子上学是个大问题,我不能让他像我这样荒废了学业。”小梁说。

有时候,小梁也感到很不公平:我们农民工为城市贡献了这么多,为什么难以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为什么社会给予农民工的待遇,远远低于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我们农民工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控制大城市规模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不是能接纳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让医保在全国通用,给我们解决后顾之忧?”
“最郁闷的就是,我能融入这个城市,但有时候这个城市却容不下我。”小梁叹了口气。说话间,列车轰隆隆驶出北京,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看着窗外的田野,小梁有些茫然。
“夜晚有灯光的房子,差不多都只有留守老人在家”

列车到达合肥站时,已近下午5点,天空黑云压城,眼看一场雨雪天气就要来临。小梁的家住在临近合肥的淮南市寿县三觉镇魏荒村,离这里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要回到村里,还得辗转几十公里。
汽车进入寿县境内,丘陵和农田渐渐多了起来。“我们寿县出过两个成语,一个是草木皆兵,一个是鸡犬升天,历史上做过好几次都城。”一路谈起家乡寿县的辉煌历史,小梁显得兴致勃勃。

然而,比起历史上的热闹辉煌,如今的寿县显得有几分萧条冷清。寿县拥有135万人口,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仅是小梁所在的魏荒村,全村3000多人口中就有1300名外出务工人员。青壮年男子外出务工,妇女老人儿童在家留守,在寿县农村,基本上“家家如此”。
晚上6点多,汽车到达三觉镇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车窗外,天空中开始飘起雪花。据天气预报,安徽省将迎来30年来最冷的一次寒潮。3米见宽的村村通公路上空空荡荡,刺骨的寒意让人不禁瑟瑟发抖。
在公路两侧,一排排两层小楼错落有致,但亮了灯的却寥寥无几。“现在打工的大部分都还没回来呢。”小梁指着那一排房子说,“你看那些亮着一点灯光的房子,差不多都是只有留守老人在家。如果家里打工的回来了,那一定是灯火通明。”

小梁家也是如此。凭着这些年打工挣的钱,小梁一家也在村里盖起了两层小楼。但楼房大部分时间都闲置,一家9口人,一年到头只有岳父岳母、妻子和4岁的儿子偶尔住在这里。“我们老在说城市房地产的空置率,其实农村房子的空置率是最高的。”小梁打趣说。
“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平时冷冷清清,一年里也就过年那几天热闹劲儿。”小梁说,“等到腊月二十几,在外打工的人都放假回家了。那个时候,村里就会堵车堵得跟北京一样!”

魏荒村有700余户人家,3600多名村民。据村支书魏敬业介绍,村里差不多所有的40岁以下的成年人都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通常,只有很小的孩子和老人才住在村里。但大部分都会在五六十岁时回老家。谁想在大城市过一辈子?空气太差,生活太艰难。”
小梁的父亲也是这样打算。过了年,他将56岁,“很多工地都不收了”,他的最终目标是回到老家的两层小楼里,享受田园的宁静,自己种点粮食蔬菜,过着农民的简单生活,颐养天年。

但对于小梁来说,这种目标显然是自己无法接受的。“并不是说对农村生活没有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没有父辈那么深刻、那么依赖。”在他看来,父母那一辈人,土地曾经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有安土重迁、叶落归根思想。而到了自己这一代,从学校出来就进了城里,从来没有依赖土地实现人生改变,生活习惯早已跟农村脱节,“家乡的牵挂不再是物,而只是人。”
“现在回农村老家,最受不了的就是太安静,一到晚上五六点钟,就只听见狗叫,安静得让人窒息。”小梁说,有时候晚上在村里散步,只有一些老头儿老太太在门口坐着,心里会涌起一阵悲凉感。这个时候,他总是怀念起城市夜晚的灯火通明。

小梁还记得,有一年过年他没有回老家,一家人在北京的建筑工地里过的春节。“外面很冷,屋里暖气很足,出门走几步就是超市,孩子在商场里蹦蹦跳跳,那次过年,我头一回感觉,在北京过年真好!”
“我们这一代,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但我们得奔着城市去”
如今,家里最让小梁牵挂的,是正在上幼儿园的宝贝儿子。虽然有妻子和岳父岳母在家带着,小梁还是不放心:妻子在老家一家工厂里上班,工作、孩子难以兼顾;岳父岳母年事已高,手脚已不灵便。

回家乡吧,收入锐减不说,一时半会还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留在北京吧,总归漂泊无根,孩子上学也是个问题。在家里,他是这个小小家庭的顶梁柱;而回到北京,他不过是70多万茫茫建筑大军中渺小如尘埃的一员,这让小梁有些进退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