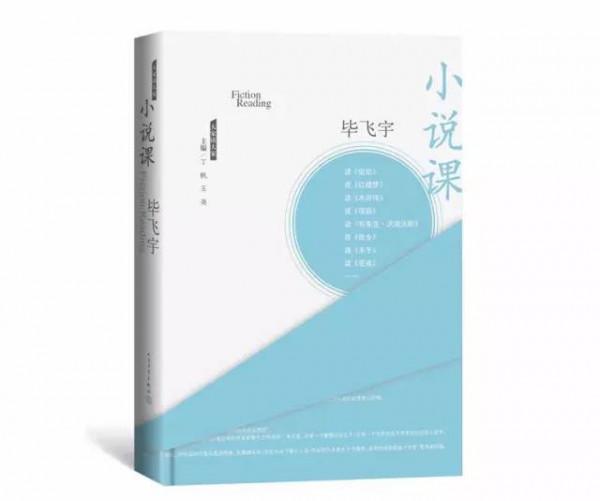毕飞宇文学自由谈 毕飞宇谈新作《小说课》:渴望这本书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渴望我的这本书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毕飞宇说,有时候他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比拟生命。有时候他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它就是玩具,一个手把件儿,他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和台湾作家许荣哲直接传授故事心法的《小说课》不同,毕飞宇的《小说课》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书中辑录了他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
《小说课》,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38.00元
如庖丁解牛式的解读中,毕飞宇将自己阅读过程中体会到的那些欣喜、感动、惊讶甚至战栗与读者分享。他认为,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
毕飞宇是一个对文字很苛刻的人。
他可能是最舍得耗时间修改的中国作家之一。一遍遍地修改,导致到最后他看自己的小说时会看到恶心。认真对待小说里面的每个人、每一章,甚至于认真对待小说里的每句话,是毕飞宇早年经历切肤之痛得出的经验,并成为他坚守的信条。
因此,毕飞宇大概是一个与作品修订版“绝缘”的作家;也因此,毕飞宇的眼光更值得信赖。当他谈小说的讲稿《小说课》出版,首先带来的期许是:什么样的小说在他眼里算得上好小说?一个挑剔的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定另有韵致。
2月24日,《中华读书报》在北京专访毕飞宇。
毕飞宇
中华读书报:看了您的《小说课》,才知道自己的阅读多么潦草。这些内容和篇目是如何确定的?
毕飞宇:确定篇目很简单,必须是经典,有广泛性。如果讲过于冷僻的作品,我就要把精力投入在介绍小说上。经典作品大家都熟悉,同学们可以直接进入小说,无论讲哪一个点,脑子里立刻会有闪现。
在备课的时侯我不会把自己当作读者,而是职业读者。具体一点说,把自己假设成作者,主要是去找他,他的感受和他的思路。读小说是可以一目十行的,但是,写却不同,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来,一个字你也不能跨过去。我是用自己写的心态去读的,这样我就可以抵达最细微的地方。
作品的格局可以很大,但是,对写作的人来说,细微处没有了,一切就都没有了。大格局不是粗枝大叶,这个问题就像升火箭,如果你决定做一个格局宏大的火箭,然而,细部不讲究,它的结果一定是放鞭炮。当然,写小说不是造火箭,我说的是意思。
中华读书报:您以经典的标准选择篇目。《小说课》除汪曾祺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仅仅是篇幅和时间的限制,还是另有原因?您怎么看待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的距离?
毕飞宇: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我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相对来讲更安全,如果我讲余华,他也许会告诉我:我可没那个意思,那我的脸还要不要?——这是玩笑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
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原因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给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我们谈中国的白话诗都要说起胡适的《尝试集》,它确实是经典,因为它是新历史的起点,但是那些诗好吗?我当年可是一边笑一边读的,它的憨态可掬远远大于诗的质量,说胡适憨会招骂,但《尝试集》的憨确实很可爱。
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认为当代文学已经具备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比现代文学的经典甚至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做作家就这样,在写出来之前,每个字你说了都算,发表了,你自己说就不算了。
中华读书报: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您对经典作品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吗?
毕飞宇: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千真万确。鲁迅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还是有新的发现,还是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对王彬彬教授说,鲁迅的小说确实是太好了。过去我们过分在意鲁迅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个作家的文本意识特别强。
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已经很成熟了,这个年龄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就有新感受,甚至是标点符号。
中华读书报:您对语言果真这么敏感吗?
毕飞宇:当然,给你举例子。我写过一个小说,叫《枸杞子》,第一句话就是“勘探船进村的那个夏季父亲从城里带回了那把手电。“我记得很清楚,等作品出来的时候,中间多了一个逗号,就在夏季的后面,拿到杂志之后我很不舒服。
这件事发生在90年代,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喜欢长句子,你多了一个逗号,它变短了,我生理上就不能接受。语言是呼吸,这里头的短长只有自己才清楚。你让有哮喘病的人像正常人那样呼吸,那就要出人命,反过来也一样的。
有一次在上海,我碰到了一个文学青年,他拿我开玩笑,说我知道你的语言了,就是主语 谓语 了 句号。虽然他说的不具有普遍性,但也有道理的。他这话有两点意思,一是我现在喜欢短句,二是我喜欢用句号。
中华读书报:您为什么喜欢用句号?
毕飞宇:我喜欢力量,这就要仰仗句号,因为句号最有力量。它像一把刀子。我特别喜欢“啪”的一下把豆腐撇成两半的感觉。逗号总是藕断丝连的。
从审美上来说,不论我想表达的东西是伤感的也好、抒情的也好,但在语言上,我希望它决绝。这是我的趣味。鲁迅对我影响很大,他的表达很清晰。我最爱的就是这种清晰。老实说,我是句号控,我喜欢句号的冷静和克制,我也喜欢句号的身份和体面。
句号是德高望重的爷爷,爷爷说,你回去吧。你必须回去。爷爷多亲切?多慈祥?可是不能抗拒。我不喜欢惊叹号,惊叹号太糟糕了,一惊一乍的,不好看。我也不喜欢省略号,装神弄鬼。屠格涅夫就喜欢省略号,当然,也许是翻译的缘故。我就是因为不喜欢太多的省略号才不喜欢屠格涅夫的。
中华读书报:这种趣味来自什么?
毕飞宇:一个人选择了力量你就必须选择清晰,不能拖拖拉拉的。在我的眼里句号非常有力量,就到这儿了,别给我啰嗦了。我喜欢句号和我开始喜欢短句子有关,它们是配套的。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课》中我第一次看到,讲究语言的毕飞宇也粗犷奔放了,有“伟大个头”、“吃饭去吧”等这样口语化的文字。因为是讲课的内容就必须保持这样的原生态吗?
毕飞宇:这是我刻意保留的。讲稿在《钟山》上发表之前,主编贾梦玮给我打电话,老一套,就是批评我。他建议我把口语化的倾向改了。我没有听他的——这是《小说课》,它来自教室,来自课堂。我希望可以保持现场感。在本质上,《小说课》不是学术专著,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是学术论著,那我的许多观点就需要论证,论证这件事我没有能力做,确实做不来,另外我也不想做。
为什么?我的许多结论是没有办法去论证的,许多地方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阅读直觉,说白了,就是猜想。老实说,这些猜想我觉得有道理,也许可以成立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论证它。我不指望在我这里能出现学术成果,我需要的是激发兴趣,拓宽阅读。
中华读书报:从另一种角度讲,这种解读也是评论。评奈保尔、曹雪芹……您怎么看待作家的评论?有什么特点?
毕飞宇:小说家评论作品时一般不会依靠概念,也不会过分地依靠逻辑,不是不想,是能力达不到。这是我们中国作家普遍性的缺陷,这是实情。当然,格非除外,他是双栖人,他太厉害了。附带说一句,许多人瞧不上学院式的研究方式,那是轻浮。
学院式的研究是一种非常高端的能力,作家可以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没问题,但我们不能轻浮——那我们评论小说依靠的是什么呢?是经验,是长期阅读所建立起来的审美能力,是直觉,是我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可我要说,直觉是双刃剑,有时候,它比逻辑更精确,更生动,但有时候也会找不到北。我还想说,大学的文学院只有学者没有作家是个缺憾,但文学院只有作家而没有学者,那就成笑话了,那要误人子弟的。
我说直觉有时候比逻辑更精确可不是胡说。没有一个小说家会彻底放弃逻辑,可小说家基本上还是依靠经验和直觉,当然,也有情感和胆量。讲海明威的时候,我特地提到了海明威对拳击手的描写,他一定会写拳击手的背脊、躺下和躲避的目光,为什么?因为海明威本人就是拳击手,他对拳击手的背脊、躺下和躲避的目光一定会有锐不可当的直觉。
我在课堂上说,海明威写这些几乎就“不用动脑子”,但是,什么是“不用动脑子”,我就有责任对学生讲清楚。
这些地方逻辑是说不清楚的。我记得当时我特地请了一位女同学走到讲台上来,她不明就里,刚走到我身边,我上去就给了她一拳头——当然,我不可能打到她,否则我得坐牢去——结果,这个女生闭着眼就转身了,给了同学们一个背。我相信,在这个点上,所有的同学都懂得海明威为什么要那样写了。
中华读书报:平时的阅读中,所有喜欢的经典作品您都这么翻来覆去地对比着看吗?包括不同版本的同部作品?
毕飞宇:我阅读经典小说,基本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太正式,其实我把玩的心更多,有点像玩古玩。我不玩古玩,我就把读经典当做了古玩。很省钱的。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
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能学习到什么不重要,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我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很谦虚,其实我是骄傲。我说,如果没有阅读,我的写作抵达不到现在的层面。我基本上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我无法想象您如何把玩一部作品。
毕飞宇:我看小说,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我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我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我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我经常在替别的作家“写”。就阅读而言,这个习惯并不好,但对于我而言,恰恰是别开生面的阅读方式。
中华读书报:您都替谁“写”过小说?
毕飞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檀香刑》——我都替他写过。我和他的区别远远大于重合,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他的原因。《透明的红萝卜》和我的契合度还是挺大的,那里面有我的生活场景,可是,《檀香刑》就麻烦了,它不在我对小说的认知范围之内,尤其他对凌迟的描写,太吓人了。
我不是说凌迟吓人,是说莫言对凌迟的小说处理吓人。我估计没有几个人会像他那么干,可他就是那么干了,那是要把作家写死的知道么?余华发明了一个文学感念,叫正面强攻,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莫言会选择在这么一个地方去正面强攻,那需要消耗多大的能量?不写作的人不一定能体会得到,那个太考验我们的神经了。
我和敬泽老师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敬泽说,这就没办法了,莫言就是有那么大的能量。
中华读书报:在重新理解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毕飞宇:谦卑。
中华读书报:您写作和讲课,都特别重视美学。您是怎么理解美学在写作中的意义?很多作家只会写,但很少像您这么清晰地提炼出来。
毕飞宇:美学是作家的软件,无论你怎样运行,都是软件在工作。一个作家的美学素养决定了他的一切,简单是说,就是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是作家的维度。
中华读书报:是否与你们这一代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与文化氛围有关?
毕飞宇:是的。跟50后之前的作家比较而言,60后的作家带有去故事化的倾向。尤其是先锋作家,不仅去故事化,有的时候甚至是去人物化。正是由于这样的美学倾向,形成了60后这代作家的共同特征,我们的文体意识都得到了很好的发育。
老实说,在艺术的准备上,我们都比较充分。余华、迟子建、格非、苏童、李洱、艾伟、东西、红柯,韩东,朱文,李冯,还有远在美国的李大卫,我很喜欢他们,我也是他们的读者。我们有我们的自觉文学,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文本在那里呢。
中华读书报:这种“自觉性”对写作的影响是什么?
毕飞宇:自觉文学和非自觉文学很不一样,不自觉的文学有可能出好作家和好作品,但是,那个带有偶然性。自觉的文学就不一样了,绝不会写到哪儿算哪儿。自觉文学是有美学确认的文学,有价值追求,有风格追求,有语言追求,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作家都不是靠生活积累才成为作家的,是他们在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是作家了,最起码,在素养上是,在认识上是。那些作家在语言上的标志性都非常强,很风格化。他们的辨识度非常高,原因就在这里。
我想说,自觉文学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做出了贡献,当代文学毕竟已经抵达这个高度了,这个用不着假谦虚,这是任何一个批评家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毕飞宇:从现代主义回到古典主义,就这样。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我还是借用西方建筑的一个概念吧,新古典主义。
中华读书报:那么《小说课》在您的写作过程中有何独特的意义?
毕飞宇:往小处说,小说课满足了我喜欢聊小说的欲望。我喜欢这个事情。往大处说,我也承担了老作家的一个责任。年轻人是不是认可我,我不知道,我无权决定,但是,我尽到了我一厢情愿的责任,一个南京大学的教师的责任。
中华读书报:您经历先锋时代,在摆脱“先锋之壳”的时候,是否也有过纠结?
毕飞宇:纠结,当然纠结。其实也害怕,我不知道最后能走到哪里,是乡下人的蛮横和勇气战胜了我的纠结和恐惧。乡下人不怕死的,逼急了,他就玩儿命。大不了一死,失败了,多大的事?
中华读书报:“乡下人”?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毕飞宇:你也不是外人,那我就说了,我是土地上生长的艺术家,本质上我是艺术家,很不靠谱,斜着生,歪着长,如果风调雨顺,我也可以结几个果子。好不好吃不关我的事。
中华读书报:《小说课》中的内容,跨度有多大?
毕飞宇:比较大。我的好友庞余亮替我算过了,从《水浒》到汪曾祺,六百年。
中华读书报:此前很多作家已有过先例,将自己的讲稿整理发表。接下来也还会有苏童、马原、叶兆言等作家加盟。这些作家的“小说课”,对于文学界来说有何意义?
毕飞宇:这个我要说一下,这一套书是关于全民阅读的,全名叫“大家读大家”,丁帆教授和王尧教授共同主编,他们有一个总序,总序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套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江苏明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
丛书集中了很多我尊敬的同行,我第一个出,这个是必须的,最矮的必须站在最前面,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对了,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原先有李辉一本书的,但是很不幸,他的太太应红女士是人文社的副总编,为了避嫌,李辉就退出了,我失去了和李辉一起出版的机会,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