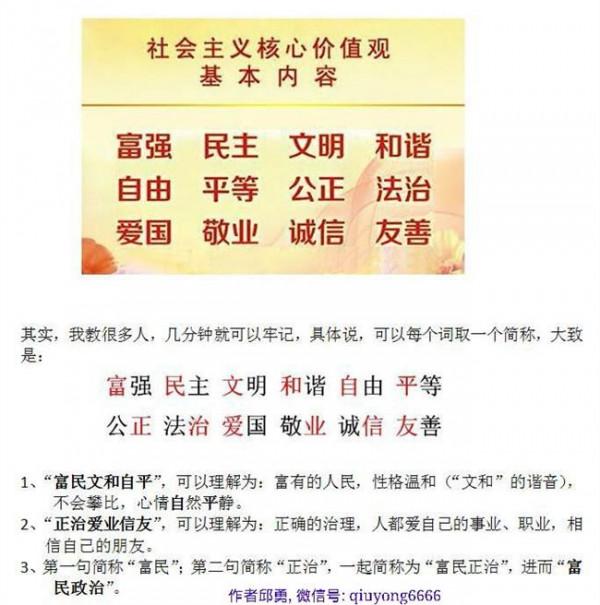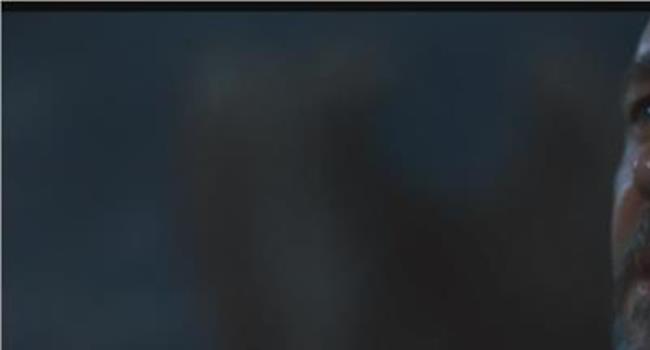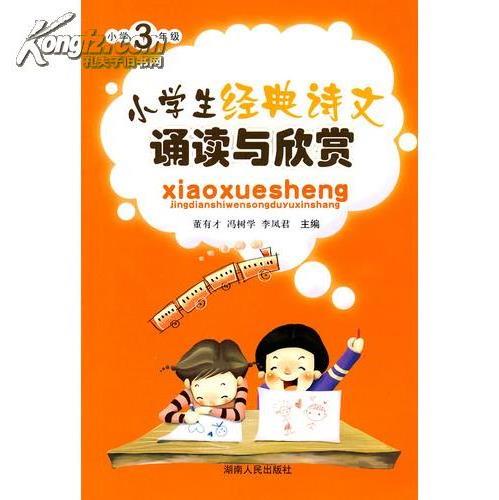余秀华诗歌中的经典句 评余秀华:在生活与诗歌的双重坐标中
关于诗人余秀华的所有争论,不外乎围绕两个话题:她是什么样的人?她写了怎么样的诗?
就第一个话题而言,谈论一个诗人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有必要么?没有必要么?
一个受过文学专业教育的人多半会说,不是那么有必要啊。自有“新批评”以来,“文本”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词汇。文学研究者关心的是文本,而并非背后的作者。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生活中是什么样的,这无关紧要。就像钱锺书那句著名的话,你觉得鸡蛋好吃,却没有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有些时髦的文学从业者还会把罗兰·巴特的话放在嘴边:作者死了。
但余秀华的火,显然不是纯粹因为诗歌,也不只发生在文学圈。她是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火起来的,是因为她“不太一般”的身份、“不太一般”的身体火起来的。她的诗,只有与这些“不太一般”并置在一起,才会让大众有兴趣。如果只面对诗,大众是缺乏足够的耐心的。大众更关心的是故事。媒体需要不断提供令读者感兴趣的故事,需要讲述余秀华是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被媒体叙述的余秀华是什么样的呢?
余秀华是以“脑瘫诗人”这样的称号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一开始,她的农妇身份和脑瘫病症一再被重复。正是因为农妇、脑瘫这两个词和诗这个词之间巨大的反差,让人充满好奇地来打量她的诗。尽管“脑瘫诗人”的命名在文学话语系统里一再被批评,但从大众传媒的角度看,“脑瘫诗人”是一个绝妙的命名。如果不是这个命名,余秀华恐怕难以得到这么多的关注。
后续的一些报道,着力描述余秀华的精神和身体、灵魂和她所处的乡村的差异,把她说成一个身处平庸困厄的生活中却享受着精神自由的“在别处”的诗人。这样的描述基本上对余秀华是溢美的。
这种描述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在“脑瘫诗人”这样的称号出来以后,就可以想象会有这样的描述。余秀华身陷苦难的高贵形象,完全符合大众的期待。对于许多人来说,阅读是一种消费,他们只为自己期待的阅读买单。复杂的思考是不适合被消费的,人们期待感动、安慰剂一般的感动。就像张楚曾经的一首歌中唱到的那样,这是“随时准备感动的人民” 。因此,媒体自然贩卖“圣洁的灵魂不幸落入残缺的身体”这样令人感动的故事。
在这样的描述下,余秀华的诗很难得到质疑和批评。因为,说她的诗不好或者不够好,就是破坏感动,这是多么煞风景和惹人厌的事啊。
但最近这样的描述开始出现了裂缝。曾经提携过她的一名当地编辑和一名网上论坛的诗歌版主陆续发出文章,描述他们眼中的那个古怪、偏执、放肆、喜欢骚扰人又喜欢骂人的余秀华。这难免破坏她之前的形象,却也不令人意外。
把余秀华的“圣女”形象和“泼妇”形象结合起来,或许更全面一些。我以为,余秀华身上体现了一种“想象的诗人人格” 。之所以说是“想象” ,是因为她以想象的人格方式来行事,把自己活成了想象之中的样子。这并非一种贬低的说法。事实上,许多人都在践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有些诗人如果不冠以诗人的名号,就循规蹈矩,而诗人的身份则庇佑他们做些不太一样的事情。“诗人”是诗人的通行证。
对于余秀华来说,这种“想象的诗人人格”使她意识到自己和平庸困厄的生活的差距,支撑她以诗人的身份生存。如果不是火起来,她或许一直陷于这平庸困厄中,这种“想象”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打破。幸运的是,她火了,毫无疑问,她可以是一名诗人了。
如果说诗是诗人的对象,那么诗人可以成为小说家的对象。米兰·昆德拉曾有一部关于诗人的杰出小说《生活在别处》 。像余秀华这样的诗人,也可以成为一部杰出小说的主角。
就第二个话题而言,以专业的态度谈论余秀华的诗,没有必要么?有必要么?
这似乎是个无需回答的问题。谈论一个诗人,当然要回到诗,专业地来谈。但基于大众传媒,这样的回答却也会引起反击。我看到网上不少人说,争论余秀华的诗好不好有什么意义啊,我就是喜欢,就是被感动了,与你何干。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到“天才的民主化”的概念。他的意思是,文化和艺术本来是精英化的。但在当代社会里,文化和艺术的等级被一种“感觉平等主义”取代了,即人人都可以说自己对某一部作品“有感觉” 、“我被打动了”或“我毫无感觉” 。
丹尼尔·贝尔说:“一个人可以同判断争议,却无法跟感受论理。 ”在感觉面前,批评家想要用自己的论断说服读者变得徒劳。因此,谈论作品成为没有意义的事,试图引导读者更是徒劳。
想要以专业的评论影响大众是困难的,而且专业地谈论作品,本身就要比谈论诗人难得多。这让真正谈起余秀华诗歌的文章显得可贵。在不多的这样的文章中,沈浩波的《谈谈余秀华的诗歌以及大众阅读口味》和廖伟棠的《大众喜欢的诗人也能是好诗人》尤显专业。这两篇持相反观点的文章都是有效的,尽管我个人更认可沈浩波。
这种有效是针对一些关于余秀华诗歌的无效言论来说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
除了诗艺上的差别(这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了) ,余秀华的诗歌在气质上与狄金森的也有明显不同。狄金森的诗中虽然经常出现“我” ,但绝非余秀华诗中热烈地自我表达的“我” 。余秀华诗中的压抑和压抑后的释放,在狄金森的诗中也很罕见。相较于狄金森,余秀华的诗同美国的“自白派”倒有那么一点相似。称她为“中国的普拉斯” ,尽管也会令人愕然,倒比“中国的狄金森”略微恰当一点。
之所以把余秀华比作狄金森,大概是把余秀华当成了一个像狄金森那样的离群索居、孤独写作、偶然被发掘的诗人。这实在是个大误会。余秀华虽然住在农村,但并非与世隔绝,网络把她和“诗歌圈”紧密联系在一起。余秀华成名之前,在网上发诗已有不短的时间,她在诗歌论坛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她从同时代的写作者那里汲取了很多东西。这与狄金森是完全不同的。
余秀华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网络诗人” 。她诗歌中的好与不好,都与“在网络时代写诗”这个背景有关。网络时代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数量,很大程度上消平了信息的不对等。以前,经典作品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读到的,现在却可以随时在网上读到。
网络上的交流互动也比以前多得多。这使得一个人的写作可以在网络滋养下很快成长。这也正是余秀华这个被冠以“农妇”的诗人不写乡土诗、不写田园诗,反倒写得很“洋气”的原因。在网上,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在别处” 。
余秀华写出了不少精彩的句子,在此不再列出。但她的诗,往往在整体上缺乏构造和经营,句与句之间缺乏必要的紧张关系,有时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这使得她在写出精彩句子的同时,并没有太多整体呈现张力的佳作。余秀华的写作还是一种自发性的写作,她需要写得更自觉一点。这种缺憾也跟网络有关:写作容易速成,却不容易达到真正的成熟。
不考虑余秀华的诗究竟怎样,单论她写诗的行为也值得欣赏。她把诗比作摇摇晃晃的世上的拐杖。诗支撑了她,安慰了她,照亮了她,这是诗的光荣。诗证明了自身的光荣。但这和余秀华给诗增添了多少光荣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