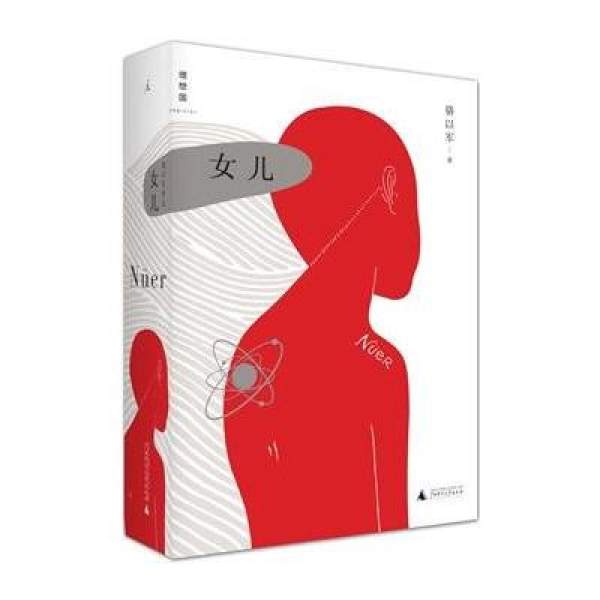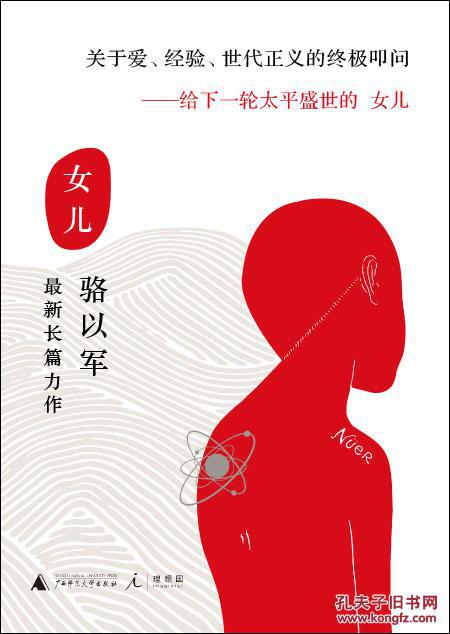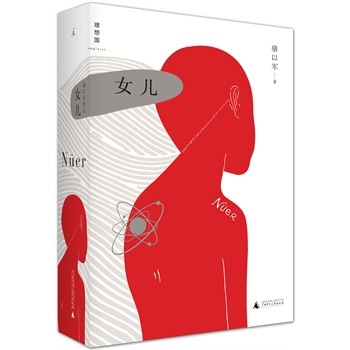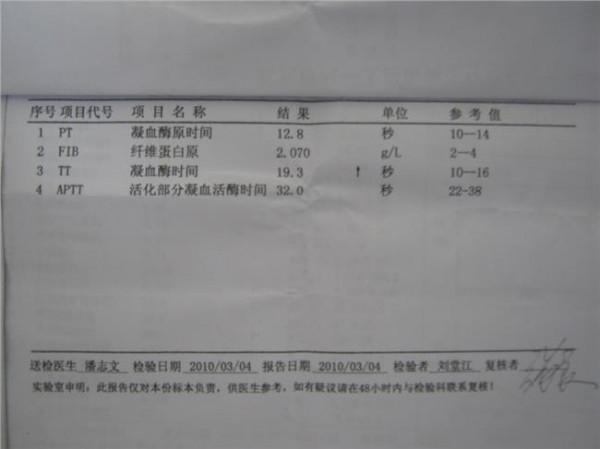骆以军女儿 女儿(骆以军所著书籍)
魔术时刻戏剧性滚落的泪珠,精密练习过上千次的侧脸低头微笑——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女儿。
什么事情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被预知了,剩下的只是绣补拼缀那朽烂斑斓的花片,这真是最深的悲哀。
亦真亦幻的岛屿纪事,影影绰绰的剪影侧写。量子力学里充满诗意,经验匮乏者掷下骰子,展现的却是现代人贫乏却多余、悲欢难以言喻的自我孤独宇宙。在《女儿》里,那些“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原本可以……”,一个更好的世界、更好的自己,最后总是为大大小小测不准的伤害掠夺去了人生。
女儿,作为爱、文明、救赎的原型,在漫长疲惫的未来里,她们将如何弥散、传播、叠加、干涉,自行演化;直到被观察到的那一瞬间,方塌缩成真?
我们当然是在一个分崩离析,全面启动的伪经验世界。我想《女儿》已不是《雷峰塔》里的女儿了。——骆以军[1]
女儿作者简介编辑
骆以军,台湾当代小说家,1967年生于台北。作品包括小说、诗、散文及文学评论,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长篇小说《西夏旅馆》2010年荣获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1]
女儿图书目录编辑
每个字词都裂解,骆以军的两个世界 蓝天使 私语 在微若之前有个房间 走钟 护士 宙斯 一个悲伤的故事 大房子 父亲 粒子互缠I 粒子互缠II 红楼梦 双面维罗尼卡 阿达 科幻小说 睡人 袭人 浮花浪蕊 公主 红包场 贾母 大雨 我老师夜间酒馆 深夜酒馆 核爆 斩蛇 最后的故事 那一夜I 那一夜II 梦里[1]
女儿骆以军《女儿》,一部不易读懂的小说编辑
对骆以军而言,小说家的创作从来不只是小说,而更系于“小说反思”,在小说之中有小说的思考,以小说反思小说,或者这二者根本是同一回事,文学的双面维罗尼卡。因此,书写《女儿》同时亦是书写“书写《女儿》的方法”。作家笔下流淌的每个字都同时是“故事”与“说故事的方法”,既是目的也是工具,是小说也是让小说断死续生的丹药。
其实自福楼拜以后,或者早在塞万提斯,小说家便已不可能是天真的讲故事的人。回忆、经验、幻想、梦境、理论……都可以是小说的素朴内容,但亦都不是严格意义下的文学,因为所有小说都命定“已经是后设小说”,都必然投身于“小说如何(再)可能?”的究极设问与洪荒创造之中。写小说同时也必然是写小说自身的理论,是自我证成与自我批判的永恒回归。
这就是当代书写的艰难处境。文学衰竭甚至已死,这句话没有其他意思:书写不再有典范、不再有套式亦不再有类型可循,一切书写都必须从零度开始,写小说意味同时书写使小说存在的崭新理由与方法。文学是一种“自我奠立”之物,“‘在那坏毁之境重新组装回自己’的那想象的一生,就是‘自己的一生’,终于修补回一个完整人形的时刻,恰也正是这个‘自己’生命走到尽头衰老将死的时候……”(p.610)
当然,这并不是在小说里套索西方理论或私心准备“被评论”,亦不是要所有小说都需写成僵硬的“后设小说”或“后现代小说”,更非在作品中繁复用典以示博学。理论、后设或用典(甚且是“假理论”、“假后设”或“假用典”)都不过是当代小说与思想结盟的多样性实验,然而,蛰居此书写核心的却是创作者的反身自问:小说家以小说探问何谓小说,正如画家之于绘画、作曲家之于音乐或电影导演之于电影。
对小说本质的自我设问,骆以军从不曾须臾离开。这使得他每一落笔,文字便裂解为二,如同两道不同却螺旋交缠的系列世界:一边是汹汹旭旭令人咋舌的各式故事奇谭,另一边则同步旋绕着关于此故事的“叙事条件”;一边是文字艳如古瓷斗彩的台湾当前生命变貌与奇观,另一边有“小说反思”与“虚构书写”的强势共生。每个滚动于纸面上的字都构成小说,同时也紧咬住小说成为小说的形上设问。
这是当代小说职人所必备的一目重瞳,语言极高明的影分身之术。
小说欲抵达虚构之化境,这是张大春一九九○年代的未竟之业。就某种意义来说,骆以军或许从来不曾“摆脱张大春”,相反的,在对于虚构的形上探索上,他比张大春还张大春。后者的问题不在于使现实过度虚构,而是虚构并未曾再虚构,因此停留在一种虚构的本质主义之中。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虚构从来不简单等同于说谎或炫学,因此真正离场,“离开张大春”的,是张大春。
当代书写诞生在一种孪生的对偶运动中,是自己对自己的内在增压与临界调校;既是书写也必是书写的书写,书写的生灭消长及其可能条件都束缩压挤入每个被写出的字词之中,每个字因此都已蜷缩折曲了整座宇宙的所有向度,同时是宇宙也是宇宙诞生运行之法。
透过意义与意象一再强化的浓洌字句,骆以军使得真正的小说部位由长篇叙事成为掐头去[2] 尾的强度断片,再反复炮制为盐卤般的事件长句,最后凝练结晶成故事字花,字即故事:故事被强势折曲于奇观式的修辞增生之中,如蛇腹拉开的华丽辞藻并不是故事的妆点,而就是故事本身,这是《西夏旅馆》(甚至长达十年的《壹周刊》专栏)所高度演练的小说技艺。
《女儿》无疑地扩增了这种“人脑奇观”,“如果是小说,她必须是炼金术士的小说,将杂碎、耗费低度心智在一无明状态的,或是密度松散的贪嗔痴、晕车般摇晃漫游的罗曼史,没办法给予启悟的平庸大革命史……全予筛漏、高温熔烧、滤去平庸浊污的杂质,找寻金属的灵魂。
那或是每个句子皆是浓缩、隐喻、折叠、典故、神话学、巫术或古乐谱的诗句。
”(p.606)然而,《女儿》(或《西夏旅馆》)毕竟不是诗集,高单位精练浓缩的字词亦不太是传统意义下的美文,那是每一次都企图将一整个宇宙的力量压注到被书写的字词之中,但每一字词同时又都反过来成为宇宙的无穷镜像,换言之,“在更高维度的智慧中”练习用神的眼睛观看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下,骆以军无论如何都是巴洛克的,这是他与上一辈作家的根本差异(郭松棻的逆向书写?)。巴洛克并不在于任何建筑或绘画形式的简单指涉,如果在《女儿》中文字如抽象风暴般被鼓动、如战争机器般被驱驰,并不只是为了小说中总是无穷叠套吞噬的叙事构成或人物事件间翻滚如涡旋的错综关系,而是缘于对无限的迫临想象与究极虚构。
“神明已不在世界之上,而是被含纳其中、肉身化于世界。”(W. Worringer)高烧炽热的语言与冷静敏锐的反思构成小说不可分离与不可化约的书写操作,最高明的虚构来自这二者的相互含纳,而巴洛克小说家骆以军正是此操作的趋向无限,这是他小说风格中最强悍与最重要质地。
因此,在《女儿》中对天文学与量子力学的一再援引,在所有作品中不断回返的文学经典与各种典籍并不是为了用典与炫学,换言之,不是对读者的知识或历史考校与霸凌,而是意图以繁复的词条语汇织就一张迫近无限的织锦,意图由“一枚不规则拼图小硬纸块逆推出一幅一千片的蒙娜丽莎微笑、一坨揉掉的废纸团繁殖出整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个密码、一个视焦重叠混乱的旅馆房间似曾相识的曝光影像……如果所有发生在眼前的事,只为了作为拼组一个巨大的谜团之材料……”(p.
4)。在有限与无限、极小与极大、单子与宇宙、心灵与物质间无穷折曲扩延的操作中,书写的巴洛克运动不言而喻。
骆以军以爱讲故事闻名,但《女儿》作为一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恐怕没有人能具体重述其故事,因为摩尔量巨观的大型故事已被彻底敲碎、泯灭于强势的折曲操作,宇宙等级的“大故事”被按捺压挤于字句之中,成为“字-故事”或“分子故事”,成为敷衍大故事表面的金箔与面具。
《女儿》就像以极高明文字所鼓吹撑大的膜,一切都发生在膜上,如吹泡泡般无穷增生繁衍,真正的宇宙仅是这层膜的翻折搅动。在《女儿》中,大故事被彻底瓦解与分子化,书写《女儿》的无限方法与修辞奇观成为故事,小说成为职人极天才与极专业的形式操演,这便是骆以军所祭出的巴洛克小说难题:字词的总体并不是故事,但故事无所不在。
在这个意义上,骆以军成为台湾当代小说家中极少数(如果不是唯一)能以“文字工夫”与舞鹤分庭抗礼的作者。
但另一方面,作为读者,《女儿》挑战的恐怕更是小说与故事间过于单纯的关系,战场已经转移到文学的分子层级,强化的魔性字词是故事的单子化,而非仅是单纯的修辞与美文,读者的大脑亦必须“流变—分子”。
因为爱讲故事而致使每个写下的字词都活色生香演技十足,甚至作品本身便是这些“分子故事”的盛大游行与众声喧哗,各种《女儿》的“大故事”版本被反复折叠与微分,以“字—故事”的方式求取逼近无限的极限值:
在此,主宰性的大故事退隐却又含纳一切可能的故事,成为故事的无穷级数。《女儿》是一个以“字—故事”所紧致填满无有空隙的宇宙,对文学的信仰转化为故事神学,成为巴洛克书写下的“女儿神”。
《女儿》成为读者内在巴洛克成分的试金石,文字如最饱满硕大的复瓣牡丹层层绽放。长期以来,“教育者”骆以军使得阅读必然同时是一种语言维度的飞梭挪移:时而是每隔几年便重手推出的长篇小说,时而是一周一次的《壹周刊》专栏,但亦是每天的脸书、现代诗、散见的访谈,甚至书评与导读。
虚构透过骆以军化身无量百千万亿于各文类之中,写狗、写小儿子、写按摩、抽烟、复健、小酒馆、永和老家……抑或点评当代文学风景、推荐书序、评审文学奖……骆以军同时是父亲、儿子、专栏作家、脚底筋膜炎患者、大乐透赌徒、老烟枪、失眠与暴食症者、爱狗人与书评家。
但另一方面,飞掠于各式文类并述说怪奇内容的每个字句都同时怦然响着同一种声音,已经华美的字句其实更珠玉藏椟地折叠着让所有书写者凛然的永恒叩问:小说与小说方法的双生双灭。
评论骆以军就是意图重现这个双星缠绕扩张的巨大文学天体,其中的暗物质、恒星、黑洞、量子纠缠与强弱交互作用……一切既存与外部的(文学)理论都无效(学院退散?),因为在“小说与其存有条件共生”的当代文学空间中,唯一合法的评论必然是由小说自身所就地组装的内在思想运动。
传统思维下的“创作/评论”二分法不再有意义,因为小说家同时亦是创造小说(评论)方法的人,超越性的理论套用必须由内在性的说情所取代。评论骆以军即是为他所曾创建的双生世界说情。
就像马尔科维奇所主演的《变脑》(Being John Malkovich,1999),由秘道进入马尔科维奇脑子里的男人可享有十五分钟以他的感觉与视线观看世界,但真正的戏剧性是,马尔科维奇最后亦由这个秘道进入自己的脑子里,于是他看到一整个“以马尔科维奇为分子的世界”:男扮女装的女高音马尔科维奇、享用美食的马尔科维奇、喝酒的马尔科维奇、马尔科维奇欧巴桑、马尔科维奇妈妈与马尔科维奇小婴儿……《女儿》或许就是骆以军版本的《变脑》,每个人物、每个句子与每个字都成为通入骆以军脑子并因此享有他小说家视线的密道,阅读《女儿》以便变脑“成为骆以军”,以便进入当代华文最风格特异的文学空间。
这样像洋葱层层剥开或包覆的剧中剧核中核,《女儿》里多次援引了《全面启动》(即《盗梦空间》——编按,下同)的多层梦境,“这一切庞大到远远超过人类能感知的负荷,那些‘多元宇宙’里即使最轻的一根羽毛,一粒尘埃,街灯孤零零投在石板上如粉尘的清光,叠加再叠加之后,其重量足以压垮那原本像纽约中央车站,可以出发、投射、到达‘任何世界’的那个自由的‘印记城’,那个‘薛定谔的猫’的箱子。
所以它到后来只剩下一种‘全面启动’的出发前的气氛。
”(p.589)梦境无疑地早就是骆以军启动虚构的起点,但作为一个“以说谎作为职业”的小说家,如果一切皆谎言,皆trompe-l’oeil(错视或“眼珠戏法”),或许只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不断叩问小说开端的巴洛克动态。
就像《续齐谐记》里著名的《阳羡书生》,书生口中吐出美貌妻子,妻子趁书生醉卧时也从口中吐出帅气的年轻情夫,情夫又趁夫妇俩共寝时吐出自己的情妇,二人在仿若梦境隧道的末端对酌,然后倏而又像俄罗斯娃娃一个接一个被重新吸入口中,还原为书生。
《女儿》的《双面维罗尼卡》亦讲了一个现代的版本,二位偷情者之一在旅馆中趁隙拨出手机与另一位爱人调情(唤出豢养在电子机器里的情人?),从一个说谎空间中再召唤叠套一个新的,在谎言的套式中又嵌入另一组谎言套式……“也就是说,她用‘他必须避开她对她男人说谎’的这个小空间里的不在场,又在梦中再开一道门,到另一个界面去和另一个情人谈情说爱。
只有谎言才能让谎言原本的混沌像镜中镜被折射得如此纯净。
”(p.275)故事间这样的重重叠套、榫接,故事的界限与界面屡屡成为骆以军小说中阴阳交接狼狗莫辨的虚构时刻,而正是在此,有华丽深重的文字充满魔性地从虚空中滚滚而出。
就像所有探寻小说本质的伟大作者一样,骆以军不可免地将触及宇宙论,以及宇宙论所不可或缺的诗意,这或许是《女儿》在内容上最明确的转变之一。但同样的,每一个谈及宇宙创生量子迸射的字词亦同时是两个世界的核裂解程序,骆以军就像是个极高明的单口相声大师,以一组文字同时讲两个故事,故事与故事的故事。这是“肉身在宇宙之中、但宇宙从诞生到死灭又都塞挤折入肉身”的不可能幻术。
然而骆以军从不是一个小说教义的形式主义者,如果每个字在他笔下都裂解成小说与小说道术的双声合唱,那亦是因为他对文学书写的究极探问总是镜像映射着生命与存有的高度思索。骆以军透过书写从不停止地传递着某种“温暖的共感”,这无疑是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伦理学核心部位,文学的本命。
形上学高度的虚构与伦理学深度的共感组成骆以军一切故事的DNA,小说从每个字词起便是伦理学与形上学所共同绞索的双螺旋构成。比如名为“宙斯”的狗,穿越了脸书、访谈、《壹周刊》专栏与《女儿》,这是同一条狗在不同书写平面上的形上学变貌与伦理学追索,亦是复杂生命在不同媒材上的丰饶切面,时而剪影、时而速写、时而白描、时而照相写实、时而浓墨重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