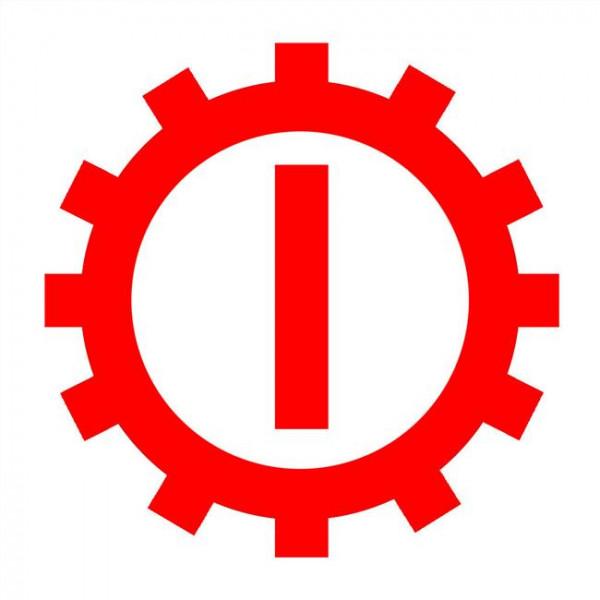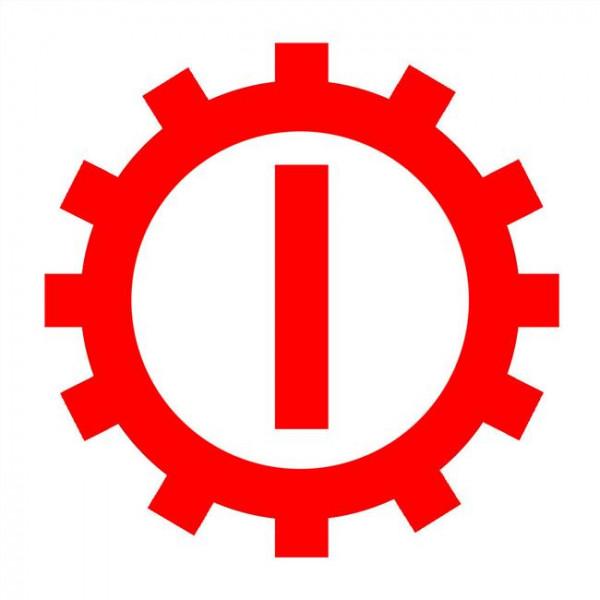艾晓明教授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找我开房 我灭了你
艾晓明,中山大学教授、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为了声援叶海燕,发布半裸照。裸露上身,胸部上写着“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右手拿把半张开的锋利的剪刀,表情强悍。
她是个女强人。她有一幅很珍爱的画。她很珍爱的这幅画在运输途中画框碎了。因为珍爱,所以要修复。因为是女强人,所以坚持不送去画廊,自个儿拿透明胶带、剪子、双面胶修理。敲敲打打粘粘,弄了40多分钟。她的脸像下雨似的淌汗,武汉太热了。她继续缠绕胶带,试图将乱七八糟的画框和画作捆绑在一起,偶尔去卫生间撕条卷纸擦擦脸。
“我就喜欢修复。”她漫不经心地说。
她叫艾晓明,中山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妇女和公共问题学者,曾积极介入和推动孙志刚案和黄静案,翻译、导演过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5月31日,60岁的艾晓明脱去上衣,袒露乳房,拍摄半裸照“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发布在个人博客和Twitter上,声援叶海燕。
此前的27日,女权活跃人士叶海燕在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抗议幼女性侵犯事件。3天后,叶和女儿在广西博白家中被一群男女围堵,叶因“持刀故意伤害3名妇女”而被警方行政拘留。
6月24日,星期天,武汉暴雨。雨点像钢珠弹,敲击在玻璃天花板上。艾晓明充耳不闻,手持一把红色小剪刀,专心修复画框。剪刀不到巴掌大,稍微厚一点的纸板剪起来都吃力,这是她用来干手工活,修饰家庭环境的剪刀。艾晓明还有一把大剪刀,是半裸照里的那把,原本是家里裁衣服用的,现在它被定格在照片里,看上去像把凶器。
“一边很温情,一边很战斗”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倩婷,在5月31日下午见到艾晓明,当时她已经看到那张半裸照。“那天上午我们去广东省教育厅递建议书,建议学校纳入防性侵活动,一种闹哄哄的工作状态里,突然在微信群看见那张照片。”柯倩婷回忆,“我的第一反应是,艾老师也在战斗!”
震惊之中,柯倩婷想起艾晓明说过身体是抗争的武器。紧接着感到难过:“逼迫一个60岁的母亲以这样的方式,为小女生追讨不被侵犯的权利,是不是太悲凉了些?”
中大副教授宋素凤曾经和艾晓明一起排演《阴道独白》,还一起裸泳过,她也看见了照片,心里笑了一下,想:“这果然是我认识的艾晓明。”
艾晓明的一位学生在这天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艾不是评委,但按照她的惯例,会携带花和酒到场。柯倩婷在这里见到她。当时艾晓明抱着一大束花,绢花,但生机盎然,还拎着一瓶茅台,“整个人看上去很喜庆的样子”。柯倩婷眼尖,她发现有字迹在艾晓明的领口透出。
“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两行字用粗粗的油性笔直接写在艾晓明胸前。艾晓明拍完照片,传上网络,引发轩然大波,然后穿上一条漂亮的宝石蓝定制裙子,戴上一串珍珠项链,带着这两行字来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
柯觉得字迹的笔风生猛,“它和宝石蓝长裙属于两种不同的风格和情绪,这就是艾老师,是她的两面,一边很温情,一边很战斗。”柯评价道。
这两行字的书写者是艾晓明的一位女性朋友,5月31日,她正巧住在艾晓明广州的家里。那天艾晓明从外面回家,两人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叶海燕案的进展,联系到最近曝光的8起女童性侵案,艾觉得要采取行动。她喊朋友:“过来帮我拍照。”
她们先用红色的笔写,艾晓明觉得不好:“红的代表喜庆,再就是红的也不是很鲜明。皮肤还是用黑色写字比较醒目。”她们换用黑色。艾晓明对朋友指指胸口:“你在我这儿写。”
“人体皮肤上有油,写不上去,用那种大号的、粗粗的记号笔,我们涂涂写写好半天。也可能因为不是新买的笔,放了一段时间了,因为我们一般不用大号的笔,可能是做什么培训,别人用完了扔下来的。最后写了十几分钟才写完那几个字。”艾晓明回忆说。
拍照也是朋友负责。“有的时候剪刀太低了,有的时候剪刀太高了,有的时候眼神不够危险。拍了五六张吧,选了一张。”她说。
支持问责万宁性侵事件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拍半裸照?艾晓明说,“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和“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先是有一封公开联名信,“征集千人签名,问责万宁警方”。联名信反响有限,媒体的报道也有限,“中国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非常多,针对儿童的兽行也很多,女权发出的这个声音太弱了。没人听你的。谁听你的啊,一封信有什么用啊?”
她不打算上街举牌。“叶海燕已经这么做了,你要解释就非常困难,因为警察不听你解释。”
拿起剪刀,袒露乳房。也许就是适合中国社会的方式,因为能传播。很多时候,社会进步就是在乱七八糟中推进的,或者说,社会进步的推进一定是乱七八糟的。是这样吗?
不过艾晓明不太喜欢《人物》记者上述“乱七八糟”式的解释。她强调用裸体来表达不是她一贯的工作方式:“女权主义的社会运动包括文化批判、社会批判、高等教育,当然也有具体在某个战役上的作为。不是说大家一起裸体上阵就是万无一失的百战不败的方法。每一种表达形式都有一个具体语境,它的作用也只能在具体语境里去理解。没有神器。”
艾晓明的那位女性朋友则不同意说此事“荒谬”:“艾晓明在拍摄时进入了一种严肃的创作状态。她的抗争正是中国荒诞政治处境下的严肃抗议,她采取了一种与通俗公众沟通的调侃隐喻方式。”
“艾晓明你好大的胆子”
室外大雨如注,对那幅画的手工修复仍在进行。小钉子从木框里时不时跑出来,我们尽量捉紧木条。
在广州,艾晓明身边主要是朋友和学生,而在武汉有她的父母、弟弟、丈夫、儿子。“在武汉我更像一个家庭成员”,这么说的时候,艾晓明正在四处寻找那把红色小剪刀。
想了解艾晓明,听她讲之外,最好和她一起做一件事。
中国当代著名揭黑记者王克勤和艾晓明在2005到2006年合作过,他们一起关注河北的艾滋病问题。三四个月里,王克勤在艾滋病人家里吃饭、喝水,艾晓明会抱着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女孩睡觉。王克勤想“艾晓明你好大的胆子”,“从那以后我觉得艾晓明好勇敢。比我勇敢”。
画和画框终于被黏合在一起。活干得很粗糙,但好歹可以支起来看了。“要是画廊看见修成这样,肯定说不行。”艾晓明笑眯眯地说。但她不会把它交给画廊的。
这幅画的主题是一个女性芭蕾舞者,她做了一个轻盈的舞蹈动作。艾晓明说看到画就能想起与之相关的经历,她也喜欢芭蕾和画中舞者呈现出来的那个瞬间:“自制和对身体的控制力”。
控制力来源于权利。艾晓明说女人第一层的权利,“身体是自己的,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另一层权利,“即使我脱光了,也有能力跟你反抗,如果你违背我的意志,我有保卫自己的权利。”
她说起冰岛女总理露乳沟:“露出乳沟怎么就是不端庄?你受着吧!你忍着吧!你没看过吗?你不就是乳房恐惧症吗?你到底恐惧什么?一看见乳沟你就不得了了,那实际上其实是你对女性进入政坛的恐惧。是女人就有乳房,有乳房就有可能露出乳沟,既然女性进入了政治领域,你的感官就得改变,就这么简单。”
午饭后,艾晓明主动教《人物》记者拍照,她把一把长长的刨子递过来充当“凶器”,开玩笑地让记者草拟“开房找我”的面部神态。“眼睛里要有凶光,”她一面按快门,一面教导:“想象你面前站着一个坏人,目露凶光,威慑对方!”
连拍了十几张都不够味。
“眼神太平和”、“又笑了”、“想象你最希望别人看见的你的样子”。艾晓明反复指导,仍未成功。
她的狠劲儿是可以立刻拿出来的。聊到半裸照里那把大剪刀的含义,她喝一声:“找我开房,我灭了你!”声音也并不怎么高,眼睛里凶光一闪。
“你那样拿着刨子能扎着人吗?”她看着记者,感慨道:“我们国家就是缺乏这种教育。真遇见坏人了让你凶,你临时根本凶不起来。”
“没走在谁的路上”
1994年,艾晓明出版处女作《血统》,讲她的“文革”记忆和家族记忆。她的外祖父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南京保卫战的守城指挥官。书的第一页,她回忆了自己在1966年学会的一种名为《鬼见愁》的舞蹈。“跳的时候,双臂下垂微弯,手做握空拳状,挺胸昂首,双目炯炯直逼前方,声调铿锵报出名字 ——‘鬼见愁’!然后边唱边做动作: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艾晓明在书里仔细说明了这一舞蹈的跳法:“跳到这个‘蛋’字时左脚猛一跺地,右脚同时踢起,右手四指并齐,虎口有力成锐角,刀切一般切向斜下方,目光亦斜视手势所指,含义不言自明。”
传记结尾处,艾晓明已经走到了她的1993年,她摘录了另一首时代歌曲,《一块红布》。
“‘文革’那年6岁的小毛孩儿崔健,如今把扎在胳膊上的红布蒙在了眼睛上,他像当年的宣传队员一样庄重地拨了琴,比他大一轮的汉子听得蒙住眼睛,呜呜呜,嚎啕地哭: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20年后的艾晓明已谈不上喜欢《一块红布》了,她说现在她“没走在谁的路上”。
她认为自己和“那个时代”的勾连体现在理想主义上。“理想主义是这一代人的色彩,不一定是家庭气质。以前我们那代人,受的比较多的是集体主义教育。”
艾晓明的立场分界线经常被划在1999年。那一年她的儿子面临高考,她却去美国进修,在田纳西州南方大学任访问学者。她发现美国家庭收养的其他国家儿童有不少男孩,但来自中国的几乎全是女孩。她还注意到美国图书馆里关于女权的理论教育书籍满坑满谷,而在中国几乎为零。
回国后,艾晓明写了一本游学散记,在书的结尾,她说:“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无数人群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发出声音。虽然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如果想到我们都是彼此的同类,又怎么能无动于衷?中国几百万艾滋病人、无数家庭暴力受害者、那么多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百姓,还有多少故事我们不知道?眼皮子下面就有堆起来的社会问题,假如不看这些,不去了解问题的成因,我觉得愧对写作的责任。”
2003年她做《阴道独白》,和很多学生一起思考“身体政治”,就是用身体来做自我表达。“从那时候开始,裸露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理论障碍。”
照片上网那天,一个老同学让一个小朋友转告她,裸体不是你的强项。艾心想,你说裸体不是我的强项,我倒想问问你什么是“强项”。再说“我觉得裸体也是我的强项啊”。
她马上在文章《乳房与剪刀奏鸣曲》里回应:“孤立地看一个大学教授人老珠黄去亮乳房,除了不知羞耻就是个大傻逼”、“我的乳房既不坚挺也不丰满,完全没有成为欲望对象的资格” 、“我的乳房是一个年届六十的女人的乳房,松软低垂”。
她挺乐,“他们如果要攻击不就说那些话吗?”
王克勤用一句话描述他对艾晓明这张照片的看法:“勇于挑战强权者稀,敢于牺牲自我者罕,遗憾。”
艾晓明的看法比王克勤更“革命”:“这件事里只有反抗精神,没有牺牲精神。”
6月12日,叶海燕拘留期满。回家看到了艾晓明的照片,“我眼泪唰就流下来了。她更像是一种战斗,就像战士的子弹上了膛,痛快地跟这个灰暗的世界拼了。”两人没有联系过。“也不用联系,心知。也许我不一定能理解她,但她一定会理解我信任我。” 叶说。
艾晓明的丈夫没有跟她讨论过这件事。儿子说过,“妈妈了不起”。艾晓明非常相信他们能理解这件事:“因为我儿子有女朋友嘛,我弟弟也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亲人之间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解释,他们也一直知道我是做女性研究、教女权主义的,所以这些对他们根本就不是个事。”
他们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和常见的家宴不同,这张饭桌上谈的永远是天下大事、异国体制见闻、互联网最新科技。恰巧这个小区的手机通话信号很差,网络信号也时有时无,没人能抱着手机刷屏。天下事能在一顿饭里从头谈到尾,好像每个人都扛着一架高射炮。
这种时候艾晓明倒不说什么。她在饭厅和厨房来来回回,帮客人倒茶,帮阿姨收拾,回到席间的时候,已经有些粗糙的手背上总是挂着水珠。她倾听高论,但笑不语。
夜终于深了,客人陆续散去。一位作家对艾晓明说:“本来今天想和你聊聊对某些事儿的看法。”艾晓明笑着说:“下次。”她和丈夫、儿子、弟弟站在一起,热情地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