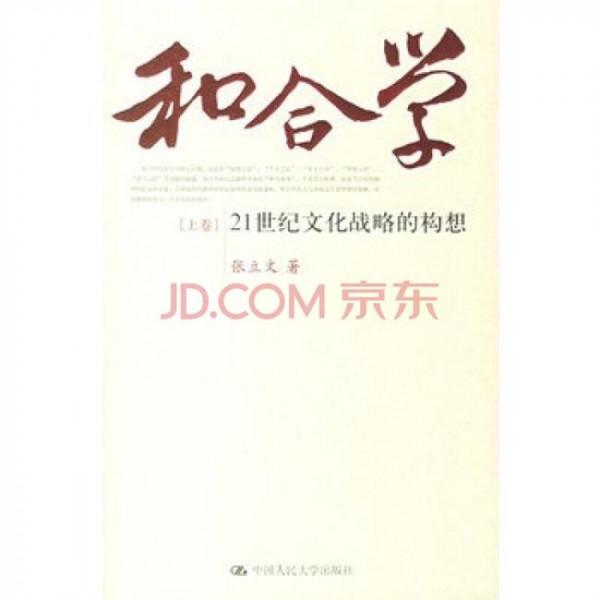聚焦从5000 年前到 21 世纪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之一——金融问题
作者简介:
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著名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金融与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中心主任。
书籍摘录:
1900 年,一位大胆的学者率领一支探险队从印度出发,穿越广袤的阿富汗“鞑靼高地”,阅遍古丝绸之路上荒芜的风景。这位拥有大无畏精神的匈牙利冒险家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是最富有传奇色彩和争议的中亚考古学者。
尽管当时中国的动荡和中亚国家摇摆不定的联盟给考察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开展这种工作不亚于进行一场“豪赌”,但斯坦因下决心重新探索和挖掘传说中连接罗马与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就像 2000 年前的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一样,斯坦因率领一支骆驼队和他的同事们沿着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线古道前行,穿过和田,来到废弃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丹丹乌里克曾是中国、印度、中亚三大文明交汇处的一座商业城市。
如今我们难以想象,这个位于中亚中心、沙漠边缘的城市曾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多语言的都市,虽然古老的城市轮廓仍然清晰,房屋、寺庙、高塔和城墙已经矗立了上千年。然而真正令人兴奋的发现是文献。考古队在其所到之处都发现了珍贵古籍:梵文撰写的佛教经文、汉字信件和笔记,以及现在被认为是死文字的吐火罗文。次年,斯坦因继续前往尼雅古城附近,在那里他发现了更加丰富且保存更完好的写在羊皮纸上的文档,它们在那里存放了近 2000 年。
斯坦因的考察表明,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之路,同时也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商人们长途跋涉,暂居异乡,与说着不同语言的人进行贸易,崇拜不同的神祇,丝绸之路成为整个欧亚大陆知识和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其中也包括书写系统。无论书写材料是木板、羊皮纸、棕榈叶还是最终的纸,书写都在扮演着基础性的信息媒介。

斯坦因最伟大的发现也是他最具争议性的发现。 1907 年,他跟随马可·波罗的文字穿越广阔的罗布沙漠,进入现在被称为塔里木盆地的地区。这条路线后来被证明是极为有利可图的。探险队艰苦跋涉进入敦煌绿洲。在那里,斯坦因参观了传说中的千佛洞。千佛洞是一座佛教圣殿,石壁上刻有惟妙惟肖的彩绘佛龛,拱卫有身形巨大的唐代风格的佛像。
从 4 世纪起,朝圣者就来此拜访。然而对斯坦因来说,真正的惊喜是一个不易被发现的、被小心看守着的藏经洞,里面收藏着自敦煌存在以来的全部档案。斯坦因认为这批文献可能会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无法预料的回报,这些档案记录着佛教与印度文化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过程。斯坦因通过贿赂获得了总计 5 马车的历史文献。
这正是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举世无双的宗教文本档案,最早可以追溯到 5 世纪。斯坦因收获的很多敦煌宝藏现在收藏于大英图书馆。后来的文献搜寻者们也设法买到了敦煌的古代文献,现在这些早期的文本被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当然,这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好处在于这些档案被保管在经验丰富的档案管理员手中,并且能广泛地被学者们研究;但不幸的是,它们并没有安置在故乡,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宝藏之一流落分散在了世界各地。动荡不安的中国近现代史使人们怀疑斯坦因的动机,他带走这些珍贵的文献恐怕并非偶然为之。
斯坦因后来再次回到丝绸之路。他于 1915 年在中国西部开始的探险活动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地区。这次探险的亮点是发现了阿斯塔那古墓群—一个被风沙掩埋的公共墓地,古老的亚洲人及其精美的陪葬品被一起埋葬在这里。和前几次探险时发现的情形一样,干燥的空气使得这里的一切几乎都保存了下来,从由奇怪的纸覆盖着的棺材,到死者带到往世的小糕点都保存得很好。

一些精美的古墓中甚至设有私人图书馆,还有做成音乐家、舞蹈家和艺人形象的陪葬人物佣,这些装饰精美的艺术品描绘了自唐代以来人们的生活场景。虽然斯坦因挖掘了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很大一部分,但是仍然为后世的考古学家留下了许多遗存。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工作了几十年,他们幸运地发现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唐代以来的墓葬。在其中一个墓葬中,他们发掘出了一组由陶瓷、布和纸制成的墓俑。这些墓俑在都城长安制造并被运往边疆,它们保守着一个令人好奇的秘密。墓俑们的胳膊是由废纸制成的,这些废纸在长安被搜集起来,然后由工匠重新利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中国最富有的女性企业家张茵通过搜集和再处理美国废纸,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阿斯塔那墓群中的墓俑告诉我们,中国企业家可能早在 1000 多年前就开始用这种方法赚钱。然而更重要的是,用于制作墓俑手臂的每一页纸上都记录着一笔7 世纪时发生于中国典当行的交易。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和她的学生安娜·玛塔–芬克(Ana Mata-Fink),对这些特殊的财务文件进行了研究。如此古老的长安商业记录很少能保留到现在,因为纸是非常容易腐烂的。这些票据仅仅是由于被再次利用并且被运送到干燥的地区才得以保留下来。事实上,一个引人注意但又悬而未解的问题是:在中国,纸张最初是如何成为商业记录和交易工具的。我们知道,竹简记录是合同记录的早期形式,但在纸张发明后,从某一时刻起,纸便成了金融记录的媒介。韩森是研究丝绸之路贸易的世界级专家。她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和家人一起生活在康涅狄格州海岸并为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她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的契约合同。典当业的票据非常有趣,因为它们与金融紧密相连。
韩森和玛塔–芬克追踪到当票的起源是长安。每张当票都记录了便携式财富的简单信息,任何有转售价值的物品都可以作为短期借款的保证金。最有趣的是,当票中包含了长安的三个地名,分别是:延兴门、观音寺和昇道坊。这些地址都指向位于长安东南角附近的典当行,大概离东市一两英里远。学者们能够有效地划分出古代中国都城经营借贷业务的区域,并指出典当行的运作方式。

典当行的客户并不是十分富有,他们典当的物品大部分都是些穿过的衣服,比如:一件黄布衬衫、一条装饰围巾、一件紫色的斗篷、一件丝绸外套、磨损了边缘的官员头饰和破旧的凉鞋。偶尔有一些贵重的物品:一匹丝绸、一面青铜镜,以及4 串珍珠。借款人一般都不曾受过教育。他们用张开的大拇指和中指两端的距离“拃”测量和标记物品长度,而不是在合同中用文字明确地记载下来。一些当票记录了利息的支付情况:崔进,农历正月十九借了 100 文钱。农历六月初七,他偿还了 40 文钱的本金和 9 文钱的利息。崔进取走了丝绸。农历七月十八欠款偿清。他生活在城东,时年 20 岁。
这个年轻人崔进是谁,为什么他需要 100 文钱?以 9% 的半年利率来借这笔钱是否值得?这份简洁的收据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年利率似乎比 20% 低一点。崔进借款次日的另一笔贷款也提供了辅证:王帅借得 40 文钱, 4 个月后偿还了 15 文钱的本金。他还支付了两文钱作为利息,这意味着大约 15% 的年利率。这样的利率也许很高,不过还难以算作高利贷。阿斯塔那墓群中出土的典当票据告诉我们,唐代有一个运作良好的个人信用体系,而且它的利率适中。
在这一体系中,便携的商品,特别是衣物,就等同于财富。当需要的时候,一件外套、一双鞋子或是一颗珍珠都可以抵押,从而转换成硬通货。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典当业刺激了消费主义的萌生,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私人耐用物品的二级市场和以此类物品为抵押的金融体系还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这其实是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事实上,与现金不同的是,保养良好的耐用商品一直被用作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典当是一种创造流动性的技术,它依赖于作为记录和签订契约的主要媒介的纸张。纸张被创造出来后不久,就被广泛地使用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之中了。

结论
本书广泛探索了作为一项技术的金融的发展历史以及它如此重要的原因。从开始几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金融技术历史悠久且应用广泛,它们不仅被嵌入文化经济学,还被嵌于社会和知识结构之中。金融工具和复杂社会的协同发展是一种在很多层面上互相妥协的过程。多样的金融方案带来了一些最重要的文明成就:书写、概率论、储蓄和投资机制,以及和谐的全球关系。与此同时,金融技术也造成了一些严重问题:奴隶制、赔款支付、帝国主义和金融危机,它们都与债务机制紧密关联。以一种长历史视角来看待金融本质的二重性是十分重要的,至少它能为我们思考如何设计未来的金融制度提供指导。
本书的另一个论点是,金融思维并不易理解。尽管今天金融家所采用的许多复杂技术可回溯至千年以前,甚至更久,但与传统相比,金融常会被视为舶来品或与传统的对立。经济危机和泡沫经常让人大吃一惊,期权、期货、债券、共同基金等金融工具,以及货币市场、公司、银行等机构在我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似乎无法想象的复杂。我认为原因(至少部分原因)是金融思维发展较晚且依赖于专业化的分析工具。从德摩斯梯尼提出的复杂的法律机制,到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中高等数学的应用,皆为这一点的佐证。
同其他技术一样,金融发展得越成熟,就越是要求人们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去了解和实践。由此类推,如果金融市场衰退,可能对每个人都产生重大影响,而不仅仅是金融家。社会常常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集体怀念金融出现之前的世界,但本书中的很多例子证明,人类文明往往正是依靠金融工具来实现价值传承,并化解无数的经济风险。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偶尔也设想过消除货币和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尽管这些建议呼吁发乎内心,但如果让金融工具倒退回从前的状态,就意味着我们要回到没有城市和大规模民族国家时的生活方式。

本书所持的另一观点是,金融问题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解决。中国的金融史就为我们提供了对于比较发展进行研究的机会,尤其是政治环境如何决定技术方案。例如,中国货币和铸币的发展轨迹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完全不同,不过最终东西方都把货币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工具。
在一定程度上,公司是现代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企业单位,跨文化比较同样显示出公司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非比寻常的现象。古代中国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公司,但却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这或许能够解释(或许也解释不了) 18 世纪晚期— 19 世纪早期欧洲和中国在工业发展上的差异。本书第 10 章探讨了李约瑟之谜。然而,在 19 世纪晚期,中国迅速采用了公司制,并赋予其新的目标,表现出了自觉的灵活性与能动性,中国人认识到,金融是一种可以学习并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公司的悠久历史表明这种制度安排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均衡,公司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博弈”,可被应用于不同的经营方式和不同的参与者。当全球金融体系朝着如主权基金类似的大规模集体性投资转型时,公司能否足够稳健地存活下去,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从全球金融发展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看来,欧洲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对资本市场的极度依赖。我认为这个特殊传统根源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四分五裂和衰弱。这一情况更深广的暗示在于,全球金融市场体系可能是包含有组织的官僚体系的强大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替代品。如今,金融市场与政府并存互补,但也不时发生冲突。金融史为理解这种动态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
历史本身就是有趣的,但历史作为衡量现在的标尺以及引领未来的向导的作用也同样重要。随着世界向一个集体性的全球文明转型,更大比例的人口融入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金融工具也需与时俱进。我们从共同的金融历史中收获的经验与教训具有更强的关联性。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以风险分担和跨期支付为目的的金融机制,以及这些金融工具的多种变化形式何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我们可以重新利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且从失败中学习应予避的问题。长达 5000 年的金融创新历史更是显示,金融和文明将永远不可分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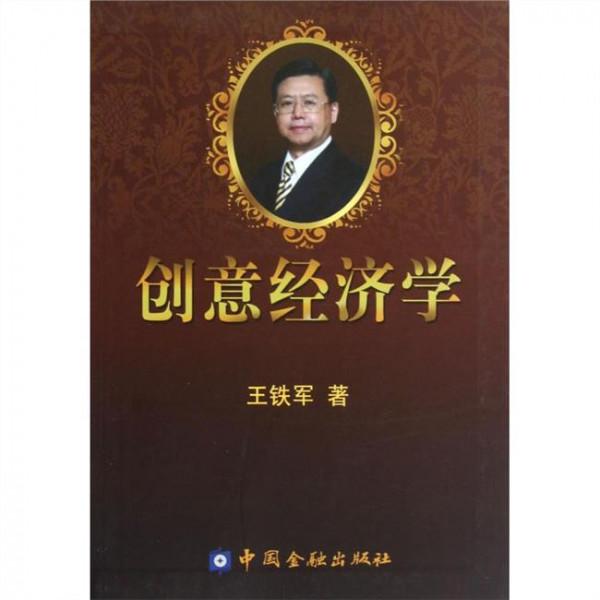

![>阮次山蒙古 [转帖]蒙古在21世纪中何去何从? 凤凰卫视阮次山](https://pic.bilezu.com/upload/1/60/160146d3938250be6837a9309bd36a89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