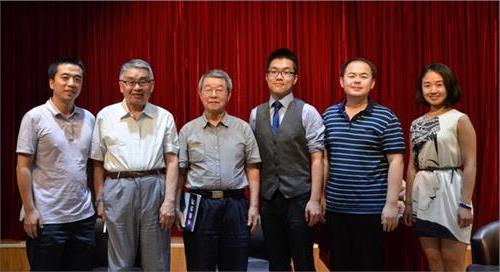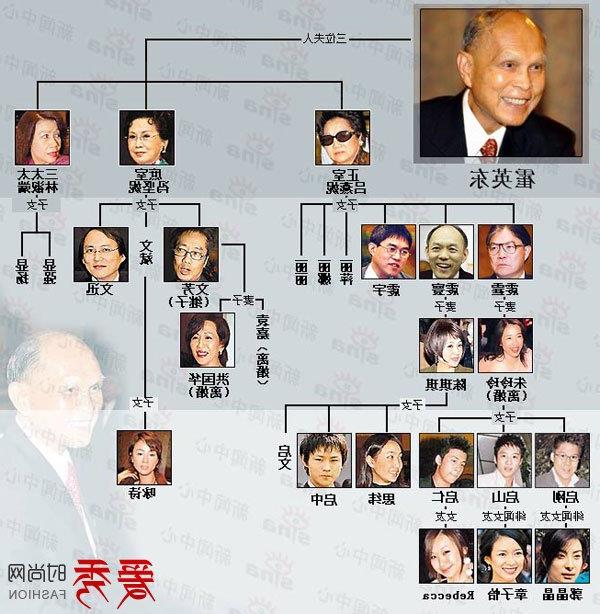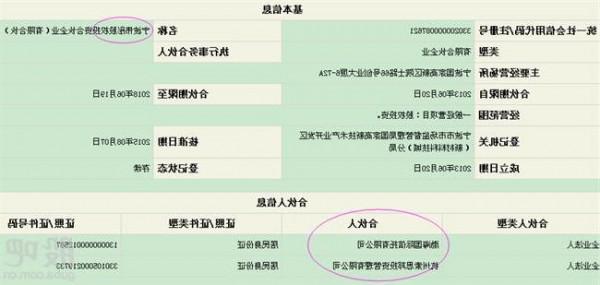荣新江老婆 荣新江:一位严格又和蔼的老师 上海书评2015
12月25日,田余庆先生以九十高龄去世。在八宝山的灵堂里,他安详地躺在那里,留给我们的,是值得珍惜的许多回忆……
我不是田先生指导的学生,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起,有机会受到他的种种教诲和多方关照。回想起来,他在我心目中,既是一位严格的老师,时常鞭策我们求学上进;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帮助爱护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稳步成长。
说田先生是一位严格的老师,有一件小事我一直记忆犹新。1983年我的导师张广达先生给我找到一个机会,在我研究生学业的最后一年里,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跟从许理和教授学习一段时间,同时收集我的硕士论文资料。作为一个在读硕士,当时办理出国手续很不顺利,断断续续拖了一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得到教育部相关部门的批准。一得到消息,我就赶紧去办各种手续。我向时任系主任的田先生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申请,田先生拿起来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拿起一支笔,把中间的一个字圈了一个圈,退回给我。我睁眼一看,原来匆忙之中,把“赴荷兰莱顿大学进修”,写成了“赶荷兰……”。我看着田先生的表情,不敢以这是简单的笔误而做任何解释,只能说是自己中小学没有打好坚实的基本功,在关键时刻就会出毛病。这件小事,让我一直牢记在心,田先生的严肃面容,督促着我在此后的治学道路上,不敢忽视任何一个字,不敢乱说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田先生的严格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要求上,更多地表现在严于律己。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历史系和中古史中心任教,同时协助老师们做些杂事。我记得第一件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中心主任邓广铭先生编辑《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当时,由我来跑腿到各位先生家送校样、再取回来,同时担任校对工作。这个工作,让我领略了不同学者的不同治学风格,而田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是,一篇看上去相当完善的《北府兵始末》,他每次校样都反复修订。这篇文章我校读过数遍,是对我此后的研究和写作影响非常大的一篇史学论文。
田先生的学术研究,一向是我们年轻人的学习榜样,他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我们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听过一学期相关内容的课。就像周一良先生说听陈寅恪先生课的感觉,“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但田先生那时候身体不好,有时讲话中一口气上不来,却又呼之欲出,我们都屏住呼吸,静候下文,而他无论如何都会把这句话说完,因为这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段落。田先生的文章和他说话一样,有着严谨的逻辑思维,一环套一环,层层展开。我们读他的著作,也有同样的体验,就是一段开始,就不能释手,非要一口气看完不可。因为我对《北府兵始末》和《东晋门阀政治》从文笔到内容都至为佩服,所以现在给研究生上“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课的时候,我推荐给学生的范文,就是田先生的这两种论著,因为它们逻辑性强,且篇章合理,文字凝练。我觉得前者可以作为硕士论文安排篇章结构的参考,后者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模拟追求的典范。
田先生的著作以严谨著称,他的《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等等,无不如此。但田先生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有的成绩,仍然不断修订自己的作品。他大概觉得我比较注意海外汉学的成果,所以一次在他改订完一部著作时,特别和我说:他让学生查阅了我们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相关的外文图书,把和他论文相关的著作都拿来翻阅过了,包括我最近给中心的ScottPearce、Audrey Spiro和Patricia Ebrey编的Culture and Power in the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一书,因为没有什么特别要提到的,所以也就没有提这些论著。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得出田先生治学的严谨和认真。
田先生以长者风范,每出一书,都送我一册,修订本也是如此。我翻开手边的《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上面题写着:“旧著重订,聊作纪念。新江教授惠存。”在这本书的《重订本跋》中,田先生提到这个重订本有几类改动:一是调换文章,删掉已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后论的《论东晋门阀政治》,增补《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和《彭城刘氏与佛学成实论的传播》两文;二是增删和修改,交代了删改原则;三是更换文题或增设副题,“目的是与内容更贴切一些”。由此可见,田先生治学严谨之风格。
田先生这种严谨的风格,也贯穿到其他学术活动当中。记得他当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历史系要聘请京都大学谷川道雄先生担任客座教授,他让我准备一份他在聘任会上使用的发言稿,并向他报告谷川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为此把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能够找到的谷川先生的著作和散在杂志中的论文翻阅了一遍,有些做了提要,然后向他做了汇报。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听得出来,他也看了一些谷川先生的论著,对于他的“共同体理论”,有自己的看法。因此,虽然我给他准备了讲稿,但他在聘任会上发言时,并没有完全按照稿子来念,而是很严谨、恰当地评价了谷川先生对六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我听了以后,十分佩服。而和田先生讨论谷川先生的学术,我仿佛又回到研究生时期上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时那样,受益极多。
说田先生是一位和蔼的老师,是说他对年轻学子的成长,关怀备至。我1984年去荷兰莱顿大学进修只有十个月,走前他建议我,最好继续在那里读一个博士学位。在改革开放初的八十年代,几乎没有人认为学习中国历史也应该去国外念博士。我知道莱顿的导师许理和是欧洲最优秀的汉学家,但他那时已经基本上不怎么研究佛教征服中国史了,而热衷于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正在研究徐家汇的抄本文献。这些并非当时我的兴趣所在,所以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但这表明,那时候作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的他,具有超前的眼光和宽广的学术胸怀。
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和田先生的接触并不是非常多,但一有机会见面,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不要走偏路。记得有一次他晚饭后来我家串门,一聊就是两三个钟头,直到九点多他夫人来电话才离去。他的谆谆教导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让我在做学问的时候,一只脚要跨出去,一只脚要立足中原。
因为他知道我主攻方向是西域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外关系,所以希望我不能脱离中原本土的典籍、制度、文化,并举相关研究西域、敦煌吐鲁番的前辈学者,如冯承钧、唐长孺等先生来作为例子。
田先生的这番教导,我深以为是,一直牢记在心,所以也时常分出一些时间来研究隋唐史,并且在研究西域史地、中外关系、敦煌吐鲁番文书时,尽量发挥所把握的中原典籍、制度的知识,把中外学术打通。
我用节度使检校官制度,来讨论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并理出判别敦煌文献年代的一种方法,即是从制度着手来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归义军史;我近年来研究入华粟特人,也是要把他们合理地放在中原历史的脉络里去讨论,尽量不要犯“泛粟特化”的错误;我一直坚持与一批同道和学生做隋唐长安的研究,也是让自己不要离开中原。
所以,我曾把田先生的这番嘱咐,写在拙著《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一书的小序当中,奉为座右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