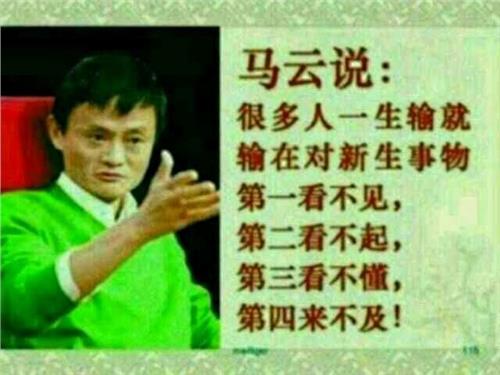大脑入侵已成现实 精神认知是否也受法律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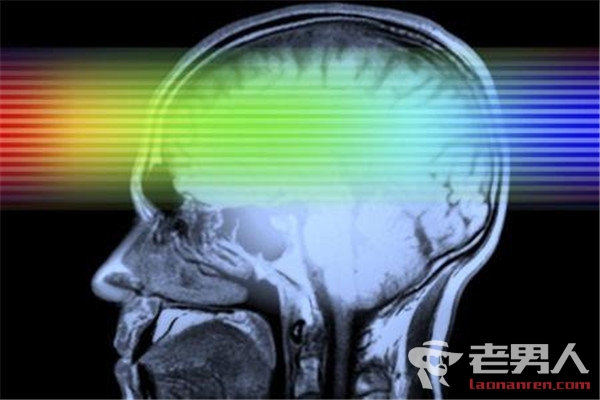
科技不断在发展和进步,据了解,大脑入侵已成现实,神经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的进步使得极其精确的观察、收集甚至改变人脑活动有了可能。
脑机接口和经颅磁刺激这类新兴认知工具可以给医学和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带来革命性的进展。然而,瑞士的生物伦理学家Marcello Ienca和Roberto Andorno表示,这些技术同时引发了一些关于人权的基本问题,需要增加对于人权的法律保护。
近期对这些问题表示出的关注非常有效且适当,但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引入这种权利的后果。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有意操纵自己的大脑和其他人的大脑。从咖啡因到冥想,甚至到广告,我们有许多法律上和社会上可接受的工具一直在试图改变人类的认知行为。当我们把其他药物,更可疑的道德行为和法律地位等列入时,这个工具名单必然会加长。
这些方法往往十分笨拙又难以衡量(市场营销先锋John Wanamaker这样总结到:“我花在广告上的资金浪费了一半,问题是我连浪费的是哪一半都不知道”),不过就算这样,我的工作也足以为继了。
我们很容易把历史上的,甚至当今的一些认知操作工具当作一种炼金术。但他们现在正逐渐让位于一个更具科学性和技术性的方法,控制早期认知操作形式的方法——主要是粗暴的监管与责骂——并不适于这个新的干预时代。

四项权利
因此,Ienca和Andorno提出了四项核心权利:认知自由(利用神经科技改变自己心理状态的权利);精神隐私(禁止未经允许他人读取其心理状态、结构和内容的权利);心理完整性(禁止未经允许改变他人精神状态、结构和内容的权利);心理连续性(禁止使用改变个性的神经工具的权利)。
简而言之,在确立了对自己的认知选择说“是”的权利之后,同时也可以归结为是对认知干预措施说“不”的权利。
这些权利已经面临各个方向的威胁,Facebook正尝试通过社会传染到新兴产业神经营销学来改变用户情绪。而且,尽管他们现在所做的努力还杂乱无章,但他们指向了具体的未来,他们有意改变个人思想,从而实现社会、政治或经济目标。
不过,Ienca和Andorno所提出的四项权利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其他问题。父母是否有权通过神经科技改变子女的心理状态吗?我们是否有权知道我们依靠的某个人——如老师,飞行员,总统或总理——使用了认知增强,还是拒绝了接受具有潜在用处的神经科技?
犯罪分子能否拥有这些基本权利?如果不能,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允许非自愿读取或改变罪犯大脑呢?社会是否有权授权那些可以带来显著社会效益的神经科技干预的使用(想象一下,也许能有一种针对恋童癖的神经科技“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