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的照片 北京人物(26)领军清史编纂的戴逸
几年前,笔者初次步入地处张自忠路北侧原段祺瑞执政府一座斑驳灰暗的哥特式旧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时,沧桑感油然而生,往昔的历史风云刹时掠过脑际。在一间四壁是书,只有一桌一椅,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办公楼里,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接待了我。
至今不能忘记的是,老人那满头银发,那浓重的常熟乡音,那亲切的目光和自始至终暖人的微笑。印象更深的是,一位学界大家对清史的一往情深,对启动清史编纂工作的热切企盼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不久前,笔者再次造访了戴逸先生。乡音依旧,微笑依旧,所不同的是,他已由“企盼”变成了“导演”——三年前,中央正式批准了清史编纂工作,他被委以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这项建国以来迄今最大的文化工程。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位七十九岁的老人,他一生的治学、研究、著述和追求,都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易代修史、盛世修书,是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以近六百年为例,曾有三次大的修史举动:第一次,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就开始编修《元史》;第二次,清代康熙盛世,编修《明史》;第三次,清朝垮台,北洋政府组织编修了《清史稿》。
但是,民国初年开始,历经十三载完成的这部《清史稿》,由于作者大多是满清遗老,他们对前朝怀有割舍不下的感情,留恋旧日岁月,不仅体例过时,观点陈腐,史实也多有谬说。编修一部崭新的清史,一直是人们的强烈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极为重视这项工作。董必武曾向中央建议要修两部书,一部是中共党史,一部是清史。毛泽东、周恩来也很重视这项工作。毛泽东在一次与范文澜的谈话中,说想多读点清史的书。周恩来曾找吴晗谈修清史问题,由他负责这件事。当时吴晗与戴逸一位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一位是编委,过从甚密,吴晗信心十足,他希望与戴逸一起为清史编修大干一场。
1965年秋,国务院正式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是七位委员之一。他是其中最年轻的。正当他落实具体筹备工作而紧张忙碌时,“文革”爆发,不得不中断。
197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明清史专家郭影秋的关心下,搭起清史研究小组的班子,戴逸满以为又可以继续中断多年的清史工作,“批林批孔”的闹剧又使这一愿望化为泡影。其实,即使没有“批林批孔”,在“文革”那种特定环境下,他怎么可能安下心做研究工作。
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成立清史研究所,戴逸才真正可以施展他的抱负和实现夙愿了。为了有一天清史编修工作,他从稳固清史研究所这个基地开始,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规划,细化研究项目,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多年来,戴逸先生一直呼吁编修清史,他著文《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提出编写清史的规划与设想。他组织领导的研究成果——十二卷本的《清史编年》、多卷本的《清代人物传稿》都是为清史编修做准备。
2000年,戴逸先生在《瞭望》杂志再次发表题为《编纂清史此其时矣》的文章,呼吁已到了编纂清史的时机。此时,不断有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或提出议案,或给中央写信,表达他们尽快编修一部清史的愿望。2002年8月,中央终于批准了这项世纪文化工程,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同志都做了批示。
戴逸先生被委以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这是众望所归,他的学养、声望、驾驭能力和人品都是无可挑剔的。在笔者谈到这一话题时,老人的表情由轻松的微笑立时变得凝重起来,他说:“我感谢领导和大家对我的信任,这是荣誉,更是责任,压力巨大。
多年的愿望一朝实现,自然兴奋、信心十足;真的开始实施,如履薄冰,恐怕出现闪失。必须拿出一部高质量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清史。”戴逸先生向笔者介绍了清史编纂的大致情况和目前进展。该文化工程计划用十年时间,到2012年全部完成。
规划92卷,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纪,第二部分典志,第三部分传记,第四部分史表,第五部分图录,共约三千万字。全书将全面、详尽、真实、生动反映满清入关前几十年和入关后清代社会268年的历史。全国各省(市)都有人参与这项工作,包括上千名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这部清史,将有不少特点和创新,一是要有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观照。将吸收外国人对清代社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二是增加过去没有的图录部分,而且这个比例占到10卷之多。把各种清代社会的绘画、图像、地图、照片收录进去。
如《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耕织图》……形象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起到文字难以起到的作用。曾国藩什么样子,李鸿章什么样子,都有了感性认识。清末照相技术已传入中国,将搜集20万张备选,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真容”呈现给读者。
当时的中国什么样子,北京什么样子,都会在地图中看到。三是过去史中人物只写官员,没有平民,这次要充分反映这些人物。戴逸举例说,“样子雷”就将写上一笔。
他家世代是杰出的建筑工匠,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颐和园等这些中国建筑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曾留下他们的智慧和业绩,这样的人应当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至于唱京剧的程长庚、谭鑫培等人也将写入清史。
对这部清史的“创新”和“特点”,戴逸先生还举了其他许多例子。
作为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这个“导演”真是殚精竭虑。他既要总体把握,又要细致入微,要组织协调各个环节,任何地方都不能出现疏漏。
为了完成高质量的清史,在第一阶段对总体框架的研究中,即在上海、北京、广州、沈阳、台北先后多次组织研究讨论,有700多人次。为了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他这个“导演”煞费苦心。有一位清史研究上很有建树、某个方面很有专长的老先生,戴逸一连给他写了几封信,他都没答应。
戴逸又亲自登门拜望,这位有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又很有个性的老先生被这种“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感动,放弃自己的课题,加入到清史编纂中。至于戴逸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更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团结在恩师周围,尽心尽力,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博士黄爱平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清史编纂已占据了戴逸先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他已无暇他顾。过去,工作之余,还不时下下围棋,而且是个业余高手,曾取得过老同志“炎黄杯”冠军和“陈毅杯”不错的名次。这些都不得不暂时放弃,只能留待清史编纂大功告成后再说了。
老伴和戴逸同在人民大学,但她是搞哲学的。退休后,除了承担起丈夫的全部衣食起居,还始终关注着丈夫的工作,有时她的“哲学点拨”,对戴逸不无启发。相濡以沫的老伴既担心丈夫日夜奔忙身体吃不消,又理解他工作的重要,最后也只能是一句“他一辈子对工作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戴逸先生是历史学家,尤谙清史,当前的工作又把他推上了事业的高峰。其实,他最初是学工的,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大。两年以后,挚爱文史的戴逸突然的机遇又考入了北大历史系。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戴逸才华横溢,成果丰硕,著作等身,但同时历经曲折。
1946年就读北大的戴逸,名师云集,胡适、贺麟、郑天挺、陈垣、邓广铭、梅晦、沈从文、朱光潜等文史哲大师都使他受益匪浅。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通缉。但他又是听课坐在第一排、考试经常考第一的“好学生”,胡适对他印象很深,也因此破例写了保释信。他最终离开北大,辗转进入解放区的华北大学。
1951年年仅25岁的戴逸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史学著作《中国抗战史演义》,经过广播电台联播,更产生了广泛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还不到而立之年,就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副教授。六十年代中期发表的《论清官》等文章受到周扬等人的赏识,也因此在“文革”中遭难。
谈起这些往事,戴逸先生是平和的,一如他的为人。我们相信,他主持编纂的清史一定会圆满完成。到那时,再回望先生这段经历,一定会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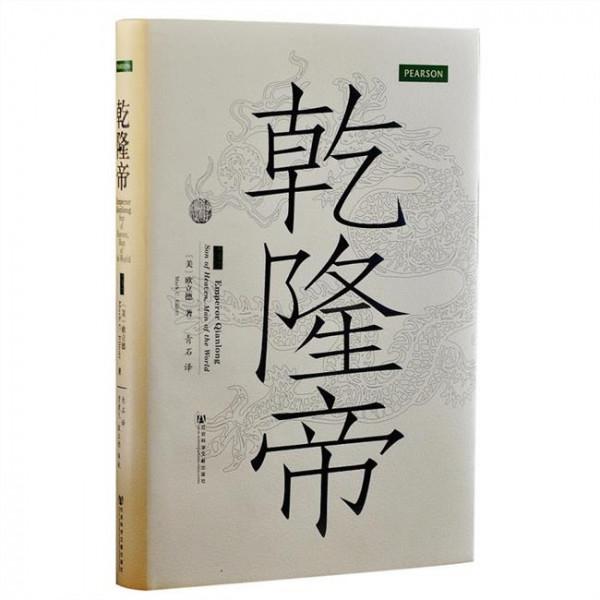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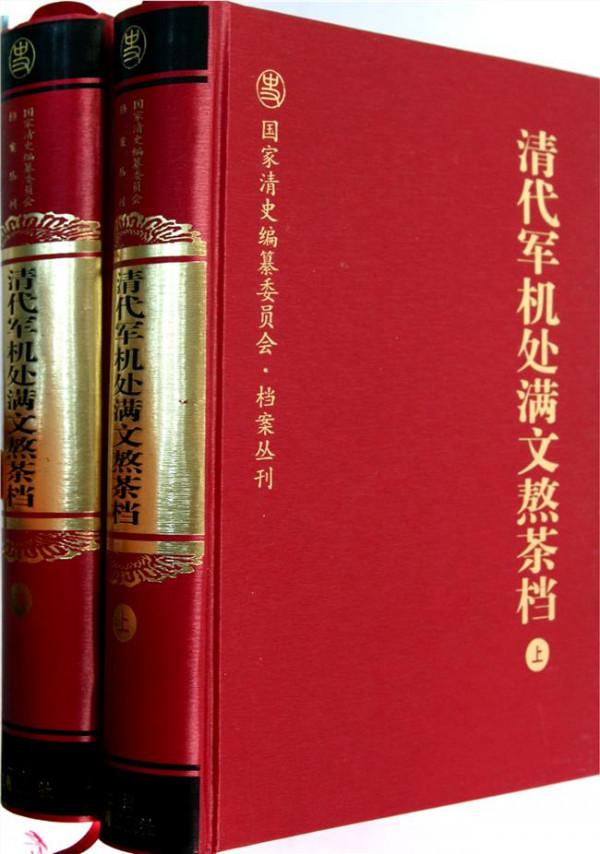


![>《戴郭邦水浒人物画谱》[压缩包]](https://pic.bilezu.com/upload/4/22/422fea39d728405ceb9e31efb717e8f7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