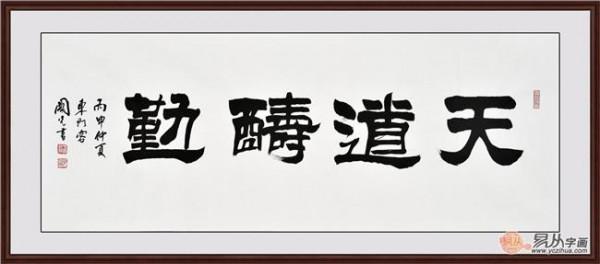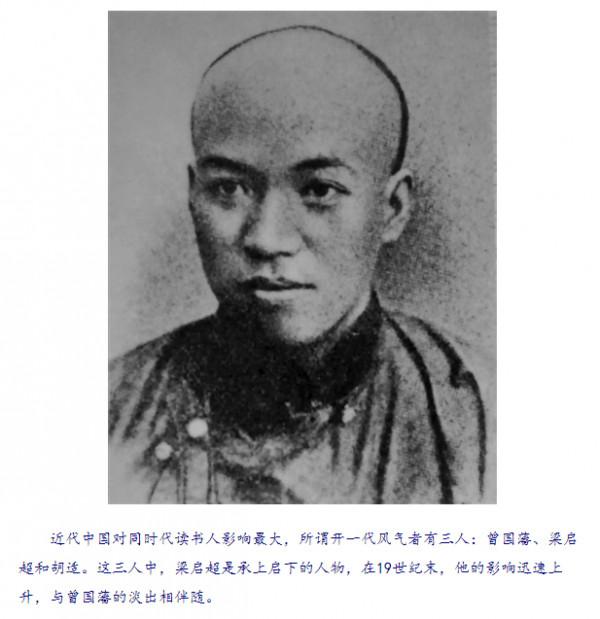杨振声五四运动 朱自清在五四运动中
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两方面,父亲对这两个方面都积极参加了,可以说,他在北大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还接受了一次准备把毕生奉献给祖国的思想洗礼。
当时的北大,确实出现了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蔡元培主持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陆续被聘来校后,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并提出种种改革的主张。
另一方面,也有辜鸿铭、梁漱溟、刘师培、陈汉章等公开表示对孔教的迷恋和卫护。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活跃的思想交锋,热烈的争鸣氛围,使父亲受到极大的启迪。他贪婪地从争辩双方汲取营养:既从胡适等新派老师那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思想和研究方法,也从旧派老师那里增进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但毕竟,新文化、新思想使他耳目一新。他从爱读佛学书籍,转而关注新文化,喜爱新文学。特别是胡适,在当时对他的影响较大,他上胡适的课也最多。
他虽然有较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底,能写很好的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骈文,但对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向之一,是始终坚持的,而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用白话文写出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歌和散文。
父亲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在“五四”前后他所创作的新诗中,以及后来的许多作品中,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不过,在思想文化上,他却并不完全赞同全盘西化的主张,而是赞同中西结合。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白话文写作方面,他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经过提炼的群众口语为基础,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所喜爱的、中国化的新鲜文风,而避免了当时流行的全盘“欧化”。
在学术方面,他更是对中西文化里优秀的进步的东西,都认真去学习和研究。
1919年2月,父亲从同学那里看到一张外国画片,画上一位母亲正抚爱着熟睡的婴儿,题为“Sleep Little One”。也许这幅画使他想起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出生不到半年的笔者的大哥,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首白话新诗《睡罢,小小的人》,来表示对新生命的挚爱和祝福,并于当年12月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
这是他最早的文学创作。以后一年多,他又陆续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新潮》上发表了多首新诗。
他一生的文学事业,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影响下开始的。他当时最爱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新潮》是1919年1月创刊的,由于它偏重文学,主办者康白情、徐彦之、谭平山、杨振声、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等又都是他的同学,对他从事文学事业似乎更有直接影响。1920年春天,也可能是1919年底,他和冯友兰等一道或先或后加入了新潮社。
经过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北大学生,摆脱了只关心个人前途的狭隘眼界,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但当他们睁开眼睛来时,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列强环伺、忧患频仍、疮痍满目、危机四伏的祖国;和一个魑魅横行、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不能不激起民族解放意识的强烈高涨。在当时那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救亡正是启蒙的必然结果和合理延伸,而不是与启蒙相对立的。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父亲参加了当天的集会游行,和大家一道激昂地挥小旗,呼口号。过后,又跟数千名北大同学一道,为要求释放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时被军阀政府拘捕的许德珩、杨振声、潘菽、江绍原等32位同学而奔走呼号。
他历来惜时如金,1919年1月以前绝少请假,更无旷课,但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文本科学生请假旷课表”,自2月间北京部分学生筹议抵抗“巴黎和会”后,连续几个月,他的请假次数明显增多,而且月月出现了旷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情。他生前曾对母亲说过,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他曾在它的一个股中工作。
父亲还在这年暑假后参加了曾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2月,该团分组有变动,父亲被分在第四组;次年3月,随着邓中夏重新当选为总务干事,父亲也被选为第四组书记。第四组共13人,他担任书记后,就按邓中夏的安排,首先组织大家到通县从事农村讲演。
据《北京大学日刊》载:这次听讲的有500余人,“结果甚为圆满”。父亲上下午各讲一次,题目是“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之后,他又按照每个团员每月须出讲两次的要求,组织第四组的团员到北京四城讲演。
他讲过“我们为什么要求知识?”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等题目,并组织第四组的其他团员讲过“山东之危机”、“救国方法”、“国耻纪念日”等,继续宣扬“五四”精神。直到五月,他毕业南归,才辞去这一工作。
父亲为人一贯朴讷。以他的性格,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中担当冲锋陷阵的先锋角色,但他却自觉自愿地、积极活跃地跟随当时的先驱者,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尽了一个爱国者应尽的责任。他是五四运动中的普通一兵,但却是主动有为的普通一兵。
父亲本不爱说话。“五四”前,他跟杨晦同坐一张课桌,彼此却很少交谈。是五四运动打破了同学间的界限,使他跟杨振声、杨晦等都建立了长久的友谊。他还同当时已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北大同学邓中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虽然不能像他们那样,把全副身心投入革命,最终成为职业革命家,但绝不排斥他们,嫉视他们,而是钦佩和尊敬他们,爱护他们。1920年1月他写的一首诗里,描写了自己在北河沿读预科时,夜里,从小河边斑驳的树影中望去,城墙上一行灯光带来了光明的感觉。他含蓄地把这些革命先驱者比作“北河沿的路灯”:
他们怎样微弱! 但却是我们唯一的慧眼! 他们帮着我们了解自然; 让我们看出前途坦坦。 他们是好朋友, 给我们希望和慰安。 祝福你灯光们, 愿你们永久而无限!
五四运动使父亲的心年轻起来了。在他1919年11月到1920年3月写的新诗里,出现了不让“生命给的欢乐”被夺去,“笑里充满了自由”的小鸟;出现了让人们“自己去造”光明的上帝和“仿佛充满了光明”的歌声;出现了“一色内外清莹,再不见纤毫翳障”的月光;出现了在火中跳起舞来,“全是赤和热”的煤;出现了在阳光、在浓浓的春意中苏醒了的小草。
总之,五四运动所唤起的民族的觉醒,使他一度摆脱了彷徨,在黑暗中又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觉得自己“波澜汹涌的心,像古井般平静;可是一些没冷,还深深地含着缕缕微温”。
这些诗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新潮》上发表后,也鼓舞了别人。在五四运动中有这种感受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这也说明他的白话新诗,从一开始就不是唯美主义的,而是来自现实、紧贴现实和“为人生”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新诗才能在我国早期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加五四运动,对父亲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还是爱国主义。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虽然是他后来说的;但这“理想”和“完美”,从他一生的实际追求来看,包含有“民主”和“科学”的重要内容,也包含有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迫切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