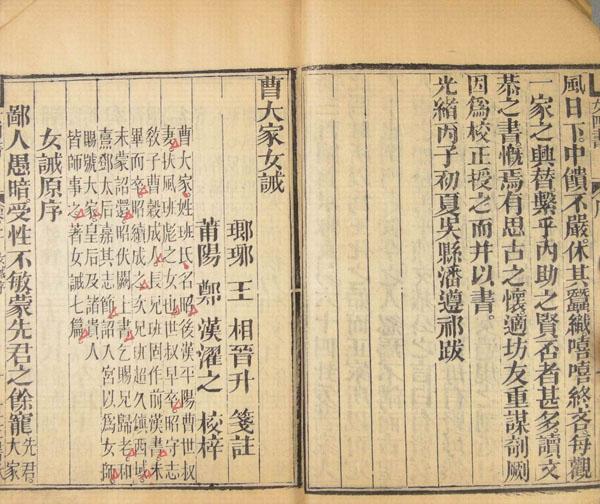杨念群的父亲 杨念群: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关键是群己界限
2013年1月9日,在梁启超《新民说》创作110周年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主题文化沙龙。以下文字来自于主题演讲。
什么叫关键?就是破局。局是破不了,因为现在都是迷局,不可能一下子破。什么是关键也是见仁见智,每个人对近代思想和近代历史演变都有自己的思考路线和选择,什么是关键也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就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如果联系到“新民”这个标题的话,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关键是群己界限的问题,就是自我跟一个群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群己的界限是怎么划的,这个不能说是最终的关键,但可能是关键之一。
这是我自己对这次命题作文,所谓破局也好,所谓什么是关键也好,什么是中国现代叙事的第一义也好,但是我想不一定是第一义,但是其中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义之一。我先把这个话题抛出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什么叫群己界限?群己界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在近代,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就是王权的倒塌,作为一个王朝,通过辛亥革命,大清帝国的覆灭,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点。我们现在非常清楚,一个王朝转变到民国,再转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这个历史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用倒推电影的方法回到当时的情境,让自己出生在大清灭亡的关键年份,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并不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破局的问题,这个局并没有破,包括到现在也没有破,在那时候更加不清楚,因为皇权突然倒塌,皇帝不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子,自己跟旁人的关系、自己跟国家的关系、自己跟帝国的关系、自己跟皇帝的关系,通通都是一锅粥,这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为什么刚才王老师说民国初年到最后大家认为还不如大清,就是因为那时候太乱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布这个局。
认同的基点是什么?“皇帝”是什么?
在回到群己界限的问题上,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让大家困惑的问题就是,一个大的帝国或者一个满清王朝倒塌之后,我们最终的认同基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认同什么样的东西不清楚。下午大家议论了很多关于人民的问题,后来吴稼祥老师说人民就是一个根本兑换不了的支票。
确实如此,大清帝国覆灭之后,“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根本不成立,因为我们原来习惯的是在皇帝的统摄之下的大一统的疆域之下生活,大清帝国覆灭、这个局倒塌之后怎么立局非常不清楚。
因为现在大家觉得皇帝倒塌,是不是真正的当家作主,这个要打问号,至少我们习惯在口号上这样理解;但是在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皇帝倒塌的之后是什么,真是手足无措。因为皇帝在传统的政治格局里,不仅仅是皇位的问题,实际上是凝聚所有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符号,也就是说,皇帝本身最不重要,他是肉身,这个位置最重要,他是凝聚的符号。
在他的统摄之下,包括疆域,包括思想、政治和经济格局、社会的变化,都在皇帝这个招牌底下实施,但是皇帝一旦倒塌之后、王权倒塌之后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我们失去了一种认同。
那么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说把皇帝留着,所以当时很多立宪派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占有优势,因为革命的后果是不可知的。你把皇帝打倒之后,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当时杨度先生有一个话,政体比国体更加重要,就是留一个国体、留一个皇帝,但是政体是一个宪政的制度,这个是不是可行?当然他考虑的是,如果把皇帝推倒之后,所有的这些符号全部倒塌,我们难以凝聚起大一统的疆域,必然是分崩离析的,所以这个皇帝可能是最重要的凝聚点,皇帝本身不重要,但是他作为文化符号的重要性是存在的。
所以当时所谓的立宪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
科举与身份
但这里面,到最后这个出发点被打破了,通过革命,最后皇帝没有了,皇帝没有之后就涉及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认同什么。原来是天高皇帝远,但是往下走有一系列制度去维持这个运转,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科举。大家不要以为科举制度是考试制度,我从来不把科举认为考试制度,它实际上是一个身份分配的制度。
官员进入到科举渠道之后,他可能在上层、中层或下层,科举制度把所有的官员分配到不同阶层,起到所谓政教教化的作用。政治是靠科举制度人员安排和身份安排来建立起整个网络。
科举制度一旦打破之后,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也就是说,政教关系的体系彻底崩解,崩解之后大家可以身份有所转换,但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点是什么?一个是身份分配,一个是把上层的政治跟下层的政治和社会加以沟通。
下层的政治是什么?宗族,地方的自治。上层是什么?基本是内阁、阁员,所谓的皇权体制之下的层面。科举制度给予官员一个身份安排,你要是中了举人可以当县长,中了进士可以进翰林院当大官,你中了秀才,你在底层可以成为士绅阶级,成为士绅阶级之后可以在地方基层形成地方社会,他可以控制这个地方社会,通过教化、通过修桥铺路、通过政绩把地方自治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基层等级。
上层自然有它的一系列的等级。而且这个科举制度可以流动,它没有固定的阶层,你如果是一个大官,退休之后到了家乡,同样成为士绅。曾国藩就是这样,回到家乡之后,他可以布衣领军,他那时候已经卸掉官职,他抵挡太平军那么多年,等于救了大清半壁江山,他就是从科举制流动沉到底层变为士绅阶层的。
国家破坏论?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科举制是皇帝倒塌之前就已经被撤销了的,但是皇帝消灭之后,这套系统处于瓦解状态。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刚才所说的群己界限问题:我们作为个人,我们认同什么。现在皇帝没有了,第一个认同被杀掉了。
地方社会没有了,因为没有科举制了,没有士绅阶层了,所有士绅阶层转换成所谓的学堂学生。学堂学生是什么概念?学堂全都是行政的技术官僚的大本营,学堂学生是一个技术官僚,但是他不承担起道德的教化的在基层自治的责任,学堂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说,第一,皇帝认同去掉,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科举制没有了,我们还能认同什么?唯一的认同就是国家,现代国家。下午很多老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包括梁治平教授谈到国家主义的问题。
原来天高皇帝远,我们知道有一个皇帝在,现在皇帝没有了,地方社会没有了,我们还能认同什么?就是认同一个国家。当然对于这个国家,任公先生曾经在《新民说》之前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他原来是认同这个国家的,就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取代了清王朝之后,才能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他的新史学也很好,新史学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培养国民,我们所有的史学都是为培养国民而存在的,他这个用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点,到底这个现代国家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被建立起来,当时不清楚,所以就引起民初一个最大的波澜,我们知道是国家破坏论——通过政党政治建立现代宪政基础,彻底替代清王朝,但是结果是军阀混战,大家轮流做庄,谁有钱、谁有权、谁有军队就可以。
后来陈独秀先生在五四之前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国家破坏论》,他把国家偶像整个打破,他说国家这个东西太糟糕,我们不要搞国家。后来我们知道任公先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后期他向文化转变,很多人也都在讨论文化问题,我们怎么新民,怎么把自己的素质提高。
重新认同: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
还有一条线非常重要,叫做无政府主义。早期的共产党人中很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彻底失望,在上层建立宪政和建立民主政治的梦彻底破灭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无政府,我们重新界定这个群己界限在什么地方,不应该在现代国家的层面,应该是在社会的层面上。
如何建立这个社会,建立基层的组织,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到了这个阶段,无政府主义大兴,毛泽东跑到岳麓山搭个小帐篷,耕几块地、养几只鸡,就是这么做的。整个基层组织的过程被认为是重新认同,建立现代社会、现代群己界限过程中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运动很快又破灭掉,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建立乌托邦社会,那是多么可笑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个东西破灭之后,转入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波动,最后就走向革命。革命是一个不断被激进化、被车轮不断滚动往前走的无法阻止的过程,就是因为大家尝试的各种各样的群己界限无法界定,其造成必然的后果,就是政党介入之后,替代了国家的认同,变成了一个党国体系。
国民党那时候也是党国体系,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逐渐变成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五四的时候非常自由,大家可以有多种选择,你可以到香山那边搞一块地自己玩一玩,那时候人们可以有多种职业选择,你的身份、面目可以不断变化,政治的、文化的。但是到了最后,变成非黑即白,包括现在的争论也是那时候的遗毒,什么新左派、自由主义,反正你不是左派就是自由主义,怎么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呢?
当然儒者突然出现了,即第三条道路,秋风先生原来是自由主义者,他可能要走第三条道路,我希望有第四条、第五条道路,最终归结都是群己界限认同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组织,都在这样的脉络里面。
但是我个人认为,革命本身是有问题的,在这点上我是一个“反革命者”。革命是造成最终灾难的最重要的一点。因为通过革命的手段所造成的所谓民主的一些制度完全是不可及的,所以新左派有时候为“文革”辩护,说“文革”就是大民主,大家参与,随便想骂谁骂谁,把老子揍一通也没人管,这是民主吗?民主是一个绝对的群己界限,要严格区分的。
首先你要有私德,跟公德界限非常分明的。所以公民社会是私德和公德之间界限分明的状态,当然这个谈起来太复杂,而且我们右边就是宪政专家,我不从这个角度来谈。
但是民主本身的建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是动员式的。我们所谓民主,人民群众表面是参与了整个运动,但是所有运动都是伟大领袖支配下的运动。人民群众,人民本身,没有表达自己渠道的任何权利,整个社会没有人民真正发声的渠道和途径,在某种意义上根本建立不起来新的群己界限。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什么是关键:重建“群己界限”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谈到“什么是关键”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建自己的群己界限,当然这个群己界限有很多途径,秋风在边上,这一点我跟他可能会有共鸣。当然我不同意他说的“新就是旧”,但是有一点,旧的很多东西,特别是体制那样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通过创新机制达到群己界限的重新界定,比如政教关系,我不是说科举制度一定好,我不是为它辩护,科举制度有时候很烂,比如说八股文,但是在建立政教关系的上下层、分层制度上,科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如果我们要想恢复我们真正的认同和群己界限的话,在基层的社会里建立起我们真正的政教关系的体系,显得更加重要。否则,我们所有的信仰、所有的认同,我们无所着地。所以我想,我们所谓“破局”也好,所谓“关键”也好,我们应该是在这样一个状态点去寻找真正的新民的出路。
杨念群:著名历史学者,杨度曾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杨念群自选集》、《再造“病人”》、《何处是“江南”》等多种著作,主持《新史学》丛刊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