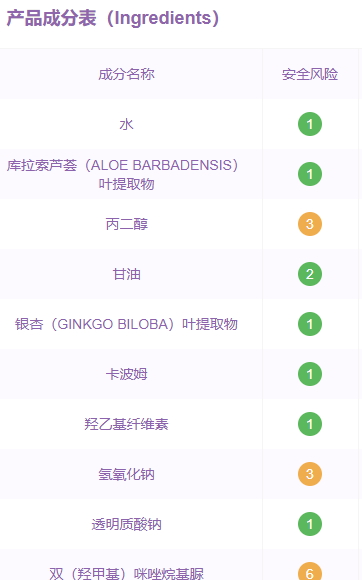高鹏程:胡弦《寻墨记》在寻找什么
文化史学者,艺术理论家余秋雨在他早期著作《文化苦旅》中提到,他一直有个心愿,想深入探寻一次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但却迟迟无法诉诸笔端。因为面对体量庞大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
但思忖良久后,他还是欣然落笔。他找到了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的文化符号——一副笔墨。虽然笔与墨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文化精神、意味和倾向性。但是,它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传统文化的世界。余秋雨由此写下了他的名篇《笔墨祭》,完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人一种心理习惯的深入探究。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不是散文《笔墨祭》,而是长诗《寻墨记》。它同样面对的是烟波浩渺的传统文化,同样把焦距对准了它的一个显著的符号—— 一锭漆黑、沉默的墨块。那么,面对烟岚缭绕、水汽淋漓的传统文化,《寻墨记》要寻找什么,诗人胡弦会用他怎样的生花妙笔另辟蹊径,探幽触微,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盛宴?
且让我们跟随胡弦走进他的《寻墨记》。
在由11个章节组成的长诗《寻墨记》里,第一节显然是一节"定调"之章。
光线腐烂后,另外的知觉从内部 将它撑满。
长诗起句,用了一个包含多重悬念的肯定句式,为读者带来了一连串的疑问:这里的光线是指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的光源在哪里?光线为什么会腐烂?另外的知觉又指什么?它在什么内部?它为什么能将它撑满?
开篇之处,强烈的悬念让人不由自主陷入了某种迷局。也激发了读者为寻找答案迫切的阅读欲望。
当胶质有所觉悟,又有许多人逝去了。
这里,胡弦有意使用了一个关键词:胶质。一方面暗示出了他所抒写的对象——墨块。另外当他从墨块中剔出胶质这个词,更大的用意在于,他已经洞悉了胶质对于一块墨的意义。它是墨得以凝结成块的关键性的物质。它的凝滞,黏连又是影响发墨和书写的原因。而当他赋予墨更多的象征寓意时,胶质一词包含的意味同样开始变得丰富。而它的觉悟又是什么?作者并不急于揭示出答案。而是继续向前,去呈现觉悟后的结果:
浩渺黑暗,涌向凸起的寂静喉结……
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浩渺的黑暗里,谁试图发声,它将发出怎样的声音?当黑暗的一部分也忍受不住如此长久和浩渺的黑暗试图发声时,它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声音?
——傍晚,当我们返回,新墨既成,那么黑如同 深深的遗忘。
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来解读。第一,它从形式上对应了长诗的小标题,这是一首借以和X谈话而开始抒写的长诗。X是谁?作者也没有交代。我们自然可以有多重理解,它可能是作者现实中的某个朋友(这在诗中后面的一些章节同样还有涉及),也可以认为这只是作者的一种书写策略。
X,往往有着不确定的指代,也许就是很多人。这样的一种书写策略,可以使诗意情境和日常描述自然契合,使诗人在现实语境与内心镜像之间自由穿插。同时,这一句还从内容上回应了长诗的正题《寻墨记》,是的,《寻墨记》寻找的就是一种黑,就是如同深深的遗忘的一种黑。
读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约略回头再审视一下我们阅读中那些悬念。尽管依旧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里的光线,肯定是曾经烛照过墨的光线,烛照过这一块墨所寓指的某种黑的光线。但是它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腐烂,消失。因此,我们的寻找不是从外而内的寻找,而是借助那一团墨,一团黑从它内部获得的知觉,从它寂静的欲说还休的喉结里去探寻我们所遗忘的东西。细读这一节,我们不难发现,胶质是作为"另外的知觉"的对应物存在的,胶质是凝结的话,另外的知觉就是撑开,就是打开一块墨内部空间的力量,基于此,我们对于作者所提到的"另外的知觉"已经可以约略忖度出它的喻指。
本雅明说,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反对着它自己最终的目标,因此,天堂的神灵的踪迹就能够在它自己的彻底的对立面中被发现——在无尽的灾难中它是世俗性的,被称之为进步的风暴从天堂吹来。这句话用在这里,也是恰当的。当外部的光线消失,我们不妨从墨的内部入手,借着另外的知觉为我们撑开的空间,去探寻墨的本性,探寻那被我们所遗忘的美与救赎。
诗歌由此开始进入。
在长诗的第二节,胡弦没有继续去探究这一锭模块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知觉以及它的黑里面究竟包含着怎样的遗忘,而是写到了四个与墨为伴的人。
我熟知四个与墨为伴的人: 第一个是盲者,他认为,将万物 存放于他的理解力中是正确的,因为不会被染黑。 他对研墨的看法:无用,但那是所有的手 需要穿越的迷宫。 第二个说:"唯有在墨中才知道, 另一个人还活着。
"说完,他的脸 就黑下来,出现在皇帝、美人、佞臣们身边。 在那里,墨成为色彩存在的依据。 第三个刚从殡仪馆回来,一言不发且带着 墨的气味、寒冷,和尊严。 第四个在书写,在倾听 一张白纸的空旷,和那纸对空旷感的处理。 他告知打探消息的人:事情 比外界所知的更加离奇,但所有 亲临现场者都要保守秘密, 因为这是结局。
这四个人,胡弦并没有给出他们明确的身份。但通过他富有意味的描述,我们不难有自己的判断。其中的盲者,是和墨有着某一种同等属性的人。是能够理解墨中之黑的人。也是对于墨的意义持消极态度的人。这让我想起传统文化中的老子代表的道家的观点。
在他看来,用黑来处理黑,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作用是穿越迷宫或者抵达宁静。而第二种人,和盲者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试图从墨中获取意义的人。或者说,这是胡弦在利用某种人声音在试图为我们探求墨中蕴含的意义。
至少在他看来,墨是色彩存在的依据。无论色彩存在于墨中或者恰恰应为墨的映衬使得色彩变得更加清晰可辨。在我的解读中,我愿意把他看成一个代表正义、道德力量的裁决者,或者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人的形象,一个相信墨迹、文字的力量但似乎并不得意的文人形象。
我甚至想到了李白。第三种,用一个经历生死的人的形象,暗示出墨的另一种意义,在死亡面前,在"生"的意义终结的地方,墨同样也应该有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第四个人,应该是一个洞悉了墨和书写的终极意义的人。是的,他洞悉了墨这样一种文化符号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或者更大层面上事物发展规律和最终结局——一张白纸的空旷。也明白这结局的不可言说。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去细究胡弦设立的这四个与墨相伴的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具体定位。也许他的确有着现实中某四个人的影子,但出现在这样的一首诗里,它也就天然地具备了一种形而上的隐喻意义,这也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它区别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当然更区别于划界谨严的学术著作。
它用形象说话,在语言的能指何所指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作为诗人的胡弦当然深谙诗歌语言的奥义,他的用意当然并不在于为我们严格界定对于墨不同看法和态度的四种人,而是通过四种与墨息息相关的角色,完成对于墨,对于墨中之黑意义的概括性的探究。
但他一开始似乎就陷入了某种吊诡的悖论,他试图探询墨中隐含的意义,但也预知了这种探求最后的真相——一张白纸的空旷。
那么,接下来的探究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相对结局的空无,或许,它存在于某种过程与变化中?那么,该从哪里找到路径去进入一块沉默墨块的内部,进入它那漆黑外表下的斑斓世界去探求那些在过程和变化中的意义呢?
长诗的第三节,印证了我们的阅读猜测。是的,所有事物的意义,并不是固定存在的,而确乎存在于某种变化中。在这一节里,胡弦借助对一张太极图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观点的佐证。
那年在徽州,对着一个硕大的太极图,你说, 那两条鱼其实是 同一条。一条,不过是另一条在内心 对自己的诘问。 ——但不需要波浪。正是与水有关的念头 在导致感官的疯狂。
同样,在我们对一块陈年的墨进行探究的时候,也是与黑有关的念头,在导致我们思考的艰涩。
"……如果已醒来, 它就不再完全像一个物体。"
是的,当历经长久的时空变迁之后,即就是一块墨恢复了内部的知觉,但是,外部的光线已经腐烂,时过境迁,我们已经无法再去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审视它了。
这一观点,也正如余秋雨在《笔墨祭》中所言: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其中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在他看来,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因此,对于某种文化符号意义的探知,有时候必须要回到这种文化符号所依附的整体性背景中去。胡弦无疑也在此获得了顿悟,在从太极图的黑白转换、互生互化、周流不息的玄机中看到了这种存在于流转变化中的意义,存在于墨色中某种更深更黑的东西。
同时,正如本雅明指出的那样:悲剧的空洞的、石化的对象,它的意义已经流失,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就像商品一样,仅仅在空虚的、同质性的时间中作永恒的重复。这种无活力的面貌,分裂为最小单位的风景,不得不在寓言化符号、已死的文字或者没有生命的手稿中第二次具体化。
寓言家能在废墟中挖掘曾经相联系的意义,用一种惊人的新的方式来处理它们。神秘的内在性得到净化,寓言的指涉物能被修复为适宜于多样性的使用和阅读。
我想胡弦也是熟知这个道理。在接下来的第四节和第五节诗行中。胡弦为我们设置了两个截然不用的文化背景。第四节,为我们重构了一副中国古典文化的经典氛围:庭院古老,红梅绽放,稍显颓废的文人倚窗望远,窗外是郊原的空濛。窗内是残卷、药香。而闭上眼,神思中依旧是游丝般的音乐,薄如蝉翼的爱人……而一锭墨,在这样的语境中,自然能够幻化出它难以名状的销魂的色泽和美感。
而当这样的背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时空之后,一切都已变得光怪陆离。难以言喻。在长诗的第五节,胡弦把我们的实现从烟雨空蒙的传统文化场景拉回了荒诞的现实情境。在一个特定的特殊年代对文化中的某种黑的成分,进行了了盘诘和追问。
长诗第五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胡弦在此用对"X"倾诉的方式,回顾了当年求学时对于墨的使用。年轻学子怀揣庶愿,是试图用多种方式甚至利用艺术跨界的方式去探求墨的意义。事实上他探求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某种结合的可能性,但是,结果并不容乐观,在失去传统文化整体性背景之后,对墨的意义的探寻已经如同猜谜,变得扑朔迷离:"多年前我们在南京求学,那时,对墨的使用如同猜谜。
"而且更吊诡的是:"即便偶尔猜到谜底,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又会抽身离去。"
接下来的诗行中,胡弦把这种探寻转向了更为荒诞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文革背景中去考察。我们知道,十年文革,不光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浩劫,也是对世道人心的一次摧残,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的破坏。胡弦再次为我们设置了两个猜谜人:
一个满头白发,端坐,不为谜面上堆积的狂热所动; 另一个善于隐形,所有人都走了他才重新回来……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位一位是传统文化的旗帜鲜明的坚守者和维护着,另一位则是失语者。或者说,他们分别代表了传统文化里的仁者和智者的形象。我们无法判定对于我们一度敝帚自珍的传统文化,在遇到这样荒诞不堪的现实境遇时,到底是哪一种态度更为合理有效。但有一点值得肯定:
"没有幽灵做不到的事,只是你 要保持耐心。"
是的,当一种文化强大到成为一种传统,它自身便具有了强大的自我生存、繁殖和延续的能量。"六和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长久以来,中国文化似乎一直被限定在一个封闭性的类似于太极图的圆中。不关心六和之外的存在。
儒释道都是闭合的圈子,都是在自足中存在。都不需要外在的补充。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是惊人的,尽管这种自足和闭合阻碍了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导致了文化的单一性。但是也同时使它具备了沿着自身轨迹运行的并能自我修复完善的可能。
长诗的第六节,胡弦再次将眼光移向了浩瀚的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去观察,去寻求它生生不息的脉搏的搏动。他发现,苍茫的江河两岸,河网始终密布,始终有人泛舟其上,带有墨痕的河流和梦境从未断流,始终在缓慢更新……而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些,如果我们认为自身能够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的确连失控的明月也不配做伴侣。
"某种存在不可再问及,它已 脱离命运的钳制,比如被命名为追忆的想象……" ——那是被虚构出来的空间,并且, 那空间已自作主张。
是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哪怕在现实中,适合它生存的背景荡然无存,它依旧可以存在于我们的追忆和想象中,而且在追忆和想象的空间里,它依旧能够自作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事实上这也的确是每一个有艺术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割舍的东西。写作《笔墨祭》时的余秋雨无疑是冷静的:"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