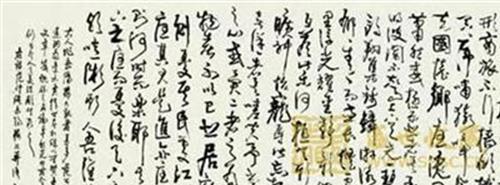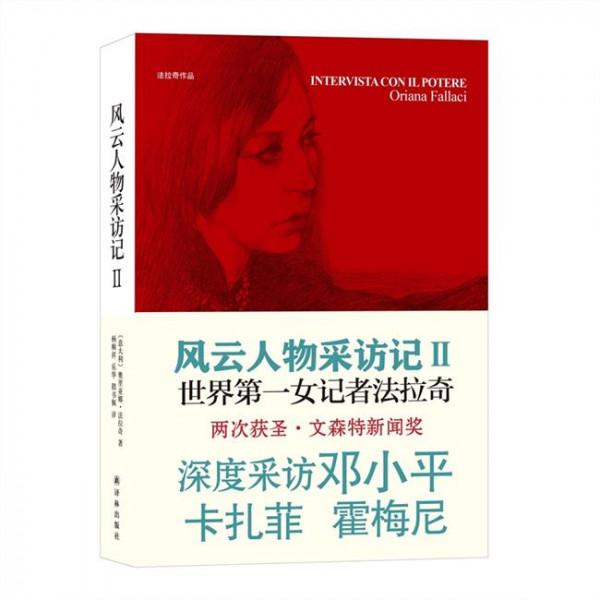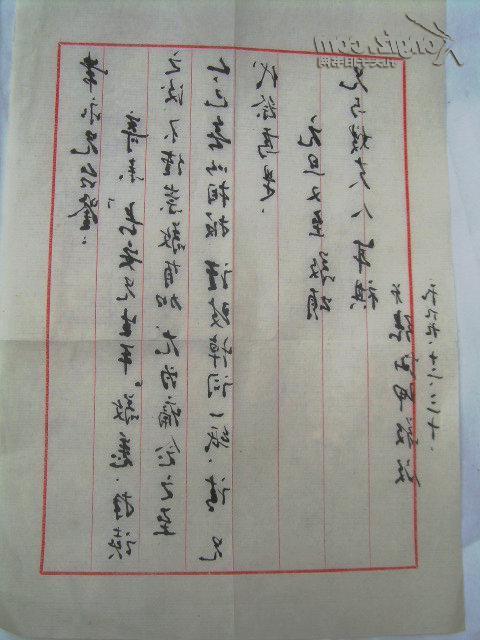法拉奇的采访记录 法拉奇给风云人物采访记写的序言
这个憎恨权力的女人,一生中却采访了那么多当权派,以及,她的出名,也直接和采访这群当权派有关。也许,诚如法拉奇所说,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智慧、强大和理智,但,他们有勇气有魄力有权谋,然后权力就被抓走了。
——————————————————华丽的分割线——————————————————— 我编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它成为当代26位政治名流的历史的直接见证,成为一部新闻报道的集子或历史文献。
但我不希望它论文一本仅供那些研究权力之争的学者们阅读的采访集。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作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我进行每一次采访都费了心血,像对待那些与我利害攸关,我必须态度明朗的事情那样去关注我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我对每件事情都根据我所持的道德标准明确表态)。
我不是带着像解剖学家或记者所持的超然态度去会见这26位大人物的。我去见他们时往往情绪激动并带去了一连串问题。
这些问题,我在访问他们之前总是先向自己提出。我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要弄明白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几个人? 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也永远没有人能解答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因为每一个答案的本身都包含着矛盾。
难怪很多人妥协了,他们说:历史是由所有人和个别人创造的,个别人成了领袖,因为他们生得逢时,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时机。也许是这样。但是那些不愿为生活中荒唐的悲剧所欺骗的人宁可相信帕斯卡的话:“如果克委巴特拉的鼻子当时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成为另一个样子。
”他们宁可信奉伯特兰•罗素所信奉和所写的:“随它去吧,世界上发生的事由不得你,而是取决于赫鲁晓夫先生,毛泽东先生,杜勒斯先生。
要是他们说‘你们去死’,我们就得死;如果他们说‘你们活下去’,我们就得活下去。”我无法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总之,我无法否认我们的生存是由少数人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幻想和反复无常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能动性和意愿决定的。
这些少数人,通过他们的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甚至一个简单的行动或对某个暴君的谋杀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和大多数人的命运。 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假设,这种观点触犯人的尊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是一群在时而高贵时而卑贱的牧人手中的绵羊?还是一批充当配角的货色或是一片飘零的落叶?为了否定这个假设也许得信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历史是由人民通过阶级斗争创造的。
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现实生活并不能肯定这种观点。你会反驳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人能证明,如果马克思不诞生或马克思不写资本论,约翰•史密斯或马里奥•罗西会写资本论)。
于是,你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这样的转折而不是那样的转折的是少数人;使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是少数人;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都来自少数人;谋杀暴君的也是少数人。
你不禁不安地自问,这些少数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坚强,比我们明智,比我们有胆量吗?或者他们既不比我们好,也不比我们坏,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一些不值得我们钦佩也不值得我们生气和嫉妒的普普通通的人?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过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只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那一套。
谁能保证学校没有给我们灌输谎言?谁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萨珊、凯撒和斯巴达克为人真诚的确凿证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战绩,而对他们的人品、弱点、谎言、理性和道德却一无所知。
我们手中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维琴盖托里克是坏蛋。
我们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头发是金黄色的还是褐色的,受过教育还是大老粗,是否与玛丽亚•玛达雷娜同过床;不知道圣路卡、圣马太、圣马可、圣约翰关于耶稣的传说是否真实。啊,要是有谁用录音机采访过他,记录了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
啊,要是有人把圣女贞德在审讯中和在被烧死前的话速记下来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我对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晚、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
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 今天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人们可以在采访时对控制着世界和改变其进程的少数人照相,拍电影,录音;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马上加以报道,加以说明,并进行热烈的讨论。
为此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其他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
理会到这一点后,很自然地会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是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
我说我每进行一次采访都花了心血,这并不言过其实。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接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
要是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本书就这样在7年中编成。7年中,我为“欧洲”周刊作了26此采访。我本着这种精神去访问我所要会见的人物,即:除了获取新闻外,每次访问都力求弄清这些人物与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约见他们经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们几乎总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来回答我的请求(实际上本书中的26个人并不是我希望会见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上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时间。
当我终于见到他们时,我就得千方百计地延长会见的时间。一旦见到了他们,便真相大白。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
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地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获得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并继续在斗争着的人。
至于那些在某个方面使我喜欢并对我有吸引力的人,坦白地说,我思想上对他们是有保留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信任他们,因而我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更不能把他们当作同路人。
也许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它能使某些男男女女意识到自己有权利或感到他人授予这种权利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
无论是暴君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无论是刽子手将军还是受人热爱的领袖,我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也许我错了,但是人间乐园并不是在上帝告知亚当和夏娃将劳累终生和备受分娩的痛苦的那一天消失的。
人间乐园是在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存在一位不允许他们吃苹果的主人,并在他们为了一个苹果被驱逐出家园之后不得不在星期五禁止吃肉的部落里当首领的时候消失的。
是的,在有人群的地方需要有管辖人群的人,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但是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需要有管辖他们的人,需要一个头目。没有人知道这个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
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以为它真的存在而去追求它,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感到有责任告诉读者,我坚信苹果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
我更有责任让读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的同时,我却理解那些反对、前者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
我把反对暴君看做是对人的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好利用;而对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帖耳、默不作声,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认为他们作为人已经名存实亡。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我与我的同志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见到的一件事。
那是1973年夏季,帕帕多普洛斯还在台上,帕那古利斯带我去见一些抵抗运动者。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3个字母OXI,希腊文的意思是“不”。
这3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也不褪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地、无视一切地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 是的,这本书没有过高的要求,它只指望成为一段由30来位大人物提供的当代历史的直接见证。
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意义。虽然新版本要比原来的版本丰富,但再版时我并没有重新加工。我只是在每一篇的前言中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有的地方只是改变了动词的时态,也就是把原来的现在式改为过去式。
根据同样的原则我在新版中增加了于原书出版后进行的另外10次最重要的采访的记录。这10次采访的对象是朱里奥•安德雷奥蒂、乔治•阿门多拉、马卡利奥斯大主教、中央情报局的头子威廉•科尔比和他的对手奥蒂斯•派克、圣地亚哥•卡里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亚马尼。
显然,时间会使我对某次采访的印象及对某个人的看法有所加深和发展。但是,如果我采用后来的观点来评论事情,就会使它们失去作品作为记录当时当地情况的文献的价值,使它们失去真实性,就像一张经过修改的照片一样,只是在象征性地结束此书前,在介绍关于对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的访问时,我认为有必要加一段有关他的事。
这不是出于个人感情,不是因为阿莱科斯曾经是我生活中的伴侣,而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
他是被本书所揭露、谴责和憎恨的权力所杀害的。因此,在他被害后,我更希望读者阅读这本书,想到那个在伯罗奔尼撒岛的树上顽强地、无视一切和永不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的“不”字。